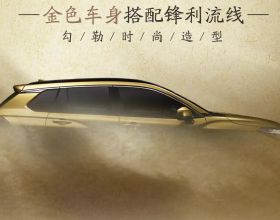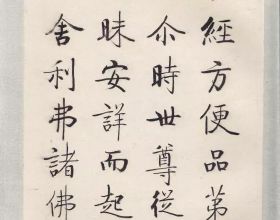《試院煎茶》是北宋詩人蘇軾詠茶詩的一首代表作,詩中涉及的有關定窯陶瓷的論述歷來是學人關注的焦點。例如對“定州花瓷琢紅玉”的理解就有“定州紅瓷說”“定州白瓷說”“定窯兔毫盞說”“定瓷堅硬緻密說”以及“茶水色質說”等多種說法,具體哪一種說法更為符合蘇軾的本意,還需要結合全詩內容來加以分析。
詠茶是蘇軾《試院煎茶》創作的重點,其涉及的北宋茶文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該詩以試院煎茶為起興,描寫了煎水、碾茶、羅茶的各個環節,並在公家與個人煎茶的鮮明對比中,抒發了詩人貧困落魄的失意心情。儘管如此,蘇軾用磚爐石銚煎茶的自足,還是流露出那種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的達觀。詩中最能體現北宋茶文化的內容是:“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蟹眼、魚眼、松風鳴,是茶文化中對煎水火候的一種把握,亦稱為湯候。黃庭堅煎茶詩云:“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其二)與蘇軾所寫湯候相似。但黃庭堅用小鼎煎茶,鼎口寬大,能夠用眼睛直接辨識水色形態。而蘇軾使用口蓋較小的石銚煎茶,一般而言,是先聞其聲後辨其色。明人許次紓對此說得較為清楚:“水一入銚,便須急煮。候有松聲,即去蓋,以訊息其老嫩。蟹眼之後,水有微濤,是為當時。大濤鼎沸,旋至無聲,是為過時。”(《茶疏》)“蟹眼之後,水有微濤”就是蘇軾所說的“魚眼生”,這個時候的水正適合煎茶,火候若過就成老湯了。按湯候的先後次序,魚眼生的階段當視為第二沸,也就是“銀瓶瀉湯誇第二”的所詠之意。但在蘇軾看來,這也未必盡合古人煎茶的本意。他明確表示古人煎水不煎茶,這與唐代陸羽的《茶經》將茶末放入沸水中烹煮的方法有所不同。一方面,他看重唐人李約在煎茶時對水質和火色的講究,主張“活火發新泉”。活火即使用炭火的火焰煎茶,新泉意味著烹茶要選擇優質的山泉水。另一方面,他推崇時人文彥博的古蜀煎茶法。其弟蘇轍在《和子瞻煎茶》詩中說:“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在蘇氏兄弟看來,西蜀煎茶法除了深諳水聲火候之外,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將煎水視為茶藝的一個獨立工序,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茶湯的鮮嫩與甘醇,以便充分發揮茶性的獨特滋味。這種方法實際上代表著唐宋不同的茶文化傾向。
鑑於此,製茶便相對成為另一道工序。《試院煎茶》提到的“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是對北宋茶文化中“碾茶”與“羅茶”的生動描述。蔡襄的《茶錄》對這兩道工序有明確的記載,即先用乾淨的紙將茶餅包裹嚴實進行捶碎,然後立刻反覆碾壓,茶色就會變白。羅茶時,羅孔細密,茶末就會漂浮在水上;羅孔粗疏,茶末則會沉底不泛。宋徽宗的《大觀茶論》認為,羅茶時要不厭其煩地反覆進行,這樣才能使茶末輕泛於茶湯之上,盡顯茶之色澤。蘇軾煎茶自然也少不了這一環節,在詩性化的語言表達中,他碾出了一顆顆美麗的細珠,還羅出了輕盈飄舞的飛雪。潔白的茶末旋轉繞甌而下的樣子,正是宋人所追求的製茶效果。
當然,煎茶工藝還需要配備必要的器具,這也是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經》專列“茶之器”25種,《茶錄》列有9種。在宋代,選用何種器具烹茶、品茶都有一定的講究,例如湯瓶崇尚金銀質地,茶盞則以青黑為貴。金銀質地的湯瓶是一種身份地位的代表,民間烹茶多使用鐵或瓷石製品。而茶盞的選擇,更主要的是配合茶色的需要。《大觀茶論》認為,茶色以純白為最佳,青白色次之,灰白黃白又次之,所以點茶時應該選擇青黑色釉面的茶盞,尤其以釉上有兔毫般細密紋理的為首選,這樣的茶盞容易呈現茶色的光彩色澤。《茶錄》也持此論,其以建窯黑瓷中的兔毫盞為上,主要是襯托茶色之白。相反,青白色的茶盞不易呈現茶色,也就不為鬥茶者使用。如此看來,在《試院煎茶》中,蘇軾於文彥博處看到的印象深刻的定窯茶盞,未必就是定州白瓷。按宋人品茶的講究程度,曾任北宋宰相的文彥博既然追求西蜀古法煎茶,其在茶盞的選擇上應不會使用連鬥茶者都不用的青白盞或定窯白盞。
現在的問題是,何謂定州花瓷,“定州花瓷”與“琢紅玉”到底是什麼關係?很多學者都注意到金末劉祁《歸潛志》中所說的“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遂認定蘇軾所謂“定州花瓷”即指定窯白瓷。也有人更進一步辨析“花瓷”指的是定瓷器壁上裝飾的各種花式圖案,而非指色彩。清代《南窯筆記》說,定窯“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淚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種,名定州花瓷是也”。定窯源出定州曲陽,屬白色窯系,受北方水土氣候影響,素有“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的美譽。宋南渡後,江西景德鎮曾大量仿製北宋官窯,其中就有定窯,因地理環境的差異,南定窯呈現出與北方不同的青白色,因其釉似粉,又稱“粉定”。北方定窯裝飾技藝以刻花、印花、劃花為主,講究刻刀的運轉與雕琢,而非使用五彩進行點綴。花式內容多以牡丹、萱草、飛鳳、盤螭為多,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認為這種工藝源自秦鏡,其妍細處非人間所有,屬於古瓷中的精麗之品。儘管清代陳瀏的《匋雅》認為“粉定”系陶瓷的裝飾技藝中有彩畫一項,但至少在定州窯陶瓷中,“花瓷”的概念仍指向素雅的刀刻紋理裝飾特色。
誠然,“定州花瓷”的含義亦非僅指白瓷。成書於清代嘉慶年間的《景德鎮陶錄》對定州窯陶瓷的記載便有白定、紅定、紫定、黑定等多種,並認為宋人以紅、白定為上。但在明代《格古要論》《遵生八箋》和清代《古窯器考》《文房肆考圖說》以及乾隆的詠定窯詩詞中,紅定幾乎都處於闕如狀態,以至於高濂、乾隆皇帝都高度懷疑紅定的存在,而把問題直接轉到對蘇軾“定州花瓷琢紅玉”的理解上。高濂將“琢紅玉”改為“琢如玉”,即認定定窯沒有紅瓷。乾隆皇帝則認為世見定瓷皆白色,蘇軾“琢紅玉”詩句欠斟酌,有辭人誇張之嫌。當代定窯復興者、中國陶瓷藝術大師陳文增先生指出,古人之所以懷疑紅定的存在,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見到過紅定。他從事定窯恢復工作30餘年,對定窯生產及其窯變規律瞭如指掌,定窯紅瓷是定窯黑釉的窯變色,成因複雜,成功率也比較低,但宋代南北定窯廠均能生產這種窯變瓷器是不容置疑的。他自己也試製成功了一款紅潤如玉的紅定,所以他確信紅定的存在。作為詩人的他,對蘇軾“定州花瓷琢紅玉”的理解也不同於前人。他認為“琢紅玉”是詩歌藝術的倒裝寫法,意思是定州花瓷儼然是在透亮柔潤的紅玉上雕琢而成。
關於定州紅瓷,宋人有明確記載。北宋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說,宋仁宗在張貴妃閣中見到定州紅瓷後,便責問她該器物得自何處?張貴妃以王拱辰所獻為答,仁宗便以妃子不應收受大臣禮物為由將其打碎。南宋周輝於《清波雜誌》中記載,他自己在出使金朝時曾見過定州紅瓷,與饒州景德鎮的窯變紅相比,後者更為鮮豔。可以說,宋金時代的北方地區,定窯陶瓷生產中均出現過紅定。元祐八年,在政爭中失意的蘇軾被派往北宋北部邊郡的定州管理軍政事務,其足跡亦至曲陽。他對定瓷不會感到陌生,而文彥博所用的定窯茶盞之所以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想必不是尋常白定,而是一件難得的窯變色定。從碾茶時產生的白色茶末以及北宋崇尚純白茶色來看,其所謂“琢紅玉”自然也不是指茶色,而是指與宋代茶文化中器具審美相關聯的色定。這種推斷只能指向定州紅瓷。
總而言之,理解蘇軾《試院煎茶》中的北宋茶文化,是解讀“定州花瓷琢紅玉”的關鍵。定窯陶瓷屬白色窯系,在北宋茶文化中,定窯白盞並不如黑色建盞那樣適合作為鬥碾茶的器具使用。相反,定窯生產的窯變瓷,諸如紅定、紫定、黑定倒是迎合了宋人的審美。
(作者:陳博涵,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