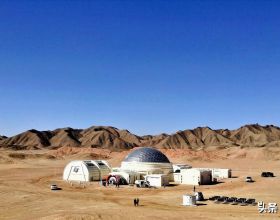閔行圖書館館員孫鶯說要請我喝咖啡,我說好啊,你定個時間吧,結果三天過後,她寄來了兩本書,一本是《近代上海咖啡地圖》,一本是《咖啡文錄》,都是她編的,她花了很大的工夫,蒐羅了從1895年到1949年間出版的近百種近現代報紙和期刊,從中篩選、輯錄出與咖啡館有關的資料,猶如拼圖一般,拼湊出一部曾經的上海社會生活史。
都說文人愛喝咖啡,我覺得或許這是一種象徵,顯示出文人對於新潮的敏感和對多元文化的接納,當然,這也是文人的腔調和情調的一種體現。雖然魯迅說他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花在了工作上,但他卻不拒喝咖啡,早在北京時期,他就上過咖啡館,1923年8月1日,他在日記裡寫道,與清水安三同至咖啡館小坐。到了上海時期,魯迅去咖啡館的次數就更多了,僅1930年上半年,他在日記裡寫到過一起喝咖啡的便有李雪峰、柔石、韓侍桁等,而與左翼作家商討籌備成立左翼作家聯盟,更是多次在咖啡館裡進行的。可見,除了消遣,魯迅是視咖啡館為會友談事的一個比較理想的場所的。
因此,在咖啡館喝咖啡便打上了“文人咖啡”的印記。確實,當時在上海的文化人大多喜歡去“孵”咖啡館,有的作家乾脆在那裡一邊喝咖啡一邊寫作,此種情形延續至今。文學家、美學家張競生說,喝咖啡的確能夠幫助激發文思,所以他常為喝咖啡不夠過癮而苦惱,覺著不能長時間一杯在手,也就不能神氣一直迷離於腦際,學者、記者曹聚仁很有趣,說自己是個“土老帽兒”,愛喝茶,不太愛喝咖啡,但是,要與人談新文藝,這就需要有一種“文藝復興”的感覺,於是就得去咖啡館,而且還特意選了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的名為“文藝復興”的咖啡館。豈料,這家白俄人開的咖啡館,沒有文化上的啟蒙景象和黎明氣息,倒是有著一股嚮往於帝俄王朝復辟重來的陳腐味,大煞風景。我讀著曹聚仁的咖啡文章,不禁莞爾。
在散文家、劇作家何為看來,咖啡館就應是一個文藝沙龍,在他的想象中,格調高雅的咖啡館要具備文化素質,門面裝潢和內部陳設既要現代化,又要有獨特的藝術趣味,“新穎柔和的燈光,非具象的壁飾,若有若無的典雅音樂,造成一種恬靜閒適的氛圍”,文人們可以在此休憩和相互交流。循著何為的文字,我也想象起那些創造著文學和藝術的人們,在這樣的咖啡館裡是何等的優雅和愜意。但是,何為常去的有著文藝沙龍品質的咖啡館卻是簡陋的,他回憶道,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那兒有一家賽維納咖啡館,裝置簡單,價格低廉,可異國情調卻為其增添了一分藝術感,所以,當時不少畫家、作家和詩人在那裡據有幾張固定的桌子,往往從下午坐到晚上,其中尤以崑崙影業公司的電影工作者居多。那時,為了把田漢的著名話劇《麗人行》搬上銀幕,他參加了電影劇本的分鏡頭工作,與導演陳鯉庭、鄭君裡,製片人夏雲瑚、任宗德,主演趙丹、黃宗英、上官雲珠、藍馬、沙莉,作曲家王雲階,美術家張樂平等人,幾乎每天下午都在賽維納咖啡館喝咖啡,高談闊論,碰撞思想火花,討論如何將話劇改編成電影,如何使影片更好地呈現愛國主題。何為認為,這樣的咖啡館就是“文藝沙龍”。我這些天正打算去看望黃宗英,我很想問問她,喝咖啡是不是因此給她這樣的明星增添了文人的氣質。
我跟孫鶯說,看了你編的兩本書,已是咖香氤氳,為了表示我的祝賀,還是我請你喝咖啡吧,地點是多倫路上的公啡咖啡館——這家咖啡館可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誕生的搖籃,既有歷史,又有文化。(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