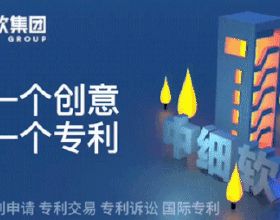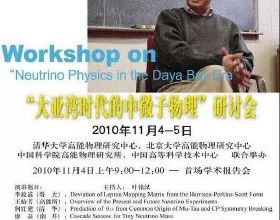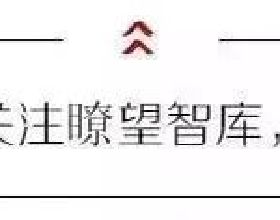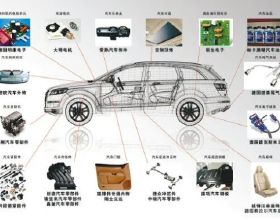評書評話在全國各地都有,大致可以分為北派和南派。北京的評書是北派評書的主體。著名的評書藝人很多,聽書的市民也很多。這大概與北京城內不從事生產、靠俸祿為生的旗人較多有關。因為許多長篇評書需要連續聽上幾個月,沒有閒暇時間的市民是成不了評書聽眾的。
在清朝前期北京城裡還沒有專門的聽評書的茶館,說評書的藝人只能拉場子撂地說書。在一塊空地上擺上一張八仙桌,桌上放一塊醒木,桌子前邊放上幾排長凳,作為聽眾席。等到聽眾大致坐滿後說書人來到場子裡,坐在八仙桌後邊的凳子上掏出手巾放在桌上,摺扇和醒木也是說書人必備的道具,都在桌上放好。在開書前說書人要先說上幾句引場詞,都是些有韻的千篇一律的套話,例如:“一塊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塊轄文武,文武一塊轄黎民。聖人一塊醒儒教,天師一塊警鬼神,僧家一塊勸佛法,道家一塊勸玄門,一塊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勸世人,湖海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藝論家門。”引場詩有靜場的作用。說完引場詩後才能開書。
直到20世紀初的光緒末年,北京城裡才出現了正式的書茶館,一些著名評書藝人改在茶館獻藝。書茶館是以聽講評書為主的茶館,每天上午接待喝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約請說書先生、唱鼓詞的藝人來此說書、演唱。茶客們可以邊喝茶邊聽評書作為消遣。評書分為“白天”和“燈晚”兩場。“白天”由下午三四點開書,到六七點散場。“燈晚”從晚上七八點開書,直到十一二點散場。有的茶館在下午一點到三點加一個短場。說書先生在某個茶館說上兩個月,然後換到別的茶館,這個茶館再換上別的說書先生說別的書,也有連說三個月的,但是很少有連說四個月的,每兩個月一輪換稱為“一轉”。
書茶館
聽書的茶客要另交書錢,一般每回書一、二文錢。書錢的分配由茶館主人與說書藝人事先商量訂約。藝人的名氣大,所說書目內容吸引人,說書技巧高,聽書的人就多,藝人的收入也就多一些,一般的說書藝人的收入僅夠溫飽而已。
北京是評書藝術的誕生地,有一批著名的評書藝人。他們說書的技藝十分高超,引人入勝,他們能說的書目比較多,其中總有一兩部最拿手的書目。王傑魁說《包公案》、劉繼業說《濟公傳》、連闊如說《西漢》、《東漢》,趙英頗說《聊齋》、潘誠立說《明英烈》、雙厚坪說《隋唐》、陳士和說《聊齋》,都無人可比。
評書按題材可分為幾類。第一類是袍帶書,內容主要是帝王將相殺伐征戰的故事,像《列國》、《三國》、《西漢》、《東漢》、《隋唐》、《精忠》、《明英烈》,由於書中人物身穿袍帶甲冑,所以稱為“袍帶書”。第二類是公案書,也叫俠義書,內容主要是官府辦案,俠客與草寇搏鬥,以《七俠五義》、《三俠劍》、《彭公案》、《施公案》為代表。《水滸》則介於袍帶、公案之間。第三類是神怪書,主要是神仙妖怪鬥法的故事,《封神榜》、《西遊記》、《濟公傳》、《聊齋》就是其中的有代表性的書目。
書茶館裡有一些老聽客,他們對所聽評書的內容十分熟悉,欣賞口味也很高,說書藝人如果得到他們的稱讚,就能出名;反之,如果說錯了書就會受到批評,以致不能出名。東華門外的東悅軒和地安門外一溜衚衕的同和軒兩處書茶館就以老聽客多著稱。藝人沒有十分把握不敢在這兩個茶館說書。反之,天橋的福海軒裡聽書的一般遊客多,因此外行也多,在此說書掙錢就容易些。
評書藝術有一整套藝術技巧,像“開臉”(描繪人物形象)、“擺砌末”(描述周圍環境)、“賦贊”(用韻文讚美人物、景物)等等,其中許多技巧已形成固定不變的程式,像描述黑臉的戰將,不管哪部書中,不管是張飛還是尉遲恭,一律都是“烏油盔鎧,皂色緞錦徵袍,坐下烏騅馬,掌中皂纓槍”。對於那些老聽客來說多次重複未免生厭。於是一些說書藝人為了適應聽眾,就加進許多“書外書”,不僅在情節敘述中添油加醋,古事今說,佐以評論,而且暗地譏諷時事,但又不露鋒芒,能讓人心領神會,妙趣橫生。
雙厚坪是清末民初北京城裡著名的說書先生,他常在同和軒、東悅軒等處說書,聽客中有不少破落的旗人。有一次,一個旗人吹噓他舉行婚禮時,皇上賜給他一根帽子上戴的花翎子,並且一再要求雙厚坪把這件事編到書里加以渲染。雙厚坪推辭了幾次,那人盛氣凌人地叫嚷:“沒關係,你怎麼編都行,上邊怪罪下來我擔著!”“好,雙某獻醜了。”這天雙厚坪正說到《隋唐》中“楊廣下揚州”一段,臨時加了一段書外書,大意是:
楊廣下揚州時正是伏天,天氣很熱,他倒坐在御覽船上乘涼,左右圍著幾個太監,拿著刀槍弓箭在那兒守衛著。這一下驚動了眾水族,忙向龍宮稟報:“天子船頭納涼,已到我等水疆!”龍王一聽:“既然如此,良機難逢,你等速去討封。”“是!”蝦米浮出水面,衝楊廣耍了一套槍。楊廣說:“封你為金槍大將軍。”蝦米高高興興地走了。螃蟹一沉一浮地橫著浮出水面,張開兩隻夾子示意,楊廣說:“封你為鐵甲大鐵將軍。”“謝封!”緊跟著鯉魚搖頭擺尾跳出水面,楊廣說:“封你為龍門大學士。”鯉魚也心滿意足地走了。輪到烏龜出場,它撲騰了兩下蓋子才露出水面,但是蓋子上長滿青苔,楊廣沒認出來,根本沒理它。烏龜急了,爪子趴在船頭,脖子伸出一尺多長,腦袋在船幫上一撞三響,楊廣嚇了一跳,忙吩咐左右:“給我射!”“嗖”地一箭,正射在烏龜的後脖子上。烏龜趕緊跑回龍宮,龍王問它:“封你什麼啦?”烏龜氣喘吁吁地說:“雖說沒討到封,皇上他賞了我一根翎子。”
當年既沒有曲藝學校也沒有曲藝團,想學說評書,必須拜師傅,沒有師傅沒有家門的到哪裡都吃不開。徒弟拜了師傅之後,就要像在家對待父母一樣尊敬師傅,每天為師傅鋪床疊被,端茶倒水乾各種家務活。師傅說書之前,徒弟要搬桌子,拿凳子。師傅開書之後徒弟要拿著小籮筐在場子裡向聽眾要錢,行話叫做“託杵”。至於說書的技巧,師傅並不直接傳授,而是由徒弟在一旁自己觀察、模仿、琢磨。聰明的徒弟經過一段時間後就能學到許多師傅的技藝,那些腦子笨的徒弟很可能三五年都學不到什麼東西,只有傻幹活的命。過去有句老話“師傅帶進門,修行在各人”,這句話雖然有一定的道理,卻也反映出師徒制度的不合理性,徒弟實際上往往成為師傅的不花錢的雜役。師傅之所以不願意下功夫教徒弟,是因為不願意樹立起今後的競爭對手。在舊社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觀念在演藝界也確實存在。
評書藝人收徒弟有許多講究。某人想拜某位說書藝人為師,要由行內人介紹與師傅見見面,師傅同意後要下請帖請客,在飯館裡擺上幾桌酒席。遍請收徒人的本門師伯師叔師兄師弟,也會邀請一些同行業的老前輩,稱為“擺支”。到了正式拜師的日子,眾人共聚一堂,在堂中供奉已故的本門前輩的神位。由代筆師書寫書生帖一份,稱為“關書”。主要內容為:今有某某人,年幾歲,經人介紹情願投在某先生門下為徒學演評書,以謀衣食。今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在祖師駕前焚香叩稟。自入門後,倘有負心,無所為憑,特立關書,永遠存照。介紹人、師傅、徒弟都要在關書上簽字畫押。這時徒弟才算正式入門,然後由師傅和本門的長輩一起為新入門的弟子取藝名,填寫在關書上。然後由新入門的弟子行拜師大禮,再向出席拜師禮的各位行禮。徒弟一般要學藝三年能出師,此時還要擺謝師宴。說書這一行學起來也非常不容易,一要口齒清楚,二要有表演才能,三要記憶力好,能把幾十萬字的長篇書目都記牢,要有歷史文化知識。
鼓曲藝人的情況與評書藝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清末民初北京地區流行的鼓曲有京韻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許多種。以京韻大鼓最受歡迎,出現過劉寶全、白雲鵬等著名藝人。20世紀30年代男演員逐漸被女演員取代,人們將演唱鼓曲的女演員稱為“鼓姬”,也有稱為“大鼓妞”的。演唱鼓曲一要口齒清楚,吐字發音準確,二要嗓音洪亮,三要身材好,相貌好,鼻直口闊,面白唇紅,女演員要身材苗條,容貌秀美,國要有表演才能,一舉一動的姿勢要好看,喜怒哀樂的表情要像樣。
鼓曲表演的場地有的是在空地上,用葦蓆圍上,擺上幾排凳子。也有的是在專門的坤書館裡,設有一個不高也不大、沒有後臺的小舞臺。演唱鼓曲的女演員在臺上坐成一排。演唱時站在臺前正中,一旁有小樂隊伴奏,臺下擺上七八張桌子和二三十把椅子作為觀眾席,聽眾一邊聽曲一邊喝茶、吃瓜子、水果等各種食品,並且不時地和臺上的女演員點頭、微笑、打招呼。觀眾可以點演員、點曲,稱為“戳活”。先由遞活者手持一把寫滿曲目的大摺扇向聽眾展示,某人點曲後,遞活者高喊一聲“有題目啦”。隨即由某演員演唱某曲目。點唱的價格一般在大洋幾角至一元。也有一些闊少爺花錢捧角,點個曲花上個一二十元的,甚至有因為捧大鼓妞將家產當盡賣光的。大鼓妞們和那些闊少之間自然也少不了眉來眼去、賣弄風情之類的逢場作戲,有的甚至勾搭成奸,由賣藝走到賣身,或者成為闊人家的小老婆。
坤茶館
在北京唱大鼓掙錢很不容易,因為北京的老聽眾多,有文化的內行人多,沒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在北京就沒有多少聽眾。只有一流的鼓書藝人才能在北京賣藝,而且口乾舌燥唱上一天也只能掙到幾塊錢。學唱大鼓也要拜師傅,拜師儀式與評書藝人拜師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