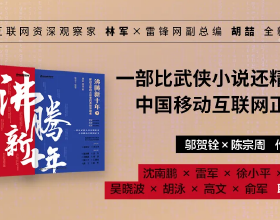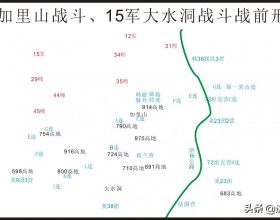“怎麼回事,胡先生?”
1936年12月25日,由美國“天才童星”秀蘭·鄧波兒主演的冒險題材歌舞片《偷渡者》上映,該片講述的是一個名叫青青的美國女童在中國上海遇奇歷險的遭遇。
電影中,萌化了的秀蘭·鄧波兒身穿傳統中式斜對襟布褂,還像模像樣地拉著二胡、說著荒腔走板的中文,電影上映的那一年,秀蘭·鄧波兒年滿8歲。
走出片場的1977年,秀蘭·鄧波兒到訪中國,此時她已經不再是“最可愛的小天使”,而是一位49歲的中年女性,息影將近三十年。
2014年2月10日,在三個孩子以及一個曾孫女、兩個曾孫女的呵護下,秀蘭·鄧波兒於美國加州伍德賽德家中平靜地離開人世,享年85歲。
“小天使”會飛回天國,但銀幕會將她的童真留下來,撫慰一顆顆灰暗的心靈。
令人矚目的生命
“我們向她致敬。她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生命,作為一個演員,作為一個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我們敬愛的母親、祖母、曾祖母和崇拜了55年的妻子。”
秀蘭·鄧波兒去世後,她的家族向各位影迷、觀眾,以及每一位關心她的人發表了宣告,正如宣告中所言,毋庸置疑,秀蘭·鄧波兒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生命。
這個令人矚目的生命起源於美國加利福尼亞聖莫妮卡市,秀蘭·鄧波兒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出納員,母親則是一名漂亮的家庭主婦。
這位家庭主婦曾經是名舞蹈演員,有著強烈的電影夢,於是那未完成的夢便寄託在了女兒秀蘭·鄧波兒的身上,三歲起,秀蘭·鄧波兒便被母親送到好萊塢星探常出沒的舞蹈學校。
“1928年4月23日,母親的計劃最終實現了,我真的是個女孩。我在晚上九點來到人世,可是錯過了晚餐時間。我從一開始就丟了一頓飯(從那個時候,我一直試圖彌補這一損失)。”
果然,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只不過,做好準備的是格特魯德·阿米莉亞·鄧波兒,而不是她年僅三歲的女兒秀蘭·鄧波兒。
“秀蘭,精神點,精神點!”
這是母親對女兒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鄧波兒自述過,她僅有兩年懶惰的嬰兒時期,從此之後就只剩下工作了,每天工作5小時,週末還要增加2、3個小時,如果拍戲出了狀況,母親是要把她關進小黑屋的。
除了拍戲,每天還要和私教學習3小時,以至於工作時也睏倦不已,母親的帶著責備的提醒就會在這時響起。不過,秀蘭·鄧波兒從未有過抱怨,不是她懂事或者明白母親的苦心,而是,“我當時以為每個孩子都在工作”。
秀蘭·鄧波兒的母親從小就為她鋪好一條明星路,為她打造有56個卷兒的專屬髮型,為她打造了一條黃金的起跑線:6歲出演《起立歡呼》大獲成功、7歲獲得奧斯卡、11歲片酬超過12萬美金、簽約福克斯……
在母親的心中,女兒不僅僅是個可愛且美麗的孩子,而且是自己的投射,如果格特魯德·鄧波兒重新活一遍,一定會是秀蘭·鄧波兒,甚至,比秀蘭·鄧波兒更好、更成功、更矚目。
可母親忘記了,她還是個孩子,她是她自己——秀蘭·鄧波兒。
人們最迷戀,甚至可以說貪戀的,是秀蘭·鄧波兒身上純潔無邪的童真,她會仰著肉嘟嘟的臉龐,穿著連衣裙、短襪和皮鞋,跳踢踏舞、噘嘴逗笑、流淚生氣。
好像看著她,經濟大蕭條社會中坑蒙拐騙、頹廢墮落和因經濟蕭條而變得異常艱難的生老病死都可以拋之腦後,所有人都可以活在童話裡。
當然,要讓很多人活在童話裡而忘卻現實的慘淡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童話會以最快的速度在秀蘭·鄧波兒自己的生活中消失:6歲那年起她便不再相信世界上有聖誕老人,聖誕夜的那天,母親帶她去百貨商場看聖誕老人,而聖誕老人向秀蘭·鄧波兒討要了簽名照。
出逃的女兒
令人矚目的生命也會有一天要走到令人厭棄的地步,對於秀蘭·鄧波兒來說,這一天到來的速度確實太快,只是她也分不清,到底是這一天來得太快,還是自己的成長速度太快?
鄧波兒的童真一早就被名利和物慾所沖淡,好萊塢和物慾社會的醜陋和骯髒並沒有因為她是個小孩而有所隱藏,反而正因為她是個天真無知的小孩,至少看上去是這樣,而更加的肆無忌憚。
一個大名鼎鼎的製片人,會在鄧波兒的面前變為一個“人體藝術家”,沒有見過他人裸體的鄧波兒最開始只覺得有趣,“我笑了,笑哭了”,而那個道貌岸然的男人則暴怒把她轟了出去。
他們讓她看見醜的,但要她表演美的,電影公司甚至要求她不要過多外出,以此來保持自己的童稚感,有人告訴她,觀眾是能從她的眼睛中看出她童真的流逝的。
到今天,在鄧波兒後期作品的短評中最頻繁出現的一句話仍然是“秀蘭·鄧波兒長大了,沒有小時候可愛了”;而在當時,少女鄧波兒要面對的是惡評如潮評和慘淡的票房。
可愛,是大多數人對秀蘭·鄧波兒的要求,一旦她長大就不可愛了,他們投射在鄧波兒身上的夢就會破碎,他們將不再為她的電影買單,哪怕少女時期的秀蘭·鄧波兒依舊美得如同白雪公主。
秀蘭·鄧波兒的青春期並沒有如夏花一般絢爛,即便她有著花一般的身軀和麵龐也無人欣賞,鄧波兒從票房寵兒逐漸走到無戲可拍的地步,於她自己而言還可以接受。
但對於她的母親來說則是致命的打擊,從女兒出生之後就著手製定明星計劃的母親,眼見自己的計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就這麼放棄自然是不甘心的。
秀蘭·鄧波兒停止演藝事業回到學校唸書之後,母親對他的印象都是巨大的人生的操控並未停止。
這位母親依然極力希望女兒繼續演藝工作、重回人生巔峰,仍然給她不斷地接合同,哪怕是一個兩三句臺詞的配角也在所不惜,說實在的,鄧波兒的母親比鄧波兒更適合當一個演員。
究竟是秀蘭·鄧波兒長大後不可愛了,還是看客們不願長大?究竟是要秀蘭·鄧波兒永遠做彼得潘,還是看客們需要這麼一雙無邪天真的眼睛來仰望自己,即便自己在做的事情醜陋、骯髒?
秀蘭·鄧波兒逐漸對演藝事業意冷心灰以及觀眾逐漸拋棄她的時候,鄧波兒選擇了結婚生子和淡出影壇。
鄧波兒的第一任丈夫約翰·阿加爾是一名空軍士兵,他是她同學的哥哥,這個男人身上擁有著鄧波兒從未體會過的叛逆,於是她17歲與這個人結婚,她也想嚐嚐叛逆的滋味。
母親是反對這樁婚姻的,這是一個極為聰明的女人,她已經預示了女兒的這段婚姻帶來不了什麼好處,但她已經無法再拴住女兒,因為女兒這場叛逆的婚姻主要就是為了逃離她。
母親讓鄧波兒不要公佈自己已婚的訊息,而鄧波兒故意帶著鑽戒出席各種聚會,她厭惡這樣的生活,被母親掌控的生活,她想得到的就是透過婚姻來擺脫這一切,卻看錯了人。
秀蘭·鄧波兒的第一段婚姻持續了5年,他們擁有了一個女兒,婚姻生活的最初鄧波兒還在拍戲,但她更痴迷於做家務活,或許在她的想象之中,自己一定可以透過婚姻來會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
可惜丈夫酗酒無度,並且想利用鄧波兒來拼命往演藝圈爬,最終婚姻破裂她還是為自己的叛逆買單了。
“我不想再遭受打擊。”秀蘭·鄧波兒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名出色的企業家,查爾斯·布萊克此前從未看過鄧波兒的電影,這一點對於鄧波兒尤為重要,但保險起見,她還是託朋友對這個男人進行了一番深入調查。
這一次,她終於明白婚姻不是叛逆的遊戲,而是慎重的選擇,與查爾斯結婚後,鄧波兒徹底離開了電影界,從此再未接拍過一部電影,他們婚後生了兩個孩子。這一次,她選對了,這是個深愛她的好男人。這個男人和她生活了超過五十年,他和他們的孩子、孫子、曾孫一直陪伴著她走完這段非凡的生命旅程。
秀蘭·鄧波兒真的長大了,不再是稚氣的兒童、不再是出逃的少女,不再是母親或者不願意長大的看客的投射。
她成為了她自己,並且沒有像別人說的“童真消散了”,她長大了,她的童真也長大了,變成了在物慾橫流的世界中潔身自好的勇氣,這比童稚的天真無邪更為珍貴。
幸福且幸運的“花瓶”
退出影壇的秀蘭·鄧波兒還是那笑語盈盈的樣子,人們都說她是不老的神話,是天使的代名詞。
但她自己明白,她現在的笑不是為了表演、不是為了討好,是屬於秀蘭·鄧波兒自己最真實的笑。
“我是一個卓有成就的幸福女人,也是幸運的女人。如果還能再活一遍,我不會對我的一生做任何改變。”
作為演員,應該說是作為童星,秀蘭·鄧波兒極大程度上是一個“花瓶”,她需要扮演的就是天真可愛的小女孩。
但極少有人說秀蘭·鄧波兒作為演員是一個“花瓶”,因為她從兒童時期就表現出了極大的表演天賦,她的哭戲令人拍案叫絕、他的一顰一笑牽動人心,何況她還支付了以整個童年為代價的勤奮和努力。
不過,作為政客,鄧波兒確實是個“花瓶”,70年代起,鄧波兒進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後出任美國駐各國大使,1976年任禮賓司司長,看著是光鮮亮麗,但她可發揮的餘地不多。
1977年4月,秀蘭·鄧波兒以外交官的身份造訪中國,電視臺連播《小酒窩》、《小水手》等多部鄧波兒的電影,一時間在中國引發了秀蘭·鄧波兒熱潮,少兒頻道主持人“金龜子”劉純燕為其配音,並因此斬獲飛天獎。
其實,早在民國時期,秀蘭·鄧波兒就已經備受國人喜愛,1935年上海大光明大戲院就放映過《亮眼睛》,當時貼出的海報已經在借用秀蘭·鄧波兒的名氣打廣告:“秀蘭·鄧波兒新傑作”。
有上海的女明星模仿秀蘭·鄧波兒而走紅,有《良友》等家喻戶曉的雜誌做鄧波兒專題,有肥皂盒、香粉的商標都用鄧波兒的頭像,並且這些商品大受歡迎。
不止是在美國,在世界上多個國家,秀蘭·鄧波兒都擁有大量的影迷,似乎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需要秀蘭·鄧波兒那般天真無邪的笑容去呵護和撫慰,畢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始終令人們心醉的是秀蘭·鄧波兒童年的面容,極少有人能真正欣賞她息影后的笑容,人們還是認為妻子、母親、祖母、外交官等身份無足輕重,作為演員這是一種褒獎。
但作為一名傳奇女性,多少有些憂傷。電影是造夢的藝術,生活卻不能永遠活在夢中,如果把生活當成了夢,不願意真實地長大,那不就和說“秀蘭·鄧波兒長大了,沒有小時候可愛了”的看客別無二致了。
秀蘭·鄧波兒長大了,但她依然可愛著,作為電影人她把童真永恆地留在銀幕上,作為一名女性,她用人生書寫了傳奇。
“她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生命。”
如何才能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小天使,可能是擁有毫無邪氣的童真,但也可能是風雨之後仍然樂觀、微笑的成長。
秀蘭·鄧波兒用一生出色的完成了“小天使”這個角色,只是觀眾愛看的究竟是她在電影中飾演的角色,還是用生命來展示的樂觀與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