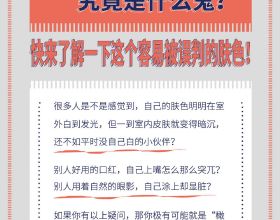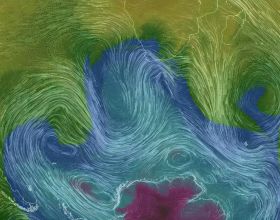我喜歡荒涼之美
文丨素 素
生態文學是當下盛行的一個熱詞。以繁榮生態文學的立場,書寫人類對生態保護的自覺和自省,書寫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態危機,已經成為當代作家的一種責任。
《我喜歡荒涼之美》,不太像論壇題目,但它的確是我一直以來的審美取向,也是我此刻最想表達的心情。
荒涼,網上百科對它有個解釋,一是形容曠野荒蕪,山河枯寂;二是形容人煙寥落,淒涼悽清。如果打比方,或是一片荒涼的山野,或是一個荒涼的村莊。在我看來,前一種荒涼,具有自然屬性,後一種荒涼,具有社會屬性。就是說,在荒涼的定義裡,既有自然天成,也有人力所為。我喜歡的荒涼,當然是前一種。
的確,有一種荒涼是大自然固有的荒涼,那是一種原始的帶有洪荒感的荒涼;有一種荒涼是大自然被人類之手修改破壞的荒涼,那是一種後天的具有悲劇感的荒涼;還有一種荒涼是因為大自然的面目全非給人類心靈帶來的荒涼,那是一種絕望的萬劫不復的荒涼。當然,這一切的發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只是人類現在正處在這個過程最灰暗最恐懼的時間節點。
正因為喜歡大自然的荒涼之美,我曾一個人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之上行走。去過大興安嶺,去過黑龍江源頭,去過長白山,去過北大荒。在那裡,我果真看到了荒涼本然的樣子,但我也看到了它消失而模糊的背影,因而寫了《綠色稀薄》,寫了《追問大荒》,寫了《最後的山》,以表達我的不安和慌恐。
我曾不止一次去過遼西。在遼西地表之下,隱藏著曠古未宣的荒涼,因為那裡是世界上第一隻鳥飛起的地方,也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開的地方。那朵花被命名為遼寧果,那隻鳥被命名為中華龍鳥。而所有在遼西出土的花和鳥,皆以化石的形態示人,告訴我那裡曾經有過的荒涼和繁榮。
荒涼是地球的原稿,也是生命的搖籃。
在這個地球上,不論動物還是植物,有誕生,就有消亡。只不過,有的誕生和消亡來自於大自然本身的榮衰代謝,有的誕生和消亡是因為地殼運動造成的山傾地覆。地球史上,曾有四次大冰期,每次都造成物種大滅絕,頑強生存了兩億多年的恐龍,就消失於白堊紀的大滅絕。這樣的荒涼,簡直就是一種不以天的意志為轉移的荒涼。
去年疫情肆虐之際,出版社邀寫一本關於荷花的書。查閱資料的時候,我發現荷花居然是侏羅紀之花。因為就植物而言,太古代與元古代,屬於菌類和藻類時代,之後的古生代,屬於蕨類和裸子植物的時代,再之後的中生代,則是被子植物的時代。裸子植物與被子植物最本質的區別,前者是不開花植物,後者是開花植物。被子植物的誕生,具有偉大的里程碑意義,在此之前,這個地球只有鳥語,從此以後,這個世界才有了花香。荷花是被子植物,曾有科學家斷言,荷花是侏羅紀冰期以前的古老植物,它和水杉、銀杏一樣,都屬於未被冰川噬吞而倖存的孑遺植物代表。就是說,荷花成功地逃過了侏羅紀末日的那一場天劫,以被子植物活化石之姿抱香而來,一直鮮豔地搖曳到現在,讓今天的人類依然能在池塘裡看到花容楚楚。
總之說明了一個事實,地球的形成史是漫長的,地球的荒涼史也是漫長的。而且,那是一種混沌初開的荒涼,也是一種沒有人類參與的荒涼。
荒涼是個哲學問題。因為人類是從荒涼那裡來的。
對地球而言,人類的出現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地球已經轉動了46億年,如果把46億年換算成一天24小時,人類在最後3分鐘才登場。然而,在第四紀末期才顫顫微微站立起來的人類,晚來遲到的人類,不只學會了獵殺和採集,學會了用火和燒製,還學會了種植和馴養,學會了用草藥治病。太陽、月亮、雪山、鷹、獅、狼、樹等等,曾經是人類童年時代的圖騰崇拜,“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更是中國祖先貢獻給人類的自然觀。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荒涼而莊嚴的大自然面前,人類的腳步曾經是輕的,充滿敬畏的,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也曾經是和諧的,美好的。因為人類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肉體生存和精神給養,皆蒙大自然所賜,亦從大自然索取。不是大自然離不開人類,而是人類離不開大自然。
荒涼是一部教科書,讓人類既學會了觀察和思考,也學會了選擇和逃避。
公元4世紀初,中國出現了世界上第一位植物學家,因為他喜歡觀察自然,寫出了一本《南方草木狀》。他是東晉人,名叫嵇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竹林七賢”嵇康的侄孫。
公元18世紀70年代,瑞典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植物分類學家,名叫林奈。他的貢獻是給每種植物都起了兩個名稱,因而被稱為“分類學之父”“植物學之王”。與此同時,法國出現了一位博物學家,名叫拉馬克,是他發明了“生物學”一詞,也是他最先提出生物進化學說,在《物種起源》裡,達爾文還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觀點。
公元19世紀60年代,德國博物學家海克爾最早提出了“生態學”一詞。而在他發明這個名詞之前,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寫出了一部生態小說《弗蘭肯斯坦》,美國作家梭羅寫出了一部生態散文《瓦爾登湖》。
我想,在坐的各位或許不太熟悉《弗蘭肯斯坦》,但大都讀過《瓦爾登湖》吧?如果從1818年瑪麗•雪萊的小說《弗蘭肯斯坦》算起,生態文學已經整整盛行了兩個世紀。
文學有啟蒙之功。因為讀過《瓦爾登湖》,所以在日常的視野裡,當我們看到紛亂無序的車流,看到噴雲吐霧的煙囪,尤其是春運和節日,看到人流擁擠不堪的車站或旅遊景點,所有的人都會有一種急欲逃離的焦慮感,最好逃到曠野無人的地方。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獨屬於自己的瓦爾登湖。
有人說,人類的文明進步有兩大推動力,一是惑然性,二是同情心。於是,因為惑然而懷疑,而有了發現和發明,因為同情而悲憫,而有了關切和關懷。然而,正是因所謂的惑然或懷疑,人類與大自然關係發生了逆轉,由和諧到緊張,由緊張到惡化。
手工被機器取代,機器被電子取代,電子被智慧取代。於是,工業化和後工業化疊代而至,人口數量在不斷增長,土地在逐漸沙化,全球氣候在變暖,海平面在上升,陸地和海洋被汙染,河流減少,草原收縮,再加上地震、海嘯、核洩漏、傳染性病毒等等。災難頻發,猝不及防。
於是,人類的自戕,造成了人類的自失。因為過度的開採,過度的砍伐,過度的消費,大自然的面孔終於由生機勃勃的荒涼,變成死氣沉沉的荒涼。也正是這樣的荒涼,給20世紀生態文學提供了話語空間和話語權力。
1949年,美國作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寫了一部自然隨筆《沙鄉年鑑》。在這本書中,利奧波德建立了一種新的倫理學──大地倫理學,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生態整體主義思想。這部大地倫理學和生態整體主義的開山之作,後來成為綠色思想的聖經。
1962年,美國作家、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寫了《寂靜的春天》,這是世界生態文學和生態運動里程碑式作品。卡森深刻地指出:“我們總是狂妄地大談特談徵服自然。我們還沒有成熟到懂得我們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征服自然的最終代價就是埋葬自己。”
1968年,美國生態文學家愛德華•艾比寫了一部散文作品《沙漠獨居者》,用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作者獨居沙漠的見聞和感受,表達了他對現代化的弊病、唯發展主義、生態整體主義等問題的深刻思考。它再次引發了環境運動的浪潮,1970年,這部作品直接影響了第一個“地球日”的確立。
在全球性的生態文學熱中,中國作家也沒有缺席。我個人曾閱讀過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李存葆的《綠色天書》,張煒的《融入野地》,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等等。生態意識,就是生命意識。同樣,生態危機,就是生命危機。為生態危機而寫作,沒有一個作家會拒絕。
卓別林說,傾聽風聲、樹葉搖曳聲的心,是一顆藝術家的心。
作家用文字和心靈的力量阻止沙化、驅散霧霾、消除汙染,其終極目的,就是讓遍體鱗傷的大自然得以治癒,還荒涼於原始,讓做了殺手而不自知的人類得以救贖,還人性於本真。
人類與自然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只有人類在自然面前退後一步,只有人類透過反哺換來大自然的復甦,這個地球才會重新變成物的母體,人類的樂園。
我希望,中國的青藏高原永遠以它的荒涼之美,高掛在世界屋脊,讓人類頂禮膜拜。
素 素,現居大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大連市作家協會主席、大連市文聯副主席、大連日報高階編輯、大連大學人文學院、大連工業大學外語學院客座教授。其散文《佛眼》獲中國作協“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散文集《獨語東北》獲中國散文學會“首屆冰心散文獎”、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散文集《張望天上那朵玫瑰》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散文集《流光碎影》獲“第二屆新聞出版總署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獎”。個人獲遼寧省首屆“最佳寫書人”獎、“遼寧省第四屆優秀青年作家獎”、大連市政府“文藝最高獎·金蘋果獎”等。現已出版《佛眼》《永遠的關外》《流光碎影》《旅順口往事》等十多部散文集。
美文推薦
散文 | 朱輝:我想與酒搞好關係
散文 | 蘇 北:我和酒的一些關係
散文丨王雁翔:母親的流年
散文丨王雁翔:我的田野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