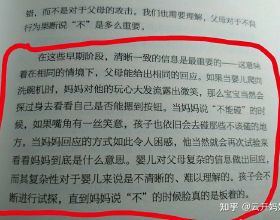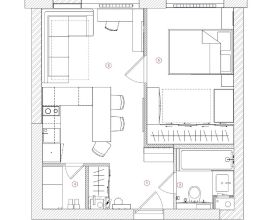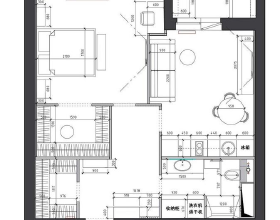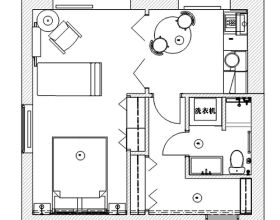郭漢城 資料圖片
【追思】
10月19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著名戲曲理論家郭漢城走完了他104年的人生路。10月25日,郭漢城遺體告別儀式將在北京八寶山舉行。
1917年,郭漢城出生在浙江省蕭山縣戴村鎮張家弄村,從小聽著紹劇與的篤班(越劇的前身)的旋律長大。一輩子都在看戲、評戲、寫戲、研究戲,與戲曲的緣分伴隨了郭漢城的一生。
我國學術界歷來認為,一個合格的學者,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戲曲學科又是一個以舞臺藝術為核心的學科,除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外, 還必須觀千臺戲,聽百種曲,如此才能全面領略我國各地、各民族戲曲的風采,深入戲曲藝術的本體,感受戲曲文化的影響和魅力。在中國,這樣的戲曲學者並不多,而郭漢城是其中之一。在70多年的戲曲研究生涯中,郭漢城足跡遍佈全國各地。他遍訪劇團,廣交演職員,在同時代戲曲學者中,他“看戲最多、戲曲界朋友最多”。常香玉、紅線女、傅全香、馬金鳳、王秀蘭、彭俐儂、石小梅、謝濤、景雪變、馮玉萍、周雲娟、陳俐、蔡瑤銑、王振義、張曼君、盛和煜、周世琮、周長賦、張弘……郭漢城的戲曲界朋友,涵蓋了從20後到80後各年齡段,既有各劇種、各流派的名家大師,也有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90歲之後,由於身體原因,郭漢城外出參加戲曲界活動越來越少。只要有誰上門拜訪,他總要拉著人家的手,讓說說最近又出了哪些新戲,業界有哪些新動向。103歲那年接受採訪時,郭漢城說:“我現在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不能出去活動,但心裡一直想著惦記著戲曲。”
郭漢城是我國著名戲曲理論家、中國戲曲理論民族化體系的重要建立者、中國戲曲現代化的奠基人和推動者,與張庚一起被稱為戲曲理論界的“兩棵大樹”。
作為戲曲理論家,郭漢城反對理論研究“空對空”,主張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有一次,郭漢城跟紅線女聊起“紅腔紅派”。紅線女說自己不懂理論,只不過出於塑造人物的需要而設計了不同的具體唱法,不明白怎麼就出了個“紅腔紅派”。郭漢城對她說:“理論沒有什麼神秘的,都是從實踐中來的,是為指導實踐,不是嚇唬人的。你的‘紅腔’的誕生與塑造新人物的需要分不開。這就是一個理論問題。”
曾擔任《中國京劇》主編的吳乾浩,是郭漢城20世紀60年代帶的第一批戲曲研究生。據他回憶,研究生學習開始後,郭漢城要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看戲,“要跟廣大觀眾一起欣賞,看的時候要進行對比,在對比中去感受和發現”。郭漢城認為,戲曲理論研究者的肚子裡至少要有上千齣戲,越多越好。他經常對學生們說,“只有看大量的戲,你提出的意見才會更實際、更可行”。吳乾浩清晰地記得,研究生三年,他和同學每年至少看200多場戲,“有時候,我們沒錢買票,郭老自掏腰包也要讓我們進劇場”。
郭漢城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大量文藝評論中。他認為,戲曲評論不應是冷漠的“他者”評論,評論家和劇作家、演員要做朋友,評論家對作品既要能入乎其內,體察作者的心聲,又要能出乎其外,給予整體評價。不同於當下一些文藝評論,要麼佶屈聱牙晦澀難懂,要麼泛泛而談缺乏真知灼見,郭漢城的很多文藝評論文章都是膾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絕的美文,其中《蒲劇〈薛剛反朝〉的人物、風格與技巧》《〈團圓之後〉的出色成就》《紹劇〈斬經堂〉的歷史真實與思想意義》尤為人們津津樂道。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傅曉航在一篇文章中所言:“《蒲劇〈薛剛反朝〉的人物、風格與技巧》在筆鋒的磅礴氣勢、邏輯的嚴密、理論的高度等方面達到了極致,可以稱得上戲劇評論的範文。”
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現實中,一些評論家要麼脫離創作實踐,要麼作風浮誇,評論評不到“點子”上,無法讓創作者信服,導致文藝評論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權威性、引導力。郭漢城在進行理論研究和文藝評論之餘,積極參加戲曲劇本創作,先後創作、改編了《蝶雙飛》、《海陸緣》、《合銀牌》(與寒聲合作)、《青萍劍》、《琵琶記》(與譚志湘合作)、《劉青提》等多部作品,這些作品多次被搬到了舞臺上,其中《琵琶記》迄今仍在演出,成為一些院團的保留劇目。因為親自參與創作實踐,所以郭漢城進行文藝評論時,總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創作者的甘苦,而不發空洞的議論,並能夠為創作者提供具體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將理論研究、文藝評論、創作實踐三者集於一身並融會貫通,讓郭漢城成為一代戲曲大家。
2020年10月,中國戲曲學院迎來建校70週年。郭漢城等六位師生代表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了為繁榮戲曲事業貢獻力量的心聲。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給郭漢城等人回信,對他們傳承發展好戲曲藝術提出殷切期望。收到回信,郭漢城十分激動,他說:“戲曲的傳承工作需要一代代戲曲人的努力與用心。”
郭漢城曾許下諾言:“我這一生願意為戲曲事業獻身。”斯人已去。他真正用一生踐行了對戲曲的承諾。
(本報記者 韓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