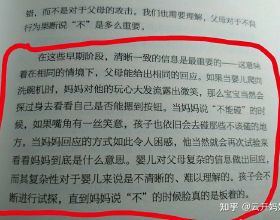我的鄰居胖嬸是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農家婦女。胖嬸個子不高身體粗壯說起話來串聲很高。樸實敦
厚的性格中有點狡黠。
胖嬸還是姑娘的時候因能幹、肯吃苦、潑辣大方而聞名於整個村子。村裡村外對她的說法是褒貶不一,但她卻是樂天派,敢說敢笑,剛才還哭鼻子抹眼淚一轉眼就喜笑顏開,父母常說她是沒心沒肺的人。拽豬草、放牛羊、擔水劈柴、做飯、洗衣樣樣都會幹,都肯幹,甚至比有些男孩子還乾的好。村裡那位裹著小腳的聾奶奶一見她就說:“閨女,地裡喔活是男人乾的,你多做做針線,學著穿針引線。”但她我行我素,一見母親讓她納鞋底子,補個褂子她就找個藉口溜之大吉。後來母親也懶得說她,由著她的性子去,家裡的大事小情她都安排的井井有條,父母親也落個清閒,儼然她在家裡扮演上了管家的角色了。
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上門提親的很多,父母為她物色了一家家境殷實的人家,她死活不願意,愣是看上了弟兄姊妹六七個的王老四,王老四姊妹兄弟七個,他排行老四,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見面就叫老四,慢慢的老四就成了他的名字了。由於弟兄姊妹多,儘管父母沒黑沒明的侍弄莊稼,但生活總顯得緊巴巴,老大的衣服穿小了老二穿,老二沒穿爛老三接著穿,村裡娃們少的幾位家長總說:“咋了呀!一窩窩帶把娃子咋給說下媳婦哩?”儘管老四一家子姊妹兄弟多,但個個身體健康,聰慧過人,勤勞善良,光景過得雖然恓惶但一家人和和睦睦。胖嬸不顧父母的反對堅決要嫁給王老四,婚後的光景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好在胖嬸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熱不怕冷,風裡雨裡水裡泥裡,攛掇著老四沒黑沒明的在地裡刨,愣是把吃了上頓想下頓的光景過得不但有粥喝,還有白麵糕糕饃吃。過好了自己的日子,胖嬸又忙著四處央濟人給錯過結婚年齡的老大找了個寡婦,給老二介紹了自己的表妹做了上門女婿,又給老三張羅娶了個媳婦,原來擔心娃多娶不下媳婦的那些老人又改口了,大家嘖嘖讚歎老四有福氣,娶了個媳婦成就了四個家。老四父母的臉上愁容也變成了笑意,佝僂的也挺直了一些,農閒時候老頭兒揹榜著手喊幾句秦腔。家興出惡犬,老四家的那條黃毛狗也整天背卷著尾巴在村子裡遊蕩,幾隻小母狗屁顛屁顛跟在後面搖尾祈寵。
胖嬸是個苦命的女人。在孃家拉扯著自己兄弟長大,到婆家又牽掛著兄弟幾個的婚姻大事,雖然人面上大家都誇她能幹有本事,但人背後卻是說不盡的辛苦,道不盡的心酸。儘管她能幹但這個家依然貧窮,她操持得依然辛苦,她不曾穿過好衣服,不曾買過雪花膏,做女子時候不愛針線的她婚後學著抹袼褙,照著鞋樣子納鞋底子做鞋,學著裁剪衣服,老四的腳上時常穿著新布鞋,老四的弟兄們也穿著胖嬸納的新布鞋上集趕店,常常招來一些光棍漢的羨慕嫉妒恨,常有人問王老大和王老二:“你兄弟媳婦兒做的鞋穿著舒服吧!你老四媳婦的溝蛋子像個磨盤子,你沒少在上頭踅摸吧!”王老大不甘示弱回敬道:“那是你姑哩,你胡說遭孽哩,小心五黃六月龍把你抓了。”胖嬸每日天不亮就起床,打掃、收拾、下地幹活。春夏秋冬,風霜雨雪,從不曾有一日停歇。看著鄰家翻修房子,胖嬸就開了家庭會議,發動老四弟兄幾個拉土和泥做瓦坯磚坯,冬三個月農閒時割毛梢柴,背麥秸攢夠了柴禾找個燒窯匠裝窯點火燒窯,經過七八個 晝夜不停添柴搭火,等那那泥坯子磚變成通體透亮的金磚時,燒窯匠就會和些泥封住灶火口和煙囪,讓人擔水在窯蓋上澆水浸窯,目的是藉助水的浸滲讓燒紅了磚瓦回性變藍。就這樣今年你家燒一窯磚,明年我燒一窯瓦,老四弟兄幾個翻修了老房子,藍瓦屋面,前門面用磚鑲門鑲窗,儘管還是土牆但在當時也算是趕上了潮流。
再後來,胖嬸給老四生了一兒一女,兩個娃聰慧乖巧,在門跟前的學校上完小學都去鎮上中學了,老四廝跟著村裡的趙發財一起到秦嶺一個叫做樊岔的金礦上打工,由於老四為人良善,做事實誠,不偷奸耍滑,不怕髒不怕累被老闆確定為炮工隊長,負責鑿巖掘進工作。所謂炮工就是利用風鑽機對岩石進行鑽眼,在一塊岩石上鑽出幾十個小孔後,然後在小孔裡填上炸藥,安上雷管引爆將岩石炸裂為小石塊,再靠人力拉兜兜車將碎石拉出。風鑽的動力來自山下柴油機發電產風透過沿山架設的管道把風送到工作面,炮工鑽石打眼時,風鑽噴出的粉塵瀰漫在狹窄的工作面,嗆人辣眼,炮工為了工作方便也不做什麼防護,一個班下來,從頭到腳敷了一層厚厚的粉塵,除鼻子呼吸粉塵外,嘴裡也吃下了不少粉塵,咽一口唾沫都帶著石磨子,覺得磣牙。
雖然老闆每班都給安排一名壓水工,讓老四打溼眼(打鑽時用水衝塵粉),老四嫌麻達,打溼眼粉塵少了卻容易堵鑽眼,耽擱時間,耽擱進度,索性連壓水工都不要了。老闆也急著找到礦脈線,早日採到金子,於是和老四一拍即合,把壓水工的工資一起算給老四,老四也拼命地幹,他既帶班,還打風鑽,每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雖然每天老四打完眼放完炮頂著一頭的石沫,渾身上下的衣服都被水和石沫染的辨不出什麼顏色,雖然每班下來老四他們被石粉沫彌的像電視劇裡的白無常,鬚眉皆白,分不清眉眼但一想到每月的三四千塊錢老四依然咬牙堅持著。老四害怕老闆拖欠工資在和老闆口頭協議的時候就說的清,工資必須月月清,每月掙得錢老四不是讓人捎回去就是透過朱陽的郵局匯回去,有了錢了,老四也成了當地的名人了,房子翻修成一磚到頂的磚房,第一個買了一臺海燕牌彩電,第一個買了碟機,夏天的晚上電視機被抬放在院子,村裡的男女老少帶著小板凳早早坐在院子看電視劇,知道了劉慧芳,知道了姜子牙、知道了妲己、知道了白眉大俠,知道了馬桶、衛生間。
胖嬸不厭其煩,每天晚上給來看電視的發煙倒水散水果糖找凳子,沒有一點傲慢和得意,儘管胖嬸的嗓門更高了,嘴角上翹了,眉毛上揚了,但更有向心力了,話語有了權威了,成了村裡紅白喜事內圈的總管,村裡的女人們常常數落自家的男人沒本事,窩囊廢,常常羨慕的看著胖嬸上集趕店、吃筵喜趕滿月穿的新衣。時不時礦上的老闆開著大溝子北京吉普送老四回來,孩子們趁沒人的時候看稀景一樣圍著吉普車嘖嘖讚歎,摸摸這裡,摳摳那裡,滿滿的羨慕,就連大人們也滿眼的羨慕嫉妒恨。
老四的父母也格外受到村裡人尊敬,村裡的大小矛盾家長裡短只要老四的父親出面沒有解決不了的,老四一大家子成了村裡的望族。村裡人都說胖嬸命好,笑容就像花兒一樣綻放在胖嬸的臉上。
雖然每天都在吃石沫子,雖然每天都在瀰漫的粉塵中工作,雖然每天被石沫浸蝕的人模鬼樣,但每月能掙三四千元,比起其它打工的收入高多了,所以老四拼命地堅持下去。在金礦上幹了差不多5年的時間,那一年剛立冬,老四幫忙胖嬸種完麥子就被老闆的大溝子車接走了,到了礦上老四沒幹幾班就突然胸痛、咳嗽,同時感到四肢無力,氣短。老闆親自開車送老四到靈寶中心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老闆並沒有告訴老四,交了住院費給老四留了些生活費就走了,一個月後老四覺得輕鬆了不少,就給老闆捎信說他要出院,老闆很快就把他接出院,並送老四回家,讓他休息兩個月再到礦上去。老四也就回家休息了,到了第二年春天老四覺得呼吸更困難了,走幾步就氣喘吁吁地,胸悶的厲害。於是就到西京醫院檢查,被確診為矽肺,大夫告訴老四這病難治,要好好休息,儘量不要感冒。老四到處打聽也終於知道病根是當炮工落下的,幾乎無藥可治,活著也是行屍走肉,只能慢慢等死。
胖嬸也多次催促老四住院治療,但老四就是拽著溝子不去,老四心裡明鏡似的,明知道去醫院是人財兩空,他不願把用命掙回來的錢送進醫院,所以不管誰再勸說他都不為所動,每天在咳嗽氣喘中煎熬。胖嬸雖然臉上還掛著笑,但眉宇間隱隱露著憂愁,說話的嗓門也低了許多。
胖嬸除了憂扯老四的病情,還憂扯兒子的婚事。兒子大專畢業沒找下固定工作在外漂泊,事業和婚事也是胖嬸極為在意的問題。孩子已經三十幾歲了,卻還是沒有合適的結婚物件。老四焦急,胖嬸更焦急,四處託人求人介紹,說了一個又一個,結果都沒了結果。胖嬸責怪兒子太挑剔,兒子總說他媽多管閒事。老四站在老婆這邊,也數落孩子的不懂事,奈何他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只能唉聲嘆氣,胖嬸也無可奈何,只能背過人偷偷地抹眼淚,只能求神打卦祈求孩兒早點找到物件。然而,胖嬸一次次滿懷希冀,一次次失望嘆息,她只能在希望與失望中憂慮著,等待著,在夜深人靜時刻以淚洗面,在柴米油鹽的日子裡煎熬著,在怒懟老四的惡聲惡語中消怠時光。
老四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妻子和孩子的累贅,一心求死奈何死神只是折磨他、揉搓他,不讓他痛快,不讓他解脫。老四也設計過各種死法,想過老鼠藥、想過上吊、想過跳河但一想到孩子還沒有成家,怕給孩子留下瞎名聲,找不到媳婦,只好放下各種結束自己的想法,在胖嬸的數落中、在胖嬸的白眼中、在胖嬸的搡打中、在胖嬸的恨死恨活的責罵中度日如年,在自己出氣就像拉鋸的喘息中苟且偷生。胖嬸儘管堅強,但她終究是個女人,還是一個辛苦的女人,她流淚、她哭,她把眼淚流在人後,把堅強放在人前,過多的憂愁使她的烏髮變的灰白,粗壯的腰桿變得佝僂,倔強的臉上瀰漫著滄桑,幹練的性格變得有些幕囊。
已經適應了胖嬸的白眼和籮篩的老四在臘月的一個夜裡靜靜的去了,胖嬸早上發現的時候已經手腳冰涼了,硬挺挺的躺著,臉呈青紫色,手指甲把胸口抓出了幾道血痕。老四的屍體停放在他親手修建起來的磚房正當間,他仰面朝天躺在反面朝上的沾滿了灰塵的棺材蓋上,頭下枕著半截胡基,臉上苫著一片禾紙,老四衣服和嘴之間連一截紅毛線,毛線一頭系在老四的衣釦上,另一頭穿著三個麻錢塞在老四的嘴裡,腳上穿著胖嬸做的從未粘土的新布鞋,雙腳被一截草繩捆攏著,身上蓋著緞被子,身下鋪著綢褥子。一張條桌放在屍首的前面,桌子上蹲放著一個裝滿沙子的罐頭瓶充當的香爐,三根燃了半截的香冒著幽幽的輕煙,煙柱打著旋旋嫋嫋升向空中,順著房梢眼飄出屋外,飄入廣袤的宇宙,散的無影無蹤,快掉下的香灰倒向一邊像歪脖挒項的老四。左鄰右舍的男人們幫忙運磚拉沙箍墓,女人們蒸饃做飯炒菜,老四的一生就在嗩吶的嗚咽聲中畫上了句號,胖嬸也終於卸掉了壓在心頭的一個包袱。
老四死了一年後,在西安打工的兒子電話告知胖嬸,他要回來結婚。胖嬸熬煎沒有錢、熬煎房子陳舊了,熬煎的整宿整宿的睡不著覺。兒子卻說不讓他管,給她轉了五萬塊錢讓她把房子簡單收拾一下,換張新床。胖嬸歡天喜地通知至親厚鄰,忙著扯蓋頭,納棉被、裝新房。國慶節前兒子和岳父一家七八口人回來了,胖嬸看到隨兒子一起進門那位姑娘,彎彎的柳眉下長著一雙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微微地顫動著,白皙無暇的面板透著淡淡的粉紅,薄薄的嘴唇塗的猩紅,胖嬸驚得張開的嘴半天合攏不了,這麼漂亮的姑娘她只在電視裡看見過,兒子竟然把她娶回家,她心裡直嘀咕不知是哪輩子修來的福氣?是不是死去的老四地下有靈保佑的結果。家裡住不下兒子就在街道的悅來賓館給媳婦孃家人開了幾間房,胖嬸聽不懂親家的普通話,全憑兒子和兒媳給翻譯。婚禮在老四的老家撲鴿窯舉行,胖嬸坐在鋪著紅緞被子的長凳上淚眼婆娑的聽著兒媳婦改口叫媽,司儀絮絮叨叨的走完了程式,客人們在鋪著紅色檯布的餐桌上風捲殘雲。送走了高朋厚友、付清了流動餐桌的費用、打掃完院子的垃圾胖嬸才有空向兒子打聽兒媳的情況,原來兒媳是獨生女,父母開了一鋁製品工廠,家產幾個億,兒子大專畢業後在社會飄蕩了幾年後,沒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個同學介紹他到這個鋁廠打工,是在廠裡打工時認識的媳婦,兒子的勤懇和憨厚引起了廠長千金的注意,聊著諞著擦出了火花,姑娘死活要嫁給兒子,拗不過女兒的父母只有同意了,但要求胖嬸的兒子必須在西安買房,看到胖嬸兒子的窘況瞭解了家庭情況後他岳母全款在西安曲江帕提歐給他買了一套200多平米的四室房,他岳父給他一輛奧迪Q6,讓他跟隨銷售經理熟悉業務。兒子說結完婚他要趕緊趕回去,廠裡的業務他要儘快熟悉,讓母親一個人照顧好自己,有合適的再找一個老伴。
胖嬸聽了兒子的情況後,不僅涕淚滿巾,她為兒子有了好歸宿而高興,她更為兒子的孝心而感動,壓在她心頭的兩座大山終於都卸去了,她似乎覺得走路都飄飄的,佝僂的腰身又挺起了,凝在胖嬸眉頭的那憂愁煙消雲散,笑容再次在胖嬸的眉間綻放。
結完婚,兒子給他的舅舅、姑姑、姨們每人發了500塊錢的紅包,兒媳婦又給胖嬸留了一張卡,並叮囑她卡的密碼是胖嬸的生日,裡面有2萬塊錢,想吃啥就買啥,別太虧欠自己。兒媳婦的一番話惹得胖嬸眼淚漣漣。把兒媳婦的手握了再握,親家母也拉著胖嬸說讓她把家裡收拾收拾去西安住,胖嬸高興的點著頭,像雞啄米一樣。忙完了兒子的婚事送走了七姑八姨,胖嬸的生活又恢復如前,老四在世時雖然惹她煩,但還有發火的物件,還有出氣筒,煩了燥了可以衝老四撒撒氣,可以向老四訴訴苦,現在老四走了只留下四面潔白的牆壁,雖然每天街道車水馬龍,人流如雲,但一到晚上胖嬸不得不蜷縮回自己的屋子,躺在暖和的土炕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滿腦子都是兒子那句:有合適的再找一個老伴。
小半年過去了,洛書廣場跳廣場舞的人群中有了胖嬸的身影,一位喪偶的吃公家飯的摟著胖嬸在《你是我的人》的音樂聲中笨拙的舞著。胖嬸的美好春天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