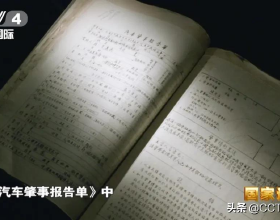前言
日軍在中國土地上的殘忍暴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只有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做不到的。
而日軍的暴行,除了在憲兵隊對待被抓捕的抗日誌士,以及在掃蕩的過程中對待普通百姓以外,更是在全國各地的戰俘集中營有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對日軍來說,殘暴是一種生活方式,殺人是他們的嗜好。
景雲祥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普通士兵,1944年豫中戰役被日軍毒氣毒暈後成了日軍的俘虜,先是被送進洛陽的西工集中營,在那裡經歷了一年的地獄般的折磨後,於1945年1月他同500多名戰俘被轉運到濟南的新華院戰俘集中營,直到日軍投降,作為倖存者之一的他回顧了在濟南新華院近半年多的非人生活。
新華院戰俘集中營
濟南新華院常年關押戰俘勞工達二三千人。凡被關進新華院的俘虜,以化驗為名,每人先要抽200CC血,然後再進行預審。名為預審,實為摧殘。在預審時找種種藉口,對俘虜施以種種酷刑:吊、打、燒、燙、往嘴裡灌煤油,手指縫裡釘鋼針。
預審室裡,從早到晚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不斷。那些受審的戰俘,有的被打遍體鱗傷、血肉模糊,有的雙手被燒得焦黑,有的人被打成了殘廢,有的就此而喪失了生命。
為防止戰俘逃跑,預審過後再把這些人關進又黑又臭的禁閉室,既不給吃,也不給喝,直把人餓得頭暈眼花,折磨得氣息奄奄,別說逃跑,就是連抬頭、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有的戰俘沒等被放出禁閉室,就已經進了鬼門關。
預審和關禁閉,這僅僅是集中營生活的開始,更大的苦難還在後邊。
被關進新華院的人,不僅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就連生存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他們完全過著非人的生活。每天要從事十幾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劈山開石,挖溝築牆,修建軍事工程。而吃的卻是摻有砂子的高粱麵餅子,咬一口直硌牙, 不敢對牙,不敢用力嚼。開始摻砂子少些,到後來越摻越多,叫人們吃不下,吃下去也消化不了,就這樣慢慢地消磨掉戰俘們的生命。
可是為了活命,吃不下也只得硬著頭皮吃,囫圇吞棗似地往下嚥。即使這樣的餅子也不讓吃飽,每頓飯只給一個,不足2兩。兩個人一碗菜葉湯,沒油缺鹽,清淡得不如普通人家的刷鍋水,毫無營養價值可言。
雖然每天要從集中營里拉出幾十具屍體,每隔一兩個月就有一批戰俘被送往東北等地服苦役,但集中營裡依然是人滿為患,一棟牢房裡要關押進100多人。
晚上人們像匙子似的一個挨一個側身臥在床板上,既翻不了身,也蜷不了腿。這個姿勢時間太長使大家腿背發麻時,有人會喊“翻身!”於是大家同時翻身向另一側躺,有時旁邊那個人不翻身——他已停止了呼吸。
至於衛生,在集中營是一個根本談不上的問題。牢房裡陰暗潮溼,滿地汙垢,如同牛圈一般。
在集中營裡,只要你還活著,捱打和折磨是常有的事。只要日本人認為你有“不軌”行為,就要受到處罰或施以酷刑。
輕者被扒光衣服令其爬煙囪,爬不上去弄下來就是一頓毒打。 有時讓俘虜頭頂石頭繞場轉,誰要撐不住或中途石頭掉下來,就會被打個半死;重則關禁閉或被狼狗咬,割耳朵、活埋等等。集中營禁閉室裡,埋有特別的十字木樁,日本兵把戰俘捆在十字架上,當作活靶練習刺殺。
在集中營東院,日本人養著一群狼狗,這些警犬日夜叫嚷,震撼著整個集中營,令人毛骨悚然。
一次集合站隊,一個叫王學安的戰俘動作慢了點,日本兵用手一指,那狗立即撲了上去,兩隻前爪搭在王學安的肩上,吐著血紅的舌頭,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狗嘴裡的白色氣浪一股一股地噴到王學安的臉上,嚇得他大氣不敢出,一動不敢動,可腿卻止不住篩起糠來。
這時日本兵一聲令下,那狗上去一口,咬掉了王學安的半邊臉,日本兵又拍拍手,那狗咬住王學安的手,搖著頭用力咬,日本兵指到哪兒,狗就咬到哪兒,直把王學安咬得血肉模糊,慘叫不已。日本兵把他折磨夠了,最後又拍了拍脖子,那狗上去一口,咬斷了王學安的喉管,最後他連叫都叫不出聲,只挺了挺身子,便死去了。
對戰俘這種慘無人道的摧殘,時時都可能發生。當時新華院附近的居民院,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從新華院內傳出的悽慘叫聲。
逃跑者的厄運
李金田原在濟南市萬盛街的一個工廠做工,被日本人抓進集中營後,受盡了酷刑和凌辱。李金田他們看到同牢的難友一個個倒下去,不是被日本人殺死、打死,就是被餓死、凍死,他們預感到難友們的今天也就是自己的明天。
“得想辦法逃出去,不能在這裡等死!”
在廁所裡李金田看看左右沒人,悄悄地對景雲祥說。
景雲祥警覺地四下看了看,點了點頭。又說:“怎麼出去呢?”
“我想好了,明天鬼子不是還讓我們去修公路嗎,路西邊不遠處有一片高梁地,只要闖過從公路到高梁地之間的那塊開闊地帶,進了高粱地就好辦了。”李金田說道。
當晚,二人想辦法分別通知了另外3位難友。
第二天100多名戰俘分佈在大約50多米長的公路兩側,從路邊挖土扔到路面上,修完一段向前移動一段,30多個日本兵端著槍虎視眈眈地在工地上轉來轉去。
李金田等人從集中營一站隊就站到了一起,這樣便於統一行動。但是景雲祥被一個鬼子指派到離他們較遠處幹活。此刻李金田等人極力抑制著心中的興奮和恐慌,一邊幹活,一邊暗暗觀察著。可站在他們旁邊的鬼子往前走三步,後退五步,一直沒有離開過。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李金田他們始終沒有找到機會,互相看著,個個心急如火。
這時前邊有個日本兵在喊,並掏出香菸對著李金田他們旁邊的鬼子井田晃了晃,招呼井田過去抽菸。
機會來了!李金田低低的一聲 “走!”4個人扔下工具,撒腿向西跑去。可就在此時敵人的槍響了,一個難友剛跑出路溝,就被打中,他又趔趔趄趄向前跑了幾步,便倒了下去。
狼狗竄了上來,咬住了跑在最前邊的兩個人。
日本士兵圍了過來。李金田回頭看了看難友們,大家臉上都很平靜,在跑之前他們已經預料到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所以大家都能泰然處之,要殺要砍由他們去吧,幾個人都在這麼想。
窮兇極惡的日本兵看他們不卑不亢的樣子,更為暴怒,用鐵絲穿過他們的手心,把他們吊在路邊的樹上,一頓槍托打得他們像鐘擺一樣盪來盪去。日本人一邊打一邊衝其他戰俘們喊:“看到沒有?這就是逃跑的下場!”
打夠了,又把他們幾個人放下來,由3個日本兵押著到了西山下,命他們每人挖一個坑,然後指著李金田:“下去!跳下去!”
“弟兄們,再見了!”李金田與難友們道別,從容地跳了下去。難友們看著坑中的李金田,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埋!”日本人命令道。
難友們誰也不肯動手,他們不忍心親手埋掉自己的弟兄。“埋!”日本兵的刺刀對著他們的後背。
還是沒人埋土。
“噗!”地一聲,日本兵刺倒了一個難友。
“幹不幹?”日本兵兇殘地吼叫著。
“噗、 噗!”另兩個難友也倒在了李金田的坑沿上。 李金田緊握雙拳,牙齒咬得格格直響,血紅的雙眼憤怒的盯著日本兵。
日本兵親自動手了,一鍁一鍁地把土扔進坑裡。土已掩到腹部,李金田開始呼吸困難。當土掩到胸口時,李金田已憋得臉色青紫,張著嘴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這時,一個日本兵擺手示意停止埋土,他抽出身上的戰刀“嗨”地一聲,手起刀落,李金田的腦袋被砍了下來,鮮血從脖於上竄出去有一尺多高。
在這壁壘森嚴的魔窟裡,要想逃出去談何容易,人們一次次逃跑,一次次被抓,伴隨而來的是一次次慘無人道的摧殘和屠殺。
一句小聲的抱怨換來雪地裡被罰跪一天一夜
景雲祥他們被送進新華院時正值寒冬臘月,戰俘們腹中無食,身上衣單,腳下又無鞋無襪。日本人並不因此而停止對戰俘的役使,深挖集中營周圍的封鎖溝成了戰俘們每天的必修課程。
為防止戰俘逃跑,新華院周圍挖有2米多深的塹壕。夏天這裡面的水有一人多深。冬天水逐漸下滲,剩下一尺來深的水已結成了冰,日本人每天驅趕著戰俘們跳進溝裡,先把冰砸開,扔上去,然後再把溝加寬、加深。
人們的指令碼來就凍得又紅又腫,有的生滿凍瘡,膿血直流;有的裂著口子,一踩到冰碴子上,猶如踩在萬枚鋼針之上,刺骨地冷、鑽心地疼。從小腿到膝蓋,全變成了青紫色。有的雙腿凍得失去了知覺,倒在水溝裡;有的甚至被凍掉了腳趾頭。
整個冬天都是這麼過來的,一直捱到了春節。
“明天是大年三十,日本人還不給兩天假嗎?”李永泰一邊把凍得又紅又腫的雙腳壓到大腿底下取暖,一邊憂心忡忡地說:“再這樣下去,我這雙腳也要保不住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搓著失去知覺的雙腳。
“哎,日本人哪是讓我們幹活,他們存心是在折磨我們,他們肯發那樣的善心嗎?”景雲祥說道。
“看,下雪了!”不知誰喊了一聲。
“好大的雪!”景雲祥抬頭向外望去。不知什麼時候,天空飄起了鵝毛大雪,一切的一切都混淆在白色的旋渦之中,只有圍牆上的崗樓還依稀可辨。
“睡吧,雪這麼大,明天可能不讓幹活了。”
李永秦抱著希望進入了夢鄉。
“起床,起床,統統地去掃雪!”日本人穿著過膝皮靴,把頭縮在皮衣的領子裡,揮舞著木棍叫喊著。
景雲祥從睡夢中驚醒。揉揉眼,天剛矇矇亮。
“這麼大雪還讓幹活!”李永泰一邊往起坐一邊小聲嘟噥著。
“啪!”冷不丁一棍子打了過來,李永泰倒了下去。日本兵又一把把他抓起來,一腳踢出門外:“幹活的有!”
朔風刺骨,雪還在紛紛揚揚地下著。地下積雪已有一尺多厚。開始人們還知道冷,漸漸地雙腳就失去了知覺。等抬腳向前邁動時,腳下竟凍結著一大塊雪疙瘩。
大家幹活很賣力,因為不敢停下來,一是有日本人的木棍時時在盯著你,更重要的是要靠多幹活、多出力來獲取一點熱量,不至於凍死在這冰天雪地裡。
李永泰剛才肩上捱了一棍子,腰上被踹了一腳,現在右臂抬不起來,腰疼得彎不下去,這個樣子讓日本人看見,一定又是一頓毒打。景雲祥等幾個難友悄悄地把他圍在中間,不讓日本人發現他幹得慢。
“開飯了!”值日戰俘把飯抬進了牢房,大家簇擁著李永泰向牢房走去。
剛走到牢門口,剛才打李永泰的那個日本兵伸手把他揪了出來:“你的,不許吃飯!”並令他跪在雪地裡,看著大夥吃飯。日本人在懲罰戰俘方面是從不手軟的。
一個上午過去了 ,李永泰被罰跪在雪地裡;下午又過去了,李永泰還跪在雪地裡。
直到第二天他們被日本兵急促的呼喊聲叫醒的時候,李永泰還沒有回來。
大家忙出去找,就在昨天上午罰跪的地方有一堆雪,走近一看,是人!大雪把李永泰埋了起來,他被凍僵了!
牢房裡,難友們緊張地忙碌著。景雲祥脫掉還帶著體溫的開花棉襖,緊緊地裹住了他。有人抓起他的雙腳放在自己的胸前,有人把他的手塞進自己腋下,大家都熱心地操持著,像對待自己的親兄弟一樣。
大家焦急而又細心地觀察著任何一點有關生命的訊號,等待著他的轉機。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 過了好長時間, 他的呼吸慢慢均勻起來,並且越來越深,隨後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眼球轉了轉,他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周圍,向大家瞥了一眼,就又把雙目疲倦地閉上了。
他顯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對現在的處境還茫然不知。李永泰又一次睜開眼後,才認出了周圍熟悉的面孔,等他明白了一切之後,眼淚像小溪一樣,無聲地淌了下來。他試圖把手從難友的腋下抽出來,難友卻把它挾得很緊;他想把腿蜷回來,可它不聽使喚,一動也動不了。
今夜是除夕。
節日的氣氛在這裡永遠是沒有的。與往常一樣的飢餓、一樣的寒冷、一樣的勞役、一樣的殘殺、一樣的死亡。
牢房裡死一般的寂靜。沒人出聲、沒人說話,甚至連咳嗽都沒有。
不一會兒從牢房的一頭,傳來了低低的抽泣聲,聽得出哭者在極力壓抑著,但還是不能抑制住悲痛,抽泣聲越來越大,而抽泣的人也越來越多,整個牢房一片唏噓之聲。
悲傷的傳染性極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傷心之事:為母親失去了兒子、為妻子失去了丈夫、為孩子失去了父親、為身陷囹圄而壯志難酬、為這難捱的苦難,為不可知的明天,為生命的短暫。
人們越想越傷心,抽泣變成了哭聲。
“別哭了!”
有人嘶啞地喊道。想必他也剛哭過,可能是剛擦乾了眼淚。
“我們決不能讓日本人看笑話!我們大家要團結一心,互相照顧,要學會保護自己,只要我們能活下去,這就是勝利!”
大家一聽,確實是這個道理:既然被關了進來,又逃不掉,哭又有什麼用呢?立時哭聲漸低,抽泣聲漸小。
可是第二天早晨,新華院又有60多人被凍死在牢房裡,沒能見到初一的太陽。他們走了,滿懷著生的希望。
結語
死者已已,而生者悽悽。在這些戰俘中,到底誰是幸運的?是已經死去的還是暫時活著的?
哪個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哪個人不期望著生命的輝煌?然而在集中營裡,對他們的生殺大權全掌握在日本人手裡,誰能主宰了自己的命運?除了抗戰勝利,又能到哪裡去尋找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