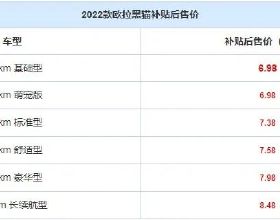圖片來自網路
從溫暖如春的網咖出來正是夜深人靜,寒月高照時分,灰白的街上除了西北風的呼嘯,只聽到自己的腳步。
我像往常那樣縮著頸子埋頭走路,肚子時不時骨碌碌響一通。再看那兩隻腳,踩著月光,一前一後起落,活像離了我也會自動前行。
一個黑乎乎的毛團憑空冒出,閃電般朝腳下滾來。我倒退兩步,忽然想起那不過是隻黑色的,有著一雙黃熒熒的、不懷好意的眼睛的家貓,昨晚就遇上過。見了我像見了親爹般歡天喜地,蹭著褲腳嗅來嗅去。
拎起它正待端詳,它不失時機地舔了舔我的手。便覺得有些蹊蹺,說是誰家養的吧,這時辰還滿大街亂跑。說是流浪貓吧,卻戴著個挺精緻的項圈。
稍稍躊躇後我決定帶走,左不過喂點兒殘羹剩飯,哪天抱去早市,保不齊還能賣幾個錢。
租住的斗室裡冷得像個冰窖。我把貓扔在地上,順手開啟電熱褥。它倒一點兒不生分,縱身一躍上了床,又打呵欠又抻懶腰,像回到自個兒的家。
肚子卻一發地餓,搞得我心煩意亂。四處翻騰了一氣,尋出半盒吃剩的盒飯。嗅了嗅還沒餿,便從床下拎出燒酒瓶子,就著剩飯對付了一頓。
再看那貓,已然盤做一團打起呼嚕,一副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德行。
我推開它,鞋都沒脫和衣躺下,望著天花板歸整了一會兒心思。房費,飯錢,我的詩……該操心的太多了,一時半會兒理不出頭緒,後來就睡著了。
夢裡有人說我中了諾貝爾文學大獎,還是頭等獎。要我趕緊備齊身份證、暫住證、六張一寸白底免冠彩照,我的詩歌一式三份也得打出來。為此政府安排了專機,許多官員、專家、美女都在機場,候著陪我出國領獎。別的好說,一式三份的列印很費了些時間,影印店的夥計忙出了一頭汗才打完一半,說話間印表機又壞了,飛機也飛走了。
一股郁烈的酸臭把我燻醒,右腳冷得要命。下意識想揉眼睛,胳膊卻動不了。努力睜開眼睛一看,禁不住大吃一驚。
身體還躺在床上,渾身上下卻被打行李用的那種黃蠟蠟的膠帶紙纏得像個木乃伊。右腳的鞋沒了,腳趾像五隻白色的蟲子在寒氣中痙攣,猴年馬月沒洗過的一隻棉線襪子正塞在我嘴裡。
“真不好意思把您弄醒了,”一個溫和的,猶如春風掠過麥田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您熟睡的樣子就像個嬰兒。不過既然咱們還有正事要辦,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使勁轉過臉,看見一個年輕女人笑嘻嘻站在床邊。雪白的臉子,同樣雪白的頸上,一條做工精緻的項圈閃閃發光。她穿著身黑色競技滑雪服,個子比天生又矮又瘦的我高一頭不止,凹凸有致的身材在緊繃繃的布料下凸顯無遺。
她伸出手,按住草地上的魚一樣甩頭擺尾的我,柔聲地說,“您完全沒必要這樣,我對您全然無害。只要您保證不亂蹦亂喊,我會拿掉您嘴裡的襪子。”
她的手勁兒大得驚人。
我忽然想起什麼,朝另一邊轉過臉。
果不其然,那隻貓不見了。
“猜得不錯,您真夠聰明。”她含笑點頭,“咱們還有正事要辦,就別耽擱時間啦。您可想好了,是採納我的提議,還是怎麼的?”
她兩次提到的“正事”不能不教我浮想聯翩,沒準撞上了湖州宗湘若先生那樣的好運也未可知。話說回來,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不拒絕狐狸、狸貓、烏鴉、鬼魂各路大神變成的漂亮女妖。至於何以把我捆成個粽子,她是不是偏好SM,只有天知道。便不再急於脫身,肯定地點點頭。
襪子拿掉了,我長長噓了口氣,正要開口,又被她捂住了。
“我知道您有問題要問,憋會兒吧。這會兒我問您答。您放心,問完我會把一切都告訴您。”聲音依舊那麼親切,手勁兒依舊那麼大,儘管疑慮像老鼠在心中啃噬不休,我還是同意了。
她似乎對這麼容易便制服了我很開心,咧開嘴笑了,露出一口銳利的小牙。
倘我的記憶沒錯,她應該有八顆犬齒,六顆切齒,十四顆臼齒,攏共二十八顆牙。
“您是個大作家,對吧?”她開始問。
我有些不好意思:“這個,呃,暫時還不能這麼說。作家,詩人,寫手,文學青年……本質上一樣兒一樣兒的。你知道,我不在乎那些虛名。”
“可您的群裡都這麼叫啊,還是怎麼的?”她似乎有些驚訝“我查閱過別人的跟帖,有說你爐火純青的,有說路遙轉世,顧城再生的,有說後現代巨星,天生諾貝爾得主的,說的是您吧?”
“粉絲的追風之詞多的去了,我從不留心那個。”我做出漫不經心樣子,一邊打量她詩一般的身材,“你若也想走上文學的道路,我可以收你做徒弟,做為特例不收學費。”
“這就對得上號了。”她似乎很滿意,“您能不能說說,您的腦子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怎麼就想得出那麼多了不起的文字?”
“你說的對極了。有人解剖過愛因斯坦的腦子,確實與常人不同。我們這號人的腦子,靈感就像雨後的蘑菇俯拾皆是,洋洋萬言不費吹灰之力。自然也少不了勤奮,您應該知道,我師從的是艾略特、波德萊爾,中學起我就筆耕不輟,至今已寫下七百萬字的文章。”
“可以出個題目考考您吧?”她若有所思地望著天花板,“小說太費時間,您就寫首詩讓我聽聽,隨便寫什麼都成。”
“小菜一碟。”我一下子高興起來,“那我就不推辭了,寫一首情詩獻給你吧。拜託先鬆鬆綁,這麼著實在沒法子用筆。”
“您直接唸吧,我只是聽聽,看您是不是在吹牛。”
稍一沉吟我立馬念道:
“篝火思念著白馬,
帳篷遙望著斗篷,
奶茶等待著騎手。
是你來,還是我去?
只等你一句話。”
“完了嗎?”她似乎意猶未盡。
“只要你樂意,十首百首立等可取。”
“確實不同凡響,比我們老大好一萬倍。我答應過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訴您,完了就辦正事。”
“辦完事再說也來得及,咱們有的是時間。”我含笑道。
“那怎麼成?”她似乎有些驚訝,“言而有信是我的一貫原則。”
真太孩子氣了,我不以為然地搖著頭想,回頭一定要把做大事不拘小節等道理好好和她說道說道。
“我們老大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比馮小剛演的老炮兒牛逼多了。”她伸出大拇哥做了個手勢,“現而今功成名就,錦衣玉食自不必說,徒子徒孫哪個小區沒有?
“不知咋的他老人家突發奇想,決心做一樁名垂竹帛的大事。您猜得到嗎?”
“還真猜不到。”我心不在焉地答道。
“老大說了,縱觀歷史,古而今王侯將相皆寂寞,唯有作家、詩人留其名。決心在有生之年傾其所有,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蜚聲海內外的大詩人、大作家,還要拿諾貝爾獎。您覺得有可能嗎?”
“草莽英雄打打殺殺也許是把好手,詩人、作家可不是什麼人都能當的。”我傲然道。
“說實在的,我對文學毫無興趣。在我眼裡小說啊,詩歌啊什麼的,全是些不當吃不當喝的狗屁。私下說一句,就讓作家、詩人五六兒的通通見鬼去吧。
“但他究竟是我們的老大啊,暹羅貴胄,又牛逼,不聽他哪兒成。
“於是買來最貴的電腦,連上最快的網線,置辦了一屋子中外名著,高薪招來幾十號詩人、作家、評論家、教授,手把手教。
“自此老大閉門謝客,潛心鑽研了兩個年頭。錢花了無數,寫出的東西依然差強人意。老師們託了學生的關係一篇篇送到報社去,發表是發表了,印出來只豆腐乾大小。
“於是一天到晚悶悶不樂。
“後來把我們全轟出去想辦法,終於按小廣告上的地址請來個退休老軍醫。望聞問切後下了方子,藥引卻有些蹊蹺,非得詩人、作家腦子不可。醫生說了,吃什麼補什麼。”
她停下來打量我的腦袋。
“我看您挺合適。”
我覺得有些不妙,趕緊打斷她說那醫生純是個江湖騙子,是瞎掰,是迷信,是犯罪。再說了,我還不是個作家,除在網易、新浪部落格、天涯紅袖論壇上傳過幾篇胡謅的東西,正經沒發表過一篇。
她可不這麼看。
“試著吃了幾服,老大頓時才思大進,下筆也有了精氣神兒。您剛才不是說過,作家,詩人,寫手,文學青年……本質上一樣兒一樣兒的嗎?我看您是謙虛,是想推辭。”
“即便非要腦子,”我急赤白臉地喊,“莫言、賈平凹、鐵凝、王安憶……我可以為你拉出個名單來,全是如假包換的大文豪。你不能捨肥甘而啜糟瀝,揪住我就不放呀。”
“這不正和您商量嘛。醫生關照了,天資聰穎,尚未功成名就的腦子藥效最好。只有這種腦子才是鮮活的,急切的,進取的。一旦功成名就,就失去了當初的活力,變得瞻前顧後、甘於守成,做引子就不好使了,吃了也補益不大。”
我急得想給她作揖,雙手又被捆得動彈不得,眼淚像珠子般滾滾而下。
她的眼裡掠過一絲同情,俯下身,柔聲細氣地勸道:“現而今您缺衣少食,往前看路也是黑的,死乞白賴再活下去真沒多大意思。再說了,您的命能為中國文學事業做出貢獻。拔一毛而利天下的好事,您怎麼就不肯呢?”
她一邊說,一邊抄起一把看來早就備好的西瓜刀,一條裝化肥用的編織袋。
原來這才是她要辦的正事。
正待張口呼救,那雙雪白的纖手已不失時機地把臭襪子填了進來。黯淡的燈光下刀光一閃,我的腦袋撲地落進編織袋裡。一道魂魄打脖腔逸出,氣球般扶搖而上,停住在天花板下。
我想大哭,又想嚎叫,卻發不出一絲聲息。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抖抖身子又變做黑貓,叼起地上的編織袋,扭呀拐呀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