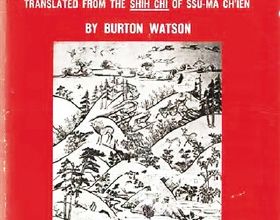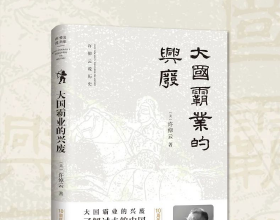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觀點,被公認為傳統史學之極則。錢穆稱之為“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但史公三句中“究天人之際”一語的確指究竟何在並不明確。對此,錢先生認為:“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他將“際”字明確對應為“分際”之“際”。我們認為錢先生的思路是正確的,事實上也已經把理解“究天人之際”句義的關鍵線索指出。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今試略論之。
後世多以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全為史公獨創,實則前人就有類似的說法。《史記·儒林列傳》載公孫弘奏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此處,“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二句極類似,其淵源關係是顯見的。那麼“明天人分際”是什麼意思呢?《漢書·儒林傳》亦載有公孫弘這一奏摺。幸運的是,彼處“分際”之“分”有“師古曰”一則,保留了其讀音:“‘分’音扶問反。”
檢《廣韻·文韻》“分”小韻:“分,賦也,施也,與也,《說文》:‘別也。’府文切。”《問韻》“分”小韻:“分,分劑,扶問切。又方文切。”按照顏師古注音,此處“分際”之“分”乃去聲問韻之“分”。我們認為顏師古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一點可以從下列文獻得到印證。《文子·上義》:“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淮南子·泰族訓》:“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二條中“分”字皆應讀去聲,意為“職分”。《文子》一句下文有“守職明分”一語,義尤顯豁。至於《淮南子》一則,後文分別講“天之所為”“人之所為”,可知其“明於天人之分”的“分”也是“職分”之“分”,即“所為”也。這兩則材料中的“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顯然對應於公孫弘奏摺中的“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可知顏師古對“分際”之“分”音義的理解由來有自。
循著這一線索,再來看《淮南子》與《文子》“天人之分”的說法,文獻中相關材料就更多了。翻檢所及,最早的用例是出土文獻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此處之“分”,龐樸曰:“本句與下面兩句的‘分’皆讀去聲,用如名分、職分之‘分’。”龐說是也,並已獲得大多數學者的認同。此句意為“只有明察天人各自的職分,才知道應該怎樣做”。另外,傳世文獻《荀子·天論》篇中有著名的“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的說法。其中,“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一句,楊倞注曰:“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乃撮述其義而非訓詁。考之上下文,此處“天人之分”的“分”,亦“職分”義。梁啟雄《荀子簡釋》引《禮記·禮運注》曰:“分,猶職也。”是也。荀子認為天有“天職”,人有“人職”,各安其分,所以《天論》篇下文即言“唯聖人為不求知天”。章詩同進一步註釋曰“‘天人之分’,自然和人事的分際”,將“分”字直接對應於漢人的“分際”。
“際”,界也。漢人所言“分際”之“際”,是對戰國以來“天人之分”中“分(職分)”之語義的進一步補足。相對而言,“分”偏重於人之作為的邊界而不表述與他物的關係;“際”則指物各有其邊界但又指向會合。《說文·阜部》:“際,壁會也。”段玉裁注曰:“兩牆相合之縫也。”要之,“分”“際” 核心義素皆為“邊界”,但“際”更多了一層基於界限而相接的內涵。由此可以看出,漢人於戰國以來“天人之分” 一語後加“際”字,背後反映的是其致力於溝通天人的思想趨向。
從“學”一方面而言,繼秦焚書坑儒之後,漢初儒術又興,其中主流即學者所謂的“漢有一種天人之學”。這一股潮流終至於“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隋書·經籍志》“緯書”類小序曰:“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其中,“說者”所云一句,是在敘述讖緯之源,指緯書所出的“前漢”時代說經者之言。其論“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是說在西漢讖緯學家看來如此;“表章六經”者,其大旨也就是“明天人之道”,亦即“天人之學”。這是漢代儒家經學的主幹。從“政”一方面而言,據《漢書·公孫弘傳》,元光五年漢武帝策詔諸儒曰:“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公孫弘在奉此對策中被漢武帝“擢為第一”。但他在此次對策中並未縱論天人,至其得用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這就是本文開頭所引“天人分際”說法之所自出。我們認為,此數句雖載於公孫弘奏摺,但其反映的恐非其個人意見而是來自漢武帝的意志。事實上,只需一觀前引“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即可知無論是“天人之道”還是“天人分際”,漢武帝一朝政治話語中的“天人”,其端皆在於天子的主動倡導。
要言之,以政統學,詔書律令者乃“明天人分際”;以學論政,“六經”之敘乃“明天人之道”。由此再來反觀太史公之著史,據其《自序》:“拾遺補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五帝本紀》:“百家言多不雅馴。”《孔子世家》:“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劉鹹炘據此總結史公之意曰:“信《六藝》,表孔子,正百家。”史公之作可謂與漢武帝一朝“表章六經”以“明天人分際”的政學兩界主流思想完全一致。
如前所論,“際”與“分”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有基於界限而相接的內涵。故史公於“天人分際”的說法中,不採“分”字而專言“天人之際”,進一步反映出他對自己所處時代主流思想的把握。而“封禪”大典,即“天人之際”之大者,亦為漢武帝一朝政學話語薈萃之極。對於這一大典的意義,《史記》收司馬相如《封禪頌》有云:“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結合我們的整個分析,可知所謂“天人之際已交”,其內在思想意蘊在於,天子(漢武帝)的作為合於其“職分”而達到天人“界際”之極,乃可得以上“交”於天,此即漢人心目中“天人合一”的中心要義。對這一層,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當他不能參與“封禪”大典的時候,甚至“發憤且卒”,因以託付“究天人之際”的修史重任於其子司馬遷。司馬遷即踵其事而完成《史記》這部史學鉅著。
(本文獲東華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2232019H—02)資助)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成富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