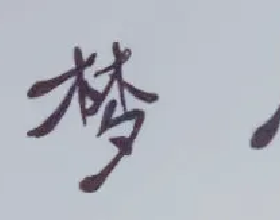---------------
卡森·麥卡勒斯寫過一部小說《啞巴》,後來,她把它改名為《心是孤獨的獵手》。無法言說會將一個人與他人、與世界隔離,那是怎樣一幅影像?深秋落雨的夜晚,在昏暗的路燈下孑然獨行?其實,最喧囂熱鬧處,往往有最濃厚的悲傷,我們終將孤獨。
這大約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之一。當然,作家不會直截了當地寫上這兩個字。
我在讀短篇小說,有點兒難,不太在行。或者說,我對它缺少直覺。別看長篇小說厚厚一本,只要翻開一頁,看幾行,基本能作出判斷,可輪到短篇,我就像味覺喪失的品酒師,“嘗”掉了大半杯酒,依然不知它的好壞。
大衛·米恩斯(你可以不用管這些陌生的名字,他們都是著名的小說家,被邀請來評點同行的作品)說:“一個精彩的故事就像身上奇癢,總得不停抓撓……好故事留給我們的疑問比答案多,同時,留給我們的答案比問題多。”
他在評點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要不你們跳個舞》。
“廚房裡,他又給自己倒了杯酒,看著前院擺著的臥室傢俱”——故事就這樣開頭了。
他那邊的床頭櫃和檯燈,她那邊的床頭櫃和檯燈……所有東西都從房裡搬了出來,還拖出一根長長的電源線,可以接通電器。
一對年輕的男女,開車路過,他們正在佈置一個小公寓。“肯定是在賣二手貨”,女孩說。她在床上蹦跳,隨手拿起枕頭,躺在結實的床上。左鄰右舍漸漸亮起了燈,男孩打開臺燈,電視機看起來很不錯。
男人回來了,拎著三明治、啤酒和威士忌。他接受了男孩所有的砍價,和他們一起喝酒,然後換了張唱片,提議“要不你們跳個舞”?
後來,女孩把這件事告訴了所有人。“這件事裡面有更多東西,但她說不出來。試了一會兒,她放棄了。”
故事戛然而止。我記得,醉意朦朧的女孩跟男人說:“你肯定是很絕望或怎麼了。”她一定忘了。
薄薄3頁。你可以給這個短短的故事,填充很多內容,也可以給各種疑問以答案。所有這些,都在“故事結尾前那一行無盡的沉默與空白中”。
這恐怕就是短篇小說的技巧:沒講出來的故事遠多於講出的。在《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裡,我讀到20個短篇小說以及對它們的點評。每個精悍的短故事裡,都暗藏機巧,它們這樣開始:
“一天下午,父親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安排好喪事。”
“去英格蘭銀行,老闆?這個點兒英格蘭銀行早關門了。”
“一個銷售員和我分享烈酒,睡著了還在開車……”
“艾米莉婭和保羅晃盪夢遊,在人類生活的彩色照片間穿行而過,在臨終之際,在歐洲,在相簿中。”
“今天早上,一個男人來我門口問我洗澡了沒有。”
阿摩司·奧茲專門寫過一本書《故事開始了》,講述好小說如何開頭,其要旨可以簡單濃縮為一句話:“開始講一個故事就像是在餐館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調情”。對於短篇小說來說,這種“調情”一定要乾脆、直接、立竿見影。
故事當然各不相同。
威廉姆斯在講一個孤兒——父親渴死在沙漠,母親溺水於海邊,他在機場航站樓六七十平方米的小小區域裡,遊蕩了7天。
諾瓦曉得的秘密比他見過的任何人都多,他不露聲色地一點點揭開真相,那一場扭轉乾坤的賭博,不過是高手設計的把戲。
邁克爾斯的“城市男孩”被女友的父母趕出家門,他像雜耍藝人一樣腦袋朝下,倒立著逃出公寓;
鮑爾斯的女主角通常“古怪、不諳世故、心理失衡”,就同一個問題——我為什麼在亨利酒店——給丈夫寫第八封信。
格林鄭重宣佈:“除了有病我現在相當健康,不騙你”。他的一個朋友很激動的話,就會一直飄到天花板的高度,像飛蛾撲向棉花糖那樣,反覆撞天花板。
康奈爾沉迷於闊太布里奇瑣碎浮華的生活:她開一輛加長林肯,車技欠佳,不得不找人幫忙停車。原先的洗衣工辭職了,新來的太不懂事,總坐在車前座上。她從在雞尾酒會上遭遇搶劫、驚魂未定的人們口中得知,約翰遜太太的鑽戒居然是假的……
每一處精心編織的細節裡,都玄機重重,可寫出來的並不多。等你細細讀過,就會發現,那些隱藏不見的奧妙,會越來越多地浮現。玩過那個看圖遊戲沒有?有人告訴你,在一幅畫裡藏著9張臉,你看到了幾個?
尤金尼德斯說,“寫短篇的首要難點在於想清楚要把哪些內容留在篇幅之外。留在篇幅之內的內容暗含了省略掉的所有東西。”這句點評,適用於《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的所有小說。
同樣適用的還有孤獨。在一篇篇情節迥異的故事背後,那些貌似平淡無奇或是稀奇古怪的人物身上,我看到了煢煢孑立的孤獨。很多小說,你會忘記它的故事,它的情節,它的人物,可它傳遞給你的那種難以言說之感,卻揮之不去。
馬庫斯評價巴塞爾姆:“如果說他已躋身於我們時代最搞怪逗趣的短篇小說家之列,那他也屬於這樣一個有著獨特才華的寫作者群體——他們擅長在紙面上摹寫出真正的悲傷淒涼。”
羅比森的女主角說,悲傷是件非常私人的事。那麼,孤獨呢?
卡寧的《竊國者》裡,在公學任教多年培養了眾多明星人物的退休老校長,被再一次利用和欺騙。他眼睜睜地看著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最心愛的學生,如今已是一位老人,他很想他問:“先生,在您這個年紀,是不是很孤獨?”
孤獨,誰又不是呢?
馮雪梅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