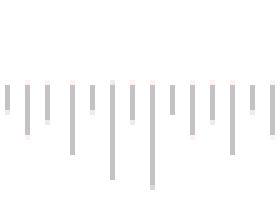第一次離開家鄉,3歲,我被爸媽送去姥姥身邊寄養。雖然家鄉和姥姥家相距僅僅3公里,可對幼小的孩子來說,視線看不到父母的地方就是一片漆黑和迷茫。
我總是騎在門口的斜坡上望著媽媽來的方向,坑塘周圍樹木環繞,有時會擋著她的身影,媽媽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或背後的那份驚喜至今想起時仍舊內心悸動。
從小,我就沒有歸屬感,沒有安全感,總想依賴別人,很羨慕可以肆無忌憚表達自己喜怒哀樂的人,可我卻活成了“完美的小孩”:不黏人、獨自上學放學、不需要家長陪寫作業、不爭不搶、從不與人鬧矛盾、安靜而溫和。
我從來都是被“自己是個外人”的孤獨感裹挾著,雖然姥姥也很愛我。可那種無法撒開性子的侷促和寄人籬下的苦悶,使我異於同齡人敏感百倍,我不敢犯錯,不敢任性,甚至不敢說話。
我只想躲,躲開任何人,躲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性格隱忍、悲觀、倔強、叛逆,別的小孩的青春期過完可能就長成了父母期望的樣子,可我從小到大,都是大人喜歡的模樣。
我乖乖聽話剪掉長髮,歡喜地穿媽媽手工做的又肥又大的衣服,不亂花錢,不塗指甲,不打耳洞,身上不戴任何裝飾品,不期盼漂亮的裙子,家裡有客人時從不伸筷去夾對面的菜,不和花裡胡哨的人在一塊玩,我只坐在院子裡安靜讀書,偶爾幫媽媽幹活,……可是我內心無比清晰:那不是真實的我。
這種清晰的念頭曾一度被我死死按壓著,讓我誤以為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我總是把書中和電視劇中看到的完美女性形象往自己身上靠,你瞧!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她,每個人都愛她,她那麼善良,總是為別人著想。即使壞人那麼折磨她,那麼傷害她,她依然以德報怨,最後感化了壞人,皆大歡喜。
大概有10年,我曾努力想成為那樣的人。
第二次離開家鄉,11歲,我讀初中。姥爺和爺爺在那三年中相繼去世,品味到失去親人的滋味,雖然懵懂,卻真實的疼。我站在前一天晚上還騎腳踏車送我上晚自習的姥爺的床前,他個子很高,床那麼短,身上蓋了一個深藍色的被子,臉也被遮住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親人離世,我再也見不到姥爺了。
媽媽哭的傷痛欲絕,我卻高燒不退,給她增添了不少麻煩,她一邊要忍受失去父親的難過,還得照顧我。我很內疚,所以我強忍頭暈目眩雙腿痠軟的難受,堅持去學校上課,以減輕她的負擔。
姥爺出殯,我請假回家。從墳地裡回來,我就暈倒了。媽媽才知我已經連續三天高燒接近40攝氏度未退,她因心疼而責怪我,我卻很開心,因為我沒有給她添麻煩。
讀初二的時候,我交了一個學習成績不好的女生朋友,她每天嘰嘰喳喳和我討論各種對男生的小心思。青春懵懂,我也覺得被人喜歡是件很開心的事。直到有一天晚上二哥和家裡人在院子裡乘涼,我放學回家聽到他笑著說我:“長大了,到了想交男生朋友的年齡了。”
媽媽說:“才幾歲,心思就不放到學習上了。”
我聽著那話刺耳,淚水在眼眶裡噙著。可他們說的是事實,我那段時間學習成績下滑了很多。
媽媽從小教育我,女孩子要自愛,不能和男孩拉拉扯扯,不必要說的話一概不理,安心學習。直到大學結束我還打心底裡認為男女關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每次聽到同宿舍女生一臉開心地向我們介紹她們的男朋友時,我心裡生出許多驚歎。
二哥是我很喜歡的人,他比大哥隨和,比三哥穩妥,我特別在乎他所說的話。自那個暑假,我切斷了和那個女孩的一切聯絡,開始認真學習。
如今,快二十年過去了。
有次回家,我聽到媽媽提起那個女生,她結婚了,丈夫死了,她自己帶了兩個孩子,生活艱苦,再婚也不容易。我聽著,心中難過,不願媽媽再提起她。
她或許怨恨過我,因為我沒有任何解釋就死活不理她了。青蔥歲月,我討厭我自己早熟和無情的模樣,把最真誠的友誼丟棄了。偶爾夢迴,總還記得她家門口那段路,我們一起上下學走了很多遍。期盼歲月多些仁慈,讓她少些吃苦,多些幸福。
我若說其實我也很渴望有人陪伴,只是太怕分離時撕扯的疼痛了。你信嗎?
而今,我還能記得的朋友中,楠楠定居海南,慧敏因病猝然長逝、郭郭去了上海、田禾在洛陽。偶有聯絡,感覺也淡了。可少女時代她們在我記憶中的模樣從未改變,曾陪伴了我最美好的高中、大學時代的她們,是我今生一直珍惜的溫柔。
真正意義上的離開家鄉,其實是從結婚開始的。雖相距一百多公里,卻因為工作繁忙、家庭瑣事纏身而疏於回家,我曾在心裡數次問過自己,我對家鄉有感情嗎?肯定和否定的答案各佔一半。
這些年內心的疏離感並沒有讓我特別沉穩,反而有時候很感性。某一個時刻我思路清晰,目標明確,有時候我卻瞬間就能把自己逼到死衚衕。
肯定自己對家鄉充滿感情是因為只要在那片土地上甚至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內心就無比踏實。否定時可能就是源於發現有很多我離開時還在甩大鼻涕的小孩,竟然已長成十幾歲的青澀模樣,彼此之間亦喊不出名字。
“前院的奶奶去世了。”媽媽說。
“啥時候的事?”
“四五天了,已經埋了。”
“嗯。”
良久。
“年紀大了,沒少受罪,走了也好。”媽媽喟嘆。
“嗯。”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樣的對話出現了很多次,每一次內心彷彿都被狠狠拉扯了一下。
害怕媽媽開口說這些事,又怕她不說。
看著我從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一步一步長大的人們,一個一個都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最讓我肝腸寸斷的是我的姥姥和大哥。
我和姥姥的感情在她去世前超過我和我媽,彷彿人生中我的每一次決定都或多或少有她的參與,我習慣了她在身邊的日子,以至於我參加工作後又回去陪伴了她將近三年。我們倆同吃同睡,我下班晚回家一會兒,她就像十年前我讀初中時一樣站在門口焦急等待。
姥姥去世,我覺得自己就如無根的浮萍,再也沒有了依靠。出殯那天,天寒地凍,鵝毛大雪,我跪在冰冷的泥路上膝蓋凍成了傷,卻沒有感覺到一絲疼痛。
姥姥去世後的半年,大哥溘然長逝。二哥打來電話,我瞬間耳鳴,耳朵裡全是呼嘯和疼痛的喊叫聲。我怔怔地站在門邊,忘記了哭泣。一生正直且嚴肅的大哥,一動不動地躺著任家人給他換衣服、穿鞋子。他那麼講究,他怎麼允許別人碰他?人生就是這樣難以預料,我的眼前總還能浮現小時候我騎在路埂邊上等他下班回家的日子。這一生,都回不去了。
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讓我成了如今的自己,已過而立之年,我依然還是十幾歲時的心境,只是增添了一份歲月饋贈的淡然和從容,其他一概未變。
有人說:生活就是這樣,沉湎過往沒有意義,人總要向前看。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每個人的成長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促,無論到了何種年歲,不能忘記最初出發的地方,因為那是生命的起源,人生的支撐和活著的意義。
越來越頻繁想回家,哪怕只是在村口站一會兒,聽一聽清脆的鳥叫聲和牆角地裡的蟈蟈聲、各種不知名的蟲子聲,聞一聞塵土的清香和鄉村獨有的味道,和幾位健在的爺爺奶奶們聊會兒天,聽聽他們講述他們小時候的生活,當然,也有我兒時的故事。
姥爺、姥姥和大哥的墳連在一起,每次回家經過,我都會把車停下,車座後傾,面朝他們,躺一會兒。
心能走多遠呢,不過還是在家鄉附近遊蕩。
責任編輯:謝宛霏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