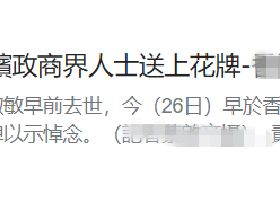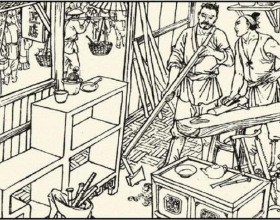兒子去世以後,秦怡一直不敢相信。
所有人都告訴她,這一次,金捷真的走了。可是她搖搖頭,一句我不信,轉回頭,把自己關在兒子的房間裡好幾天不見人。
二十多年前,臥病在床多年的丈夫金焰走了,大家和她說,現在你可以歇歇了,她說不對,我還有兒子要照顧。金焰在的時候,在陽臺上種了一盆小白花。金焰走了,再沒人給小白花澆水。有一天她去陽臺一看,小白花已經枯萎了。秦怡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撲簌簌直流:“小白花呀,小白花,你無論如何也要再開花一次好嗎?我一定也好好伺候你,你什麼時候要水,我就什麼時候給你澆水……”
寂寥長夜,皓月當空,秦怡獨自對花盤訴說心事。
結果第二天,小白花真的開了,足足有40朵。
秦怡笑了,她知道小白花的意思了。
金捷還在的時候,秦怡白天在外面忙,回到家裡又要忙著兒子的吃飯、穿衣、喝水服藥。冬天秦怡親手為兒子織毛衣,夏天秦怡又要為兒子擦身子。
秦怡對兒子之所以如此無微不至就是因為她的兒子金捷有很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秦怡經常對別人說我兒子得了這種病,其實最痛苦的是他自己,而最操心的是他的母親,我是他的母親,所以我必須加倍的給他最真摯的愛護和關心。用她的話來說,別人照顧兒子,她不放心。
別人總說孩子大了要離開父母,可是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她的身上。從兒子得病那一刻開始,兒子就是一隻折了翅膀的雛鷹,秦怡就像是羊媽媽,一口口奶著這個兒子。她被這個孩子給困囿住了,可是她沒有埋怨上天,只是用自己並不寬厚的肩膀,把孩子綁在自己的身上,一步一步,走得很踏實。
金捷小時候很喜歡畫畫,秦怡就給她買了畫筆畫架,想要培養孩子畫畫的興趣。可是有一天秦怡在拍戲的時候突然接到了家裡的電話,“不好了,你快回來吧,孩子出事了。”秦怡放下手上的事就往家趕。
一開啟家門,她看到的便是滿地的碎紙,而金捷坐在桌子旁,拿著筆和紙亂塗亂畫,塗完畫完便把那些紙撕掉,然後開始自言自語,還嚷嚷著要媽媽重新給他買。金捷這些不正常的舉動讓秦怡又驚又怕,她急忙帶著兒子去了醫院,卻讓她得到了一個遺憾一輩子的訊息,只有16歲的金捷得了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放在現在都是一個無解的絕症。
秦怡覺得自己的天都塌了,而之後當秦怡瞭解到這一切都和自己的忽視孩子的成長有關,秦怡更加是痛不欲生。
原來由於秦怡是全國有名的大明星,孩子的爸爸又是有“電影皇帝”稱號的金焰,夫妻二人的工作十分繁忙,平時孩子就託給了奶奶照顧。可這照顧卻照顧出事兒了。
金捷從小就性格內向,不喜歡言語,尤其是愛上繪畫以後,更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了畫畫的世界中去了。可是他的沉默卻給了學校那些壞孩子欺負他的機會。常常逮著就欺負他,拿籃球扔他打他,可金捷從來只是逆來順受,從不反抗,更不跟家裡任何人說。而照顧他的奶奶能讓金捷吃飽穿暖就可以了,根本不會意識到要時刻關注金捷的心理健康。
金捷受人欺負,感到孤獨的時候,無人訴說,無法排遣,長此以往,他的心理疾病發展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而作為母親的秦怡更是因此深深自責。秦怡孩子生病以後極其懊惱,痛苦,她想不到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在兒子的身上,如果有什麼折磨衝著她來就好了,為什麼要降臨到兒子的身上?
這件事讓秦怡一直耿耿於懷,即使金捷去世以後,她也總覺得是自己對不起兒子,虧欠他的太多太多。
她經常和朋友還有采訪的記者說:“當時我們一年到頭在外拍戲,缺少對他的關愛,也沒察覺到小弟內向的隱患,忽略了兒子成長的煩惱。無人傾訴,孤獨導致了他的自閉,假如不是這樣,多在他身上花些時間,或許小弟的性格可以被疏導和轉化,都是我們欠他的。”
其實我們可以想見金捷的那種痛苦。秦怡在回憶中說:在金捷的童年和少年的時光裡,想要見母親一面都很困難。多少次,金捷眼巴巴地望著窗外,盼望今天母親能夠回家,可得到的答案通通都是失望。
那天,秦怡回到家,收拾起的兒子亂扔的畫本畫架,把他們放在櫃子裡,不免心生傷感。她原本希望兒子用這一幅畫筆畫架發展一下他的繪畫天賦,學點特長,可如今兒子卻成了一個精神病人,一時間所有的希望都化成了泡影。
從那以後,那幅畫筆畫架就被束之高閣,逐漸被遺忘。
兒子生病了,秦怡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帶著金捷四處尋醫看病,可是得到的答案都是,沒辦法,治療不了。可是秦怡不信,她覺得自己要把所有虧欠兒子的都償還回來。既然在兒子之前十幾年的生命中,對母親都是等待的遺憾,那麼現在她要把這種遺憾彌補回來。
這種彌補的力量變成了一種決心,一種責任,它和秦怡在影視上扮演的那些堅韌的女性形象重合起來,她的藝術形象帶著一種真實的力量,當所有人都在驚歎她藝術創造的生命力的時候,沒人會想到她所揹負著的苦難。
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同秦怡的那麼多電影聯絡在一起,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錯覺。是怎麼樣的一種力量在支撐著她齲齲獨行,每天傍晚她回家的時候,她那較小而又堅毅的背影推開家門的影象,怎麼不讓人流淚呢。
一個錯亂的精神漩渦出現,能夠伸張出怎麼樣的一種偉大?
落淚,不是同情,而是因為偉大。
這種偉大,通俗地說叫做母親。
金捷生病以後,秦怡就把兒子帶在了身邊,哪怕是拍戲,表演前也要先把孩子照顧好再出門。
可精神疾病的治療並不簡單,最大的障礙就是怕復發,怕受刺激。為了治病,金捷不斷地吃藥、住院,甚至是殘酷的電休克療法都試過了,他的病情終於在母親細心陪伴下得到了好轉,一度還重返學校。眼看病情已有好轉的金捷,卻在秦怡一次出差,離開身邊不在家期間不幸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病情再次發作。
從那以後,金捷再也無法回到學校,也再也過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秦怡萬萬想不到孩子的病情有一天在她的照顧下再次惡化。
在海南拍攝《海外赤子》的時候,秦怡總是穿著一件長袖,從來不敢把她的手腕以上的部分顯露給別人看。其實如果有心人把她的袖子捲上去就會發現上面是累累的傷痕,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她的兒子金捷。
原來由於金焰臥病在床,無法照顧兒子,秦怡只好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金潔帶到了拍攝地海南。可不料有一天,秦怡拍完戲回到住所,剛剛開啟門,金捷便怒氣衝衝地衝著秦怡的臉就打了一巴掌。
原來海南的氣候太炎熱了,平均氣溫都能達到40度,長期生活在這種桑拿天,普通人都會被搞得燥熱不安,更別提一個精神病人了。
高溫的燥熱,原本並沒有暴力傾向的金捷得了狂躁症,發病時,他就把每天逼他吃藥的母親當做了發作物件,常常對秦怡大打出手。金捷的病情從那以後變得更為嚴重。
那段時間,金捷幾乎天天對秦怡動手,秦怡躲不過去的時候,只能任由兒子打罵。
為了不耽誤拍戲進度,秦怡只得將頭抱住,把背對著兒子的拳頭大聲叫著:“別打媽媽的臉,媽媽明天要拍戲,不能打臉。”
“不能打臉,明天媽媽要拍戲!”我們在佩服秦怡的敬業的時候,也為她的母愛動容。兒子的每次動手,她都一個人承受下來了,她把這種痛苦都歸咎於那些年自己的忽視。她把這些當做了自己的懲罰,她坦蕩地接受了這些懲罰,她唯一有著一個要求,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衝著自己來。她不止一次對金捷說:“你千萬不能動手打別人。”
可讓秦怡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有一次金捷在發病時因為天黑看不清,不小心打了家中的保姆。雖然保姆只是皮肉傷,可秦怡想想就後怕。孩子的病終於還是加重了。
無可奈何的秦怡只能把孩子送去了醫院。
金捷知道自己闖了禍,他可憐巴巴看著自己的母親,秦怡強忍著內心的不捨,把兒子交給了醫院。就在秦怡安頓好金捷準備離開醫院的時候,金捷看著母親的眼神十分不安,這眼神,秦怡十分了解,她明白金捷內心深處很害怕從此以後會被母親拋棄。
秦怡也是十分不捨兒子,可是為了兒子的病,她也只能狠心離開。而金捷在醫院這一住就是五個月。五個月裡,秦怡每逢拍戲的空隙就跑去醫院,一天三次,可就是這樣,金捷仍然放不下心。他已經習慣了母親對他的照顧。晚上睡覺的時候,總是哄了他吃藥之後才睡。可是在醫院,醫生護士有一大堆的病人需要照顧,不可能對每個病人都照顧周全。
在家裡的時候,秦怡對待兒子是百般細心的呵護,可是現在在醫院,金捷只能每天孤獨地躺在床上,看著醫護人員來來回回忙碌的背影。孤獨,一種被拋棄的感覺時刻縈繞在他的心裡,他知道自己犯了錯應該受到懲罰,所以對於治療他十分配合。他的病也逐漸穩定下來,時間就這麼一眨眼過去了五個月。
五個月後,由於治療效果顯著,金捷被許可出院了,他終於如釋重負。金捷出院後,迫不及待地向秦怡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說:“媽媽,讓我回家吧,我保證再也不會打人了。”
秦怡的眼淚一下子下來了。她又何嘗願意把兒子留在醫院,看著兒子可憐巴巴的眼神,秦怡的心也軟,她伸出自己的小手指勾住兒子的手指說:“只要你不動手打人,媽媽就不送你進醫院。”
母子二人就這樣用拉鉤鉤的方式相互許下了承諾。可是就是為了這個承諾,秦怡開始了更為艱難的治療兒子的道路。
金捷畢竟是精神病人,秦怡也不是專業的醫生。金捷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狂躁症發作起來,完全不記得自己當初的承諾。
難道要把兒子再送回醫院?不說自己不願意,兒子的病情可能會再次加重。但秦怡並沒有被困難擊倒,以前已經對不起兒子了,現在無論如何不能辜負他了,秦怡開始四處諮詢醫生,翻看醫書,可是收效甚微。直到有一次金捷情緒開始不穩定,眼看著又要動手的時候,秦怡急忙對金捷說:“小弟,別這樣,這樣又要進醫院了。”
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金捷的頭腦還是處於清醒狀態,他馬上想起了與母親的約定,立即安靜了下來。這次事件似乎給秦怡點明瞭一條出路,秦怡開始漸漸摸索出了治療金捷的方法。
秦怡在後來接受採訪時也提到了這個方法。
無論如何,他做錯多麼錯的事,我也不會去罵他,因為知道罵他了以後他會心情不好,像這種病人是不能去跟他對抗,也不能去罵他。你要跟他講道理,別鬧別鬧,鬧了又要進了醫院了,又不好辦了。
秦怡的方法,簡單一句話就是要一點一滴的照顧到金捷的情緒,要讓金捷保持開心的狀態。
在秦怡的細心照料下,金捷的病情一點點好了起來,而接下去一個驚喜卻終於在等著這對苦命的母子。
一次秦怡帶著兒子去小時候最喜歡的衡山公園遊玩,走著走著,原本和往常一樣神情木然的金捷突然激動起來,拉著母親的手興奮地手:“我小時候來過這裡,我畫過這裡的樹。”金捷的話讓秦怡驚喜不已,兒子已經好久沒有這麼興奮了,更別說開口說話了,而接下去金捷的話更是讓秦怡被巨大的喜悅給包圍了,他說:“媽媽,我要畫畫。”
秦怡愣了一下,馬上拉著兒子的手衝回家,從層層的物件中拿出那副被她擱置的畫筆畫架。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多年,曾經健康的金捷拿著它們畫畫的樣子還是歷歷在目,而現在兒子重獲健康的希望有重新出現在了秦怡的眼前,秦怡是興奮不已。那天,秦怡拿著畫筆和畫架帶著兒子再次回到這座公園。金捷看到了久違的畫筆和畫架,顯得十分興奮,他彷彿回到了他的少年時期,拿起畫筆就不願意放下。
兒子天生就是畫畫的,秦怡看著眼前的兒子內心暗暗下了一個決定。她給兒子請了一個繪畫老師,教兒子畫畫。金捷對繪畫的天賦很高,他的畫有種獨特的味道,或許是因為金捷的心中少了現實世界的許多束縛,他的畫雖然沒有過多的技巧,卻充滿著靈動的色彩。
秦怡有時候也會跟著一起畫兩筆,每天有了畫畫陪伴,金捷沒有了焦躁的神情,也沒有再犯過病,打過人。秦怡經常帶著兒子四處畫畫寫生,後來為了鼓勵兒子,她還把兒子的畫拿去義賣。
金捷並不懂得什麼叫做義賣,可當他得知義賣是為了幫助像他那樣的有障礙的人的時候,金捷總是會一口答應下來,認真作畫。
2000年的時候,在上海的波特曼大酒店,金捷的一副名為衡山公園寫生的水粉畫被展出拍賣,最終這幅畫被施瓦辛格用25000美金的價格買走了。得到這幅畫後,施瓦辛格很是興奮,他拉著金捷的手大叫著,this is a miracle。這是一個奇蹟。
是啊,這是一個奇蹟,一個母親創造出來的奇蹟。
可是在這歡樂背後,秦怡的眼中常常帶著一絲憂慮。在別人看來,秦怡現在是苦盡甘來,可是秦怡自己知道,自己陪伴兒子的時間可能不會太久了。
這些年來為了照顧患病的兒子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由於常年患病,金捷的主要任務就是接受治療,所以他並沒有生活自理能力。而且由於常年服用精神藥物,金捷的身體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患上了糖尿病和便秘,腎也不怎麼好。有時甚至會出現失禁的現象。這些都需要秦怡的親自照料。但是需要秦怡的並不僅僅只有金捷,早在金捷生病之前,秦怡的丈夫金焰就因為嚴重的胃病而做了胃切除手術,臥床不起,也需要秦怡的照料。
在女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秦怡的生命除了工作,就是照顧家中的兩個病人。
1983年12月27日,丈夫金焰去世了,所有人都以為她可以鬆口氣,可是她卻一件挑起了治療兒子的的重擔。
金捷在生病前由於秦怡忙於拍戲,金捷想見母親一面都是很困難,更別提到母親的愛護。可自從他生病以後,生活的每一天都有母親的秦怡,除了照顧金捷的飲食起居,還會始終讓他保持開心的狀態。小弟怕打雷,於是每到打雷下雨,秦怡就會養成習慣,她會立即衝到金捷的房間去寬慰他。路上遇到金捷愛吃的小吃,秦怡總是不忘帶一份回家。
在金捷患病後,他體會到了他年少時從不曾體會到的母愛,秦怡此刻加倍的愛護和關心兒子,冥冥之中用這種方式彌補了那份對兒子曾經缺失的母愛。
可是秦怡自己的身體也並不好,她生過4次大病,開過7次刀,44歲,得了腸癌,被醫生斷言“活不久了……”
死亡的陰影總是在她腦海中揮之不去。她不是怕死,她是怕自己死了以後,兒子該怎麼辦?
她死了以後誰來照顧金捷,金捷生活不能自理,大到打胰島素,小到洗澡,剪頭髮,剪指甲,生活上的一切瑣事,誰能像她這樣無微不至照顧他?萬一自己先走一步,留下這樣的兒子該何去何從?
她曾經試探性地問兒子,小弟呀,媽媽死了,你怎麼辦?
金捷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死亡,他不加思索回答,你不會死。可回答後,金捷低頭沉默片刻,他又補充了一句,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了。
兒子的回答讓秦怡不免悲從中來,當年那五個月的住院,金捷是那麼離不開自己,可是現在萬一自己真的不在了,他又會怎麼樣呢?
秦怡好想為兒子撐起一片天,可是這片天還能撐多久?自己的年紀和身體自己知道,但是生活還是要繼續呀,日子還是要熬下去。沒準有一天金捷就不需要自己的照顧了呢?
可是這一天,金捷終究還是沒有等到。
2007年年初,金捷因為糖尿病和腎病住院治療。秦怡以為這一次和往常一樣,金捷沒過多久就可以出院了,可是沒想到的是,住院沒多久金捷就因為病情加重,昏迷不醒。
秦怡擔心極了,她坐在兒子的身邊,握著兒子的手說:“小弟,小弟,看看媽媽,不要總是睡,這樣對身體不好,你睜開眼睛看看。”
她一刻都不敢離開兒子,她害怕自己一離開兒子就會一睡不起。她心中有種隱隱的憂慮,她覺得兒子這一次可能真的挺不過去了。可是她馬上又把這種憂慮撇開了,兒子還年輕,兒子絕不會先自己而去的。
但金捷此時似乎連睜眼的力氣也沒有了,可她仍舊堅持不懈地跟金捷說話。終於有一天,金捷醒了,他張開嘴,幾乎用盡自己的全部力氣說了句:“沒有關係,沒有我,你可以省點力。”
秦怡像是一尊突然被風乾的雕塑,她顫聲說:“我們治療,孩子,不要緊,我們治療。”
她知道金捷的病已經無力迴天,可是她還是懷著哪怕一絲絲的希望,她覺得奇蹟沒準又會突然降臨,就像這些年一樣,兒子在她的照顧下不是成了一個畫家了嗎。沒事的,一定沒事的。
金捷像是懂了母親,那些年母親不在身邊的怨氣像是突然間消弭了。他內心更加清楚明白母親這些年來的辛苦付出,也許自己走了,母親可能就沒有這麼累了吧,才會活得更自由更省心。也因為這樣他才會對秦怡說出那樣的話來寬慰母親。
金捷住院的季節,天氣還是乍暖還寒,金捷的手長期放在被子外面打吊瓶會變得冰涼,於是秦怡總是會在金捷打完吊瓶後幫他捂手。可這時,昏迷中的金捷還能夠有意識將手慢慢抽出來,重新握住母親的手,輕輕地撫摸,兒子的這些言行,似乎是在寬秦怡的心。金捷像是有了預兆一般,用這種方式安慰母親不要難過,秦怡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挽救兒子了,她能做的只是時刻陪在兒子身邊,不停地在他耳邊說話,讓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不會感到寂寞。
2007年3月7日半夜,與病魔鬥爭了四十多年的金捷安然去世,用金捷的話來說,自己終於可以讓母親省力了。或許金捷在冥冥中希望自己的離去可以讓母親放下一個累贅,過得更輕鬆,所以他才走得那麼從容。
金捷下葬以後,秦怡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對於別人的勸慰,她統統拒之門外。從兒子生病開始,金捷和她是形影不離,四十多年來,兒子成了她的命,而現在兒子走了,她的半條命也丟了。
秦怡結過兩次婚。第一任丈夫叫做陳天國,是電影廠的同事。一次陳天國約她去山頂,陳天國對她說:“自從見到你,我就喜歡上了你。沒有你的日子,簡直太痛苦了。你嫁給我吧。”
秦怡震驚得睜大了眼晴,她下意識地說:“不,我還太小,請你原涼。”
陳天國瞬間像發瘋了一樣,衝到懸崖邊。他拉著秦怡:“你如果不答應,我就從懸崖上跳下去。”
秦怡被逼無奈答應了。可是陳天國是個酒鬼,而且還家暴,生了孩子以後,秦怡就和他離了婚。
後來她又認識了影帝金焰。兩人很有好感,那時,電影廠距離秦怡家很遠,金焰就和她說,你可以住到我家去,我睡地板,你睡床。可是秦怡很不好意思,因為她經常工作到晚上兩三點怕打擾到他。金焰說沒關係,你來了就在樓下喊老金,我出來接你。
秦怡答應了。兩人的心越來越近,1947年,他們正式結婚。可是金焰也酗酒,後來還因為飲酒過度做了胃切除手術,重病不起。秦怡這麼多年一邊要照顧兒子還要服侍丈夫。
這麼多年來,秦怡把人世間所有的痛,所有的苦都嚥了下去。她已經習慣了,可是現在這些個重擔一下子突然去了,秦怡卻不適應了。
金捷去世了,秦怡將兒子的畫都收好,那副最喜歡的衡山公園寫生畫被她裝裱起來放在了客廳。她還有一副兒子畫她的畫像,十分珍惜。畫像上的秦怡還是年輕時候的模樣,只是手法十分粗糙幼稚,這是最後進醫院前金捷畫給媽媽的,在他的心裡媽媽永遠是年輕漂亮的。秦怡明白兒子對自己的不捨,她又何嘗不是呢,家裡的擺設,桌椅板凳的位置,兒子的畫筆畫架,最喜歡的躺椅,兒子的房間裡的陳設,統統沒有變過,一切好像金捷還活著一樣。
只是物是人非。
她白天在片場工作,晚上回到家還是像往常一樣喊兒子,小弟,媽媽回來了。可是兒子再也不會出來。晚上,下雨打雷了,她會去兒子房間看看窗戶有沒有關好,可是走到門口才想起來,這個房間裡再也不會有人了。她有時候覺得兒子還在眼前走來走去,可是一抬眼,房間裡空蕩蕩只有自己。
她一直擔心兒子離開她不能適應,可她竟然沒考慮到她離開了兒子更是無法生存,甚至一度活不下去。秦怡只能不斷地勸說自己要堅強,要勇敢。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電視上正在播放汶川大地震的畫面,看著那些倒塌的房屋,看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秦怡突然泣不成聲。我的孩子雖然有病,可是他活到了59歲,可是這些孩子卻這麼年強,在不應該走的年紀離開了。我怎麼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小愛之中呢,我有能力,我可以幫助更多的孩子。
秦怡將原本給金捷攢著看病的錢,捐獻給了四川災區。
她說:“我年紀這麼大了,出不了多少力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捐款……”
有人讚揚她月工資不過2000元,還把終身積蓄都捐了出來,她馬上否認:“我的生活不受捐款的影響,沒有積蓄,還有下個月工資。”
秦怡好像重新活過來了。93歲的時候,她自編自導自演了電影《青海湖畔》,95歲她出演了《妖貓傳》裡的老宮女,單是坐在那裡,就有一種“白頭宮女在 ,閒坐說玄宗”的詩意和滄桑。現在她99歲了,住在醫院裡,有時候趁著醫護人員不注意還想偷偷溜出去拍戲。她是閒不下來的,老是想要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舒繡文曾經說她,美得就像花瓶裡盛開的康乃馨,無論男女,見了都喜歡。
秦怡,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讚美這個偉大的女性。她把人世間所有的苦都吃透了,她的身上有著難以言喻的偉大力量,這是一種叫做母親的偉大力量,我想,就憑著這種無以言表的偉大,她亦無愧於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