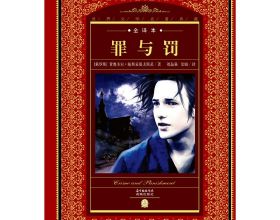題記——包小山,出生在五十年代上海的一個幹部家庭。優越的家庭環境,把他養成了一個貪玩,沒有責任心的男人。直至年逾古稀,生命即將終結時,他才幡然醒悟,悔恨不已......
就在包國強老夫妻去世後的一年多的時候,包小山突然有一天,像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出現在電子廠的家屬區。他穿著一套嶄新的深藍色西裝,開著一輛白色的普桑轎車,身旁跟著一個妖豔的女人,身體已經發了福的包小山,見到熟人一邊打招呼,一邊不停地發著手裡拿著的中華牌香菸。
當年和包小山要好的哥們,聽說他在深圳做生意,發財了,陸陸續續地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
晚上包小山在飯店擺了三桌,把當年和他要好的哥們和鄰居都請了去。
大家看著風光無限的包小山,對他當年沒有回來參加他父母的葬禮,鄰居早已忘的乾乾淨淨,相反都誇讚他有本事,為他父母爭了臉。
晚上看著回到家裡的包帥,已經長成大小夥子了,包小山微笑著指著站在他身旁的女人說:“小子,你叫她媽。”
包帥拉開門,斬釘截鐵地說:“我媽兩年前就過世了,她現在躺在西郊墓地,還有你,都給我滾出去。”
包小山抬手要打包帥,站在他身旁的女人趕緊制止了包小山,拉著他的手,用著嬌滴滴的聲音說:“老公,這裡怎麼住人啊,我們去開賓館吧。”
看著包小山摟著女人離去的背影,包帥向地面吐了兩口唾沫後自言自語地說:“什麼個東西,我媽,我只有一個媽,她叫吳春梅。”
三天後,在包小山離開家的時候,給了他姐姐包倩兩千元錢說:“姐,小帥那兔崽子也不理我,這錢,放你手,請你幫忙替我照顧好他。”
一九八六年三月份,電子廠家屬區要拆遷,包小山趕回來後,簽了字。幫包帥在學校的附近租了兩間房子,丟下幾百元錢,隨後連夜趕回了深圳去了。
那年包帥讀初二,每天早上去上學,晚上在學校上完晚自習後才回到出租屋。他的房東是一位聾啞大叔,有一個和包帥一樣大的女兒,和他在同一所中學上學。
慢慢的兩個孩子開始熟悉起來,原來房東姓李,他的女兒叫李小曼,長著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扎著一條粗粗的馬尾辮子,臉上每天都帶著微笑。房東李叔,喜歡吹笛子,每到星期天的午後,他就會坐在院子裡的那棵棗樹下,吹起那根磨得烏黑髮亮的竹笛。李小曼這時就會依偎在他的身旁,默不作聲,靜靜地聽著。悠揚的笛聲,穿過院子,飄蕩在空中。這時包帥就會情不自禁地走出屋子,依靠在門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眼前這幅美麗的畫面。
包帥看著同學們都騎著腳踏車上學,他也想有一輛屬於自己的腳踏車。在他過十五歲生日的那天,中午放學後,包帥用路邊的公用電話給他父親撥了好多遍,好不容易等到他的父親包小山接電話。當包帥說想買輛腳踏車,騎著上學方便時,包小山在電話裡冷冷地說:“買什麼腳踏車,瞎花錢,”說完就掛了電話。
回到家裡,包帥煮了一碗麵條,只吃了幾口,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下午他沒有去學校,步行二十多里路,冒著寒風去了西郊他母親的墓地。他一邊流著眼淚,一邊伸出手擦拭著墓碑上的灰塵說:“媽,你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說完包帥在墓碑前就放聲大哭起來。
看著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包帥也哭累了,他擦了擦眼淚,一邊給他母親磕頭,一邊嘮叨說:“媽,你放心吧,我會照顧好自已的,”說完包帥鼻子酸酸的,眼淚又流了下來,隨後他一步三回頭地才離開了墓地。
回到家裡的包帥,感到渾身沒勁,躺在床上就睡了。深夜裡,他感覺越來越冷,擔心自己感冒了,於是起身找感冒藥,找了半天,藥也沒找到,暖瓶裡也沒有開水。他頭重腳輕地出了房間,敲開了房東李叔的門。這時聽到動靜,起床的李小曼幫忙找來感冒藥,又給他端了杯開水。包帥吃完藥,在李叔的攙扶下,回到房間裡,躺了下來,望著房東李叔離去的背影,包帥迷迷糊糊就睡著了。
在睡夢中,包帥看到母親,滿面微笑著端著一碗雞蛋麵向他走來,他接過母親手裡的碗,一邊吃著面,一邊望著母親。就在包帥沉浸在無比幸福的時光裡,這時他被人推醒,他睜開眼睛,看到李小曼笑盈盈地端著一碗蛋炒飯站在床邊說:“快起來吧,這是我爸給你做的,吃了好上學。”
包帥吃完飯,李小曼騎著腳踏車揹著他向學校走去。
自包帥那次生病後,房東李叔知道他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就經常喊他過去一起吃飯。有房東父女倆的關懷,包帥感覺他有了依靠,一心用在學習上,初中畢業後,他順利地考上了市裡的重點高中。
就在包帥讀高二那年,有一天晚上,他剛回到屋裡,李小曼走進房裡,流著眼淚說:“包帥,我也沒有可以說說心裡話的朋友,你說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包帥望著在流眼淚的李小曼問:“你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嗎?”
李小曼伸手擦了擦眼淚,看著包帥,講出了她的身世。
原來李小曼不是房東親生的,十幾年前她在火車站,是被她的養父撿回來的。今天派出所來人,抽了她的血,說要入庫進行DAN比對,說她的父母在找她。
李小曼不想找她的親生父母,她不明白他們既然生下了她,又為什麼要拋棄她。
包帥安慰著她說:“小曼,你也不要這麼想,說不定,你父母不是拋棄你,是有其他原因呢?”
李小曼抬頭望著包帥說:“即使如你所說,我如果和他們相認了,那我養父怎麼辦?他在我心裡,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父親。”
包帥想了想,伸手撓了撓頭說:“小曼,這個我也說不好,你自己拿主意吧,李叔確實是個大好人。”
一九八九年春節前,包帥的父親包小山因生意失敗,回到了上海,住在包帥的出租屋裡。
他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包帥那年高三,學習任務非常重,晚上回到家後,還要替他父親洗衣服,打掃衛生。後來,包小山直接將人帶到家裡打牌,常常是通宵達旦。有幾次,夜裡一點多鐘,包小山還把把包帥喊起來,去給他們買菸,買夜宵。
就在包帥高考的前一天,包小山一班牌友一直打到深夜,洗牌“嘩啦啦”的聲音,再加上吵鬧聲,包帥怎麼也睡不著。為了第二天的高考,包帥無奈之下從床上起來說:“叔叔,我明天要參加高考,求你們不要再打了,回家吧,讓我睡會覺吧。”
這時大家都愣住了,屋裡剎那間靜了下來,這時一個牌友說:“嗨,怎麼把這事給忘了,快快,我們散了吧,讓孩子好好休息。”
一九九零年七月份,包帥以高出一本分數線三十多分的優異成績,被北京一家科技大學錄取。
就在包帥準備去北京上大學的前兩天,當地的派出所幹警帶著李小曼的親生父母,從安徽省蕪湖市趕到了上海李小曼的養父家裡。
見到李小曼時,她的親生父母抱著她一邊哭著一邊說:“女兒啊,我們終於找到你了。”
李小曼推開她的父母,流著眼淚問:“你、你們為什麼現在才來找我?我不想認你們。”
這時她的母親直起身子,伸手不停撫摸著李小曼,一邊注視她一邊哭著說:“閨女,你丟了十五年了,我和你爸就找了你十五年啊。”
站在一旁的滿頭白髮,顯得十分蒼老的李小曼生父走了過來,拉著李小曼的手,流著淚水說:“女兒,你可以恨我們,是我們當時沒有照顧好你,才把你給弄丟了。”說完,他轉身拿出一個布包,從裡面拿出十五個,已經變色的熟雞蛋說:“閨女,自你走丟後,每年你的生日,你媽媽都要給你煮一個熟雞蛋,你看這些雞蛋,一直收著,我們等你回來啊。”
這時李小曼,雙膝跪在地上,一邊給她的親生父母磕頭,一邊哭著說:“對不起,爸爸,媽媽,我錯怪你們了。”
李小曼的父母趕緊拉起她,一邊流著喜悅的淚水,一邊說:“不哭了,孩子。”
隨後李小曼的親生父母來到滿眼噙著淚水的聾啞人李叔的面前,雙雙給他跪下,一邊磕頭,一邊說:“大兄弟,謝謝您,把我們的女兒養大。”
李叔趕緊起身拉起李小曼的親生父母,一邊擦眼淚,一邊擺動著手。
那天,包帥正在火車站候車大廳裡,等去北京的列車時,一陣悠揚的笛聲《外婆的澎湖灣》在候車大廳的角落裡響起。包帥順著悠揚的笛聲,他看到房東聾啞人李叔,站在不遠處,專注地吹著笛子,一滴一滴金瑩的淚珠順著他那蒼老的臉頰像斷線的珠子流了下來,這時整個大廳一下子安靜了,除了優美的笛聲之外,就是喇叭裡傳來的“請前往安徽蕪湖去的旅客,到三十號出口,做好登車準備。”
這時,只見在三十號出口處的李小曼,站了起來,流著眼淚,向著她的養父跑了過去,她一邊奔跑著,一邊轉頭對她的親生父母親說:“爸,媽你們先回去吧,過兩天,我帶著養父一起去看你們。”
在包帥去北京上學後,他的父親包小山又一次返回了深圳。
為了完成學業,包帥節假日去飯店做短工,上學期間,去校外做兼職家教。在他大二那年開學不久,在上體育課時,包帥在操場上嘔吐不止,被老師及時送進了醫院,經醫生診斷,包帥患上急性腎炎。
學校打電話給包帥的父親,在深圳做生意的包小山,讓他儘快趕到醫院,說他的兒子生病了。可幾天之後,看包小山還沒有回來,學校的老師再打電話聯絡,原來的電話已經打不通了。
最終包帥的醫療費用是學校給墊付的,在同學和老師的照顧下,包帥的身體漸漸恢復了健康,不知什麼原因,自這次生病後,包帥總感覺右腿行走時有些不便。
從包帥生病到出院,作為他唯一的親人——他的父親包小山始終沒有出面,也沒有打個一次電話 ,自此包帥抹去和他父親包小山的所有聯絡。
包帥出院後,他的姑姑包倩來學校看過他一次,臨走時給包帥五百元錢,包帥拒絕著說:“姑,感謝你來看我,我有錢,你拿回去吧。”
二零一七年包小山和他現任妻子離婚後,被淨身出戶,離開深圳回到上海,住在他父母生前的兩居室房子裡。
包小山在和牌友一起打牌時,因心肌梗塞發作,被送進醫院,在醫生要見他的家人時,他才想起了他的唯一的兒子包帥。出院後,他四處打聽兒子的下落,最終透過包帥一個大學同學,才得知他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在北京中關村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具體是哪一家,同學就不清楚了。
包小山曾兩次去北京中關村,也沒有找到兒子包帥。
二零一八年春節剛過,包小山在樓梯間又一次暈倒,雖然命被搶救過來,但醫生告訴他說,他的心臟功能已經大部分喪失。在他生命隨時都可以終結時,他想見到兒子的心情越來越迫切,在醫院醫生的幫助下,請來了《生活早報》的記者洪玲,希望能給與包小山一些幫助。記者洪玲一邊安慰包小山老人,一邊埋怨著說:“叔,我不是說你,你這個父親做得真是太不稱職了。”
半月之後,洪玲來到醫院見到包小山說:“叔,我們透過尋找,你的兒子是找到了,但他堅決不見你,希望你能理解,我們盡力了。”
這時包小山老淚縱橫地拉著洪玲的手說:“我理解,自我和他母親離婚後,他受了近三十年的罪,我傷他太深了,只要他過得好,我就放心了。”
記者洪玲望著滿眼充滿期待表情的包小山說:“叔,透過你兒子包帥的同意,我給你錄了他的一段影片,你看看吧。”
在一個廣場上,包帥右腿走起路來有些僵直,厚實的背影,看上去像一個老人,這時影片中傳來了包帥的聲音說:“他既然生下我,又不養我,在我最需要父親的時候,連一個電話也沒有,現在見面還有什麼意義,在我的心裡,從來就沒有爸爸,只有媽媽。”
病床上的包小山,看著影片中包帥的背影,痛哭著說:“兒子,都是爸爸的錯,原諒我吧,我對不起你和你的媽媽,下輩子,我做牛做馬,報達你們。你不見我,我也不恨你,因為是我傷你太深了,請原諒爸爸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