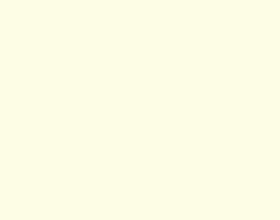翦伯贊(1898—1968),維吾爾族,湖南常德人。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傑出的教育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翦伯贊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七七事變後,任南遷的北平民國大學教授,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等,並任常任理事,出版《歷史哲學教程》一書。1938年,在長沙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積極參加抗日救援工作。1939年3月,前往湘西漵浦民國大學任教,團結進步學生,與國民黨反動派做鬥爭。1940年2月,翦伯贊任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兼《中蘇文化》副主編,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進行學術講演。1943年,翦伯贊完成了《中國史綱》(第1卷)和《中國史論集》(第1輯)的寫作。
新中國成立後,翦伯贊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歷史研究》《考古學報》編委,並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翦伯贊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他治學嚴謹,著作宏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並主編了《中國史綱要》。
曾有學者提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譜系中,被史學界尊稱為“馬列五老”的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構成了第一方陣。他們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推動者和建設者,而且在不同的史學領域均取得卓然超群的成就。“五老”在治學的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終生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職志。但是,這不等於說“五老”在治學上沒有自己的特點和個性。恰恰相反,他們的治學特點和個性都極為鮮明。可以這樣說,他們是以不同的治學特點和個性向著同一個目標,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了相互促進的合力。就翦伯贊而言,他的治學特點和個性,鮮明地體現在理論建樹上。翦伯讚的史學思想,結合中國歷史實際,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論題範圍,推進了對許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特別是在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建設過程中,翦伯贊作出突出貢獻。他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歷史相結合有關論題的探索,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關係的見解和主張,對於“史論關係”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觀點,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源,而且至今還具有發人深思的意義。
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先驅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正式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是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的首次大規模實驗,初步塑造了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史學,又不同於實證史學的全新的學術正規化。不消說,儘管論戰中的各家各派都聲稱以唯物史觀、辯證法為武器,但難免魚龍混雜。即使對於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也難以避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偏差。但是,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的成績是第一位的,其對於馬克思主義全面進入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是第一位的。因此,對於這次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家均給予高度重視,並及時地作了總結。其中,翦伯贊為總結論戰經驗教訓而撰寫的《歷史哲學教程》一書,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專著。該書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進行了系統闡述,重點論述了“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的關聯性”“歷史的實踐性”等理論問題,具體包括“一般性與特殊性之辯證的統一”“客觀條件與主觀創造之辯證的統一”“下層基礎與上層諸建築之辯證的統一”等論題。這部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很突出的哲學色彩,深化了李大釗先生所奠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中外歷史年表》
為深化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使之更加科學地發揮指導中國歷史研究的作用,翦伯贊在書中剖析和批評了機械論的研究傾向。機械論者將歷史發展完全等同於經濟發展,“完全否認意識形態乃至政治形態對現實社會經濟所起的反作用,以及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相互影響作用。在歷史發展的關係中,排去了活生生的人類意識的創造作用,把人類歷史的發展,作為與人類無關的死板的社會經濟之自然主義的發展”,從而回到了“進化論的舊窠”。翦伯贊指出,機械論與觀念論殊途而同歸。就意識形態來說,觀念論者分離意識與存在的關係,顛倒它們的作用;機械論者則抹殺意識對存在的影響作用。他們的觀點雖然不同,甚至相反,但其無視存在與意識的適應性這一點是相同的。顯然,翦伯贊既堅持了唯物主義,更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只有辯證唯物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顯然,將唯物史觀歸結為單純的經濟史觀,是錯誤的。其實,這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原本不是問題。恩格斯就曾經對將馬克思主義單純理解為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做過明確而嚴肅的批評。但是,考慮到當時的具體情況,機械唯物主義的傾向又是很難避免的。因此,翦伯讚的論述具有校準方向的意義,這對於全面而科學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在史學界的順利推進,都富有建設性的積極意義。
繼1938年的《歷史哲學教程》之後,翦伯贊在1943年又發表《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現出馬克思主義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的水準。比如,翦伯贊高度重視漢族與其他民族歷史的關聯互動,提出“真正的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之總和”。他還強調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一方面,“中國史的變動,往往影響世界史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史之於世界史,正猶細胞之於人體”。他指出,一般性必須與特殊性相結合,研究中國史,應該從發展之一般法則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時,也應該從特殊性中去發現它的發展之一般法則。他提出不應以分析兩大敵對集團的關係為滿足,應關注中間社會群與兩大集團的關係。他更注意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如宗藩的混戰、外戚宦官的專政。他還看重內外矛盾的轉化,邊疆民族進入中原社會,是外在因素引發中原社會經濟的變革。他提出,考察意識形態發展的方法,是把那些從社會經濟基礎上蒸發出來的思維(如哲學、宗教)還原到它們的出發點,把那些由思維而再凝固為形象的東西(文學、繪畫、雕刻等)再蒸發為思維。翦伯讚的這篇文章,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深入的學理和銳利的文風,映現出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成熟與完善,因而受到廣泛讚譽。
新中國成立後,沐浴著新中國的春風,翦伯贊意氣風發,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投身於新中國的史學建設。1961年,翦伯贊為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中國史綱要》擬定的提綱——《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結合史學界關心的問題,再次就如何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指導中國史研究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系統性想法,供史學家參考和討論。翦伯讚的意圖,是希望儘快建立起與新中國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建構新的史學正規化。應該說,這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責任擔當精神的體現。為此,他對涉及史學發展的諸多根本性問題作了系統而深入的思考,希望史學界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形成共識,從而儘快將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態建立起來。翦伯贊正面闡述關於“如何處理歷史上的階級關係”“如何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如何處理歷史上的國際關係”“怎樣對待發展觀點”“怎樣對待全面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歷史人物”“政治、經濟與文化”和“理論、史料與文章”8個方面的問題。這8個問題,既內蘊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內,也植根於新中國的現實語境,是重新編寫中國通史需要預先解決的理論問題。應該說,翦伯讚的許多思考是很深入的,觸及一些深層次問題。例如,關於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農民階級覺悟等問題,翦伯贊提出,不能將農民戰爭等同於無產階級革命;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農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翦伯贊肯定歷史上農民反抗的積極性和進步性,但沒有忘記其時代侷限性乃至落後性。他主張秉持全面的觀點,用兩隻眼睛看歷史,既要看到光明面,也要看到黑暗面。他說,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黑暗總是主要的歷史內容;反之,任何黑暗時代,也不能沒有一線光明。翦伯贊還提出,從事研究要分析與綜合相兼,“分析不怕細緻、深刻,否則不能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綜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則不能顯出歷史的全貌、線索”。分析時要鑽進個別歷史事件中去,用顯微鏡去發現問題;綜合時要站在個別歷史事件之外,用望遠鏡去觀察歷史形勢。翦伯讚的觀點引起史學界廣泛關注,引發了人們的深入思考。儘管人們對翦伯贊見解的理解並不相同,但是,翦伯贊積極探索的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真誠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風範,都是令人敬仰的。
宣講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
在史學理論體系中,“歷史主義”是一個頗有歧義的概念。有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有其特定的含義與指向。翦伯贊所宣講的歷史主義,毫無疑問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但是,單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來說,如何對其理解和運用,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1951年,范文瀾針對其《中國通史簡編》中“借古說今”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已經觸及怎樣科學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原則的基本問題。次年,翦伯贊發表《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一文,則在理論上將歷史主義問題明確提出來。
《中國史綱》
翦伯贊批評了當時評價歷史人物中出現的兩種非歷史主義傾向。一種是脫離具體歷史條件,用現代工人階級的標準去要求歷史人物。翦伯贊指出,這種傾向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原則,因為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出發去評價歷史人物,就是“要嚴格聯絡到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另一種傾向是,對歷史上正面歷史人物,特別是勞動階級的代表無原則拔高,甚至用現代詞語來描寫,使那些歷史人物現代化、理想化。翦伯贊認為,這兩種非歷史主義的傾向,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則。
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原則出發,翦伯贊告誡說,對統治階級及其傑出人物,不要依據簡單的階級成分一律加以否定,要按照他們對歷史所起的作用和對歷史所作貢獻的大小給予應有的歷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評價。此外,在論述農民戰爭時,不要忘記農民戰爭發生在封建時代,不要忘記農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記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
在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效與政治功能方面,翦伯贊指出,不要試圖把黨的政策、號召和口號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不該用當前黨和國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去描述封建社會的民族關係。翦伯贊說,必須處理好政策和理論的關係,要認清政策的時代性、特殊性和具體性,科學地處理好歷史研究和現實作用的關係,避免隨意改寫歷史。
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說,歷史主義所需要回答的核心理論問題,是其與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的關係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堅持的觀點,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將階級觀點看作唯物史觀的唯一觀點,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僅僅看作階級分析方法,也是不科學的,並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實際。在這方面,1958年的史學大躍進或“史學革命”,就出現了對階級觀點的誤解和濫用。對此,當時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表示不贊同,並提出了批評。這樣,就引發瞭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關係的問題。翦伯贊就此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引發了廣泛注意和討論,並被視為主張歷史主義的代表。
翦伯贊當然並不反對階級觀點與階級分析方法,他認為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並不衝突,因為二者本來是結合在一起的。既然階級是歷史上的階級,那麼,分析歷史上的階級狀況,自然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觀點。在這方面,恰恰是馬克思為後人樹立了典範。他說,如果只有階級觀點而忘記歷史主義,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歷史主義而忘記了階級觀點,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對歷史事實做出全面公平的論斷。離開歷史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翦伯贊批評階級觀點的片面化,一旦片面化,就會對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剝削制度一概打倒。他說,有人基於古代史都是階級社會的歷史的認識,“把全部中國古代史說成是漆黑一團,說成是一堆垃圾,說成罪惡堆積”,這顯然是“非歷史主義的”,屬於虛無主義的態度。針對當時“打破王朝體系”的做法,翦伯贊強調,不管按照什麼體系編寫中國通史,都不應該從中國歷史上刪掉王朝的稱號。他不反對“打破王朝體系”,但強調“‘打破王朝體系’是打破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從歷史上消滅王朝的稱號。王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消滅的,也是消滅不了的。……歷史學家無權根據自己的愛憎從歷史上消滅具體事實”。顯然,翦伯讚的主張是正確的。
事實表明,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大討論,促進了中國史學界對於唯物史觀的深層理解,提升了人們的認識。當時參加討論的雙方為了追求真理,都充分論述了各自的主張。這是一場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的討論,並沒有本質上的分歧,因此都共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作出貢獻。其中,翦伯贊先生的貢獻,是後人不應該忘記的。
“史”“論”結合的典範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在與實證史學及非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競爭中不斷成長壯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貫強調理論指導,反對“史料即史學”的觀點。圍繞這一主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發表了許多論著予以闡明。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翦伯贊對理論與史料關係問題的考察非常全面而深刻,因而影響極大。首先,翦伯贊反對將歷史學降格為史料學,把考證當作歷史學,特別是陷入煩瑣考證之中不可自拔。他認為,煩瑣的考證必然要混淆歷史發展規律,因為在歷史程序中,常常會有一些細微的事件夾在當中,如果對於每一個細微的事件都加以考證,就必然會為了注意到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離開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其結果,讓人們看不見歷史全貌、歷史骨幹和脈絡,看不見歷史的發展和發展的動力,聽不到歷史跳動的脈搏,更看不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會使人的頭腦侷限在最狹窄的範圍內,使其僵化,使人失去掌握歷史全域性的能力。他提醒說,如果不從這種煩瑣考證中解放出來,史學家就會糾纏在無窮無盡的細微事件上面而不得脫身,就會像鑽牛角一樣,愈鑽愈窄,最後的結果是此路不通。
翦伯贊在《歷史科學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史料之於史學,正像磚瓦之於房子,布帛之於衣服,我們可以說,沒有磚瓦蓋不起房子,沒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們能夠說磚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嗎?從史料到史學,正像從磚瓦到房子,從布帛到衣服一樣,中間還要經過一系列的複雜的勞動過程。……而這種功夫是一種極其細緻的思考過程,只有經過這種過程,才能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才能把材料變成理論,才能變史料為歷史。”他認為,蒐集史料只是替歷史研究準備材料,並不是歷史學的終極目的。歷史學的任務總不能就是編成匯抄,它應該是一種分析史料的科學。因此,就應該學會分析史料,把史料變成歷史。翦伯贊一再強調,不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史料等於廢物。資料是一匹野馬,沒有馬列主義理論就無法駕馭。據鄧廣銘回憶,翦伯贊經常建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年以上的教師多學理論,說史料好比一堆銅錢,理論則好比串錢用的繩索,必須運用馬列主義把散漫的史料貫串起來,使之形成系統,用來闡明歷史問題的實質和真相。
此外,翦伯贊高度重視史料工作。他指出,研究必須用很多時間去搜集資料,鑑別資料,透徹地掌握資料,用唯物的觀點、辯證的方法分析那些經過鑑別的、透徹掌握了的大量資料,然後才能對於一個歷史問題作出概括或結論,而且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概括或結論。在翦伯贊看來,“只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歷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他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他的細節,在史料的昇華中,顯出他的發展法則”。他還認為,如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運用史料,則史料愈豐富愈好,史料愈豐富,得出的結論就愈益正確。1956年,翦伯贊在巴黎的青年漢學家年會上總結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時說:“觀點和立場的不同,並不妨礙對同一問題的討論。因為無論如何,我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這就是史料。”也就是說,史料是展開學術討論的基礎。翦伯贊還發表《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史料的收集與辨偽》《略論收集史料的方法》等專門闡述史料問題的文章,討論相關問題,見識和水平極高。
對於一度出現的“以論帶史”口號,翦伯贊表示不認同,提出“史論結合”的主張。他說:“歷史是具體性的科學。論證歷史,不要從概念出發,必須從具體的史實出發,從具體史實的科學分析中引出結論。不要先提出結論,把結論強加於具體的史實。”因為一般的理論和概念只是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不是出發點。理論和概念是研究具體史實得出來的結論。如果從理論和概念出發,那豈不是先有結論,然後按照結論去武斷歷史?豈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抽象到抽象?這種研究方法不是辯證法而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所以,“以論帶史”只會將史學研究引入歧途。他還說:“‘以論帶史’的提法,意味著研究歷史要從理論和概念出發,不從具體事實出發。”翦伯贊批評了當時以引用經典著作為能事的傾向,似乎史學論文中引用經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則理論性愈高,史學家的全部任務就在於挑選經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於一再重複這些文句。翦伯贊認為,正確的做法是“把史料溶解在理論之中,或者說把理論體現在史料之中,使觀點與材料統一”。當然,理論與史料的有機結合,不是那種“寫一段理論,再寫一段史料”或者“寫一段史料,再寫一段理論”形式上的結合。翦伯贊提出的“史論結合”為史學研究依循健康的路向發展提供了指引,至今仍是多數史學研究者信從的規則。正因如此,翦伯贊被史學研究者稱為整合史觀與史料“兩大學術譜系”的鉅子。
當下,歷史學的繁榮已遠遠超越翦伯贊所處的年代。從近代中國史學發展趨勢來說,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主流和歸宿,凝聚和承載著一批先進學者的智慧和學識,充滿關乎歷史學根本問題的理性思考和成果。翦伯讚的理論遺產是這些理論思考和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不斷重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正規化的構建與興起研究”(19AZS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