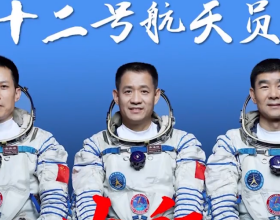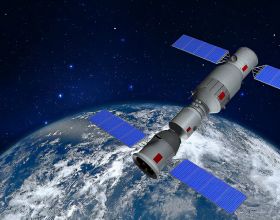我叫花墮,養在十二院裡。
所謂十二院,就是汴京最大的青樓。十二院裡有我十一個姨娘,個個貌美如花,好似天仙,但最美的還是我娘。我娘花見慚是整個汴京出了名的花魁,依我看,莫說汴京,便是整個大晁也找不出比我娘還貌美的女子。聽聽我孃的名字,花見慚,就算是那嬌豔欲滴的花兒見了我孃的姿容,也不由得生出幾分慚愧。
「你娘是楊貴妃嗎?居然有羞花之姿。」
「小麵糰,你怎麼能這麼說我娘,楊貴妃可是年紀輕輕就沒了!」我猛地站起來,指著對面的人。
那小麵糰一張小臉白淨無比,兩隻眼睛像黑葡萄掉進清泉裡,水汪汪的看著我,整個人簡直是大寫的無辜,「阿墮,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什麼意思!」
小麵糰剛準備開口,一隻雪白纖長的手伸了出來將他的耳朵提起來「江逐,你又欺負妹妹。快教妹妹習字去,不許吵著娘和姨娘們歇息。」
江逐站起來,恭恭敬敬地應了聲是。
這手的主人是江逐的母親、我孃的好姐妹月槐姨娘。月槐姨娘雖沒有我娘那麼那麼那麼的漂亮,但卻生了一雙纖纖素手、一副修長脖領,不施粉黛的臉上一雙杏眼一對煙眉,顧盼之間無端地叫人生出濃濃憐愛來。
江逐的眼睛和月槐姨娘像了十足十。可我娘告訴我江逐不是月槐姨娘生的,是十二院的姨娘們撿來的。
那年寒冬臘月,滴水成冰。汴京城的早晨冷風似刀,花紅柳綠了一夜的十二院絲竹聲剛剛歇下。十二位頭牌正要歇息,便被一陣啼哭聲驚起。裹著披風到門口一瞧,只見花緞被包裹著一個小嬰兒,正紫著一張臉費力嚎叫,不知是凍的還是餓的,聲音漸弱。頭牌姑娘們面面相覷,十二院的鴇母陳媽媽哄散了姑娘們,只有月槐阿姨將小嬰兒抱起來,貼著他的小臉,「你瞧,他哭的多傷心啊。」
從此小嬰兒便被十二院收養,姑娘們還請了最有文化的頭牌,也就是我娘,給他起了個名字——江逐。
「他是被棄逐的,且是月槐撿的,就隨著月槐姓吧。」我娘如是說。
後來我長大些,很是憤懣地問過我娘,為什麼給他起了個這麼好聽的名字,卻給我起了這麼個怪名字。
那時我娘正在和秀川姨娘朝霧姨娘擲骰子玩,臉上貼滿了紙條子,對著我不耐煩的揮揮手,「我本是不願生你,想將你墮了的,所以就叫花墮咯。」
我哇的一聲哭了,哭的很大聲。我五歲的人生中從未有過這樣的傷心事。
後來還是小江逐過來拉了我的手,給我吃芙蓉糕,帶我去習字,我才將這晴天霹靂拋諸腦後。
我愛習字,可我的字總是寫不好。就算有江逐手把手的教我,我卻還是寫的像一通鬼畫符。
就像現在,他不過比我大半歲,卻像個小大人搬繞在我身後,握著我的手,一筆一劃地臨王右軍的帖。
手握在一起,臉自然也離得近。我偷偷抬眼看他,他生的白皙,兩道濃眉臥在眼上,秀挺的鼻樑下是紅的像擦了胭脂的唇。
真是見了鬼。我使勁搖搖頭。還好我是十二院頭牌花魁花見慚的女兒且比他生的還好看(自認為),否則我小小年紀就要被美色誘惑了。
江逐見狀垂眸一笑,「阿墮,你瞧你,吃了芙蓉糕也不知道擦擦嘴。」他伸手替我抹去臉上的糕渣,「阿墮生的真好看,我以後定要考取狀元,八抬大轎來迎娶阿墮做我的妻子。」
我不由得就臉紅了,嬌羞扭捏之間輕輕推他,「誰要做你的妻子!」
可話音未落,只聽轟的一聲,江逐被我推倒在地,碰翻了梨花木的架子,正皺著眉頭輕輕觸碰左手。
響動之間,我娘和姨娘們通通跑來,見到江逐那副樣子,而我像個傻大鵝似的張著嘴站在一邊。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肯定逃不掉了。
果然,我立馬被請上了太師椅罰站。我娘在一旁叉著腰恨鐵不成鋼的罵我,她罵我女生男相,沒有承得她半點美豔皮囊;她罵我小小年紀,飯量以一敵三,還好個子長得高,否則新做的浴桶都塞不下我;她罵我不學無術,連汴京城最出名的先生都無奈我何,一點也不像她這般冰雪聰明…
「噗嗤。」
我娘口乾舌燥的抬起頭,看見一旁看好戲的八九個姨娘們紛紛掩面而笑。彈得一手好琴的雲棲姨娘笑問她,「阿慚,你當真冰雪聰明,機敏好學嗎?」
不問還好,一問連我也忍不住了,站在太師椅上就鵝鵝鵝地笑了起來。我娘惱羞成怒,轉過身來扯我的衣裳,繼續罵我,「你就跟你那個莽夫爹爹一樣,空有一身力氣,再無半點本事。」言語間還繼續扯我,想將我扯下椅子,好好教訓一頓,「當年若不是他有點功夫,我才不願意跟他呢。」
周圍的姨娘又笑了。不對,十分不對,這不是去學堂的車,快放我下來!
說到我爹,這可是個傳奇人物(我自以為)。雖然我從未見過他,但我娘口中的他勇猛無比,秀川姨娘口中的他英俊瀟灑,箏意姨娘口中的他重情重義。可是,若真的重情重義,為何從不見他來看我娘呢?再不濟,帶我這個女兒出去吃頓好的也行啊。我太想去汴京城裡逛一逛了,可我娘從不讓我出去,她說我兒細柳扶風、盈盈弱質,若帶出去了被街上的莽夫嚇到可怎麼好。我為了向她證明我絕非那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當天就將挑釁我的廚房二嬸家的胖兒子揍的鼻青臉腫,惹得二嬸鬧著要罷工,還是我娘塞了好些碎銀子,江逐給小胖寫了半個月的字才罷休。從那之後,我娘更不願意帶我出去了,她苦口婆心的勸我,「兒啊,別再折騰了啊。娘掙點銀子不容易,彈琵琶手指都快彈斷了,這帶你出門還不夠賠人醫藥費的。」
我趴在窗戶邊看著江逐上學堂去,流下了悔恨的淚水。我懂,我都懂,我不過是一條可憐的酸菜魚,又酸又菜有多餘罷了。
我想我爹了,若是他在,一定不會不捨得賠人醫藥費。
月槐姨娘帶著江逐回十二院的時候,我正站在太師椅上昏昏欲睡。在此之前我娘扒拉我半天沒扒拉動,我怕再像傷了江逐一樣傷了她。她拼命的拽我衣裳,我下盤很穩,穩如泰山,不動如山,甚至在太師椅上紮起了馬步。她氣喘吁吁,但好在萬事開頭難,只要肯放棄。隨著秀川姨娘一聲招呼,我娘立刻頭也不回地投身向了她最愛的活動——擲骰子。
江逐輕輕地將我拽醒,「阿墮,你不用擔心,我沒事。」他完好的右手提了一包糕點,「這是徐服記新出的蜜糖糕,咱們一起嚐嚐。」
我頓時不困了,立馬跳下了椅子跟他走了。蜜糖糕真好吃,就是吃多了有點膩,還有些困。想來天底下吃完就犯困的應該不止我一個,我就放心的睡了,完全沒管我和江逐待在一起,在他的房裡。
第二天,天剛矇矇亮,江逐就已經起床溫書了。我濛濛鬆鬆地醒來,見他一身天青色長衫,右手執卷立在窗前。背影如松柏般挺拔。不知不覺間,我的小少年已經長的比我還高了。
啊呸!不要臉的花墮,怎麼叫你的小少年。
我看著他背影露出了神秘的微笑,我知道怎麼出去了!
江逐在我的百般糾纏之下,終於同意了我絕頂聰明的主意。他給我找了一套月白長衫,又將我的長髮束在頭頂。銅鏡裡看去,不正是一個劍眉星目、唇紅齒白的翩翩佳少年。我瞧著鏡子裡的自己滿意地點點頭。娘總是說我長的和我莽夫爹爹一模一樣,半點也未有她的影子。可這也沒見得有什麼不好嘛!至少在女扮男裝這一方面,我花墮從沒輸過誰。
街市上真是熱鬧!我瞧著那些連片的賣各種各樣小玩意的商鋪簡直都要走不動道。難怪我娘不願意帶我出來,我的確有這個信心有這個能力把她的積蓄花光。江逐跟在我身後,時不時地拽住我免得跑丟。
路過一家武館時,江逐頓了頓,抬頭看向那武館的牌匾。我見狀也湊了過去。
「嘖嘖,這字寫的極差,形如枯枝。江逐,我瞧還不如你寫的呢。」為了報答和封口,我虔誠的拍著馬屁。
他一笑,眉眼彎彎甚是好看,還未說話就聽見身後有人嚷嚷著,「你們這兩個黃口小兒,口氣也忒大了。這可是當朝驍勇大將軍季賀的墨寶啊!看得懂嗎你們?」
我深吸了一口氣,仔細欣賞,最終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那人來了脾氣,偏要與我們爭執個一二出來,言語之間還推推搡搡,令我十分不爽,若不是我們沒有銀子賠,我定打他個落花流水,哼。
「毛都沒長齊,就敢評驍勇將軍的字,快回家多讀些書吧!」,那人將江逐用力一推,我趕緊撲過去美救英雄。正巧街心奔來一匹快馬。馬上的人狠狠勒住韁繩,駿馬仰天長嘶,前蹄凌空而踏,才堪堪在我們面前停下,沒有踩著我和江逐奔過去。
經此一遭,馬上的人差點摔下來。他翻身下馬,對著我怒目圓睜,「你們二人也太不小心了些,這不注意可是要出人命的!」
我剛要找推我們的人,回頭一瞧,哪裡還有他的蹤影。
再看看面前的小公子,披一身鎖子鎧,隱在晨光裡的臉如刀削斧刻般堅毅,雙腿修長,牽著韁繩的手骨節分明,真是格外好看。我看的入神,連江逐把我扶起來也沒注意。
那小公子見我們一言不發,皺了皺眉,剛要開口,只聽他身後渾厚的嗓音發問,「齊越,這是怎麼了?」
小公子恭恭敬敬地轉身行了個禮,「將軍。」
將軍。我朝只有一位大將軍,那便是我剛剛議論過的驍勇將軍。果真是不能背後說人,這不說曹操曹操就到了。
驍勇將軍季臨坐在馬上,居高臨下。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忽然開口問道,「敢問這位小公子,家住何方?齊越的馬驚了你,我們該登門賠罪才是。」
「朝花巷。」
我還未開口,江逐突然說道。
回去的路上我問他為何要騙人,江逐捏捏我的臉,「小笨蛋,你若告訴他我們住在十二院,阿慚姨娘知道了你偷跑出去,定要罰你了。」
我恍然大悟,痛定思痛,暗下決心日後一定要將江逐的保鏢工作做好,再也不能發生今天這樣的失誤。
十幾歲的小少年總是長得特別快。十月金桂飄香時候我仔細一瞧江逐,突然發現他不知什麼時候都比我高了整整一個腦袋,身子骨也變得結實有力。我仔細一問才知道,原來月槐姨娘不僅給他延請名師指點功課,還請了武館的師傅教他習武。我好生羨慕,磨了我娘足足半個月,她才點頭同意我去看一場江逐的武術課。
我看他一身短打勁裝,動作間行雲流水,自己也跟著瞎比劃。
「小公子看著像是對武術很有興趣。」
我回頭一看,說話的竟是驍勇將軍。他饒有興味地看著我道,「莫不然小公子來我府上投作親衛,我親自指點你可好?」
天哪,大將軍親自指點我,這是汴京城多少男兒的夢想啊!但我不能答應,我娘告訴我,女孩子家家最重要的就是矜持。
於是我義正嚴詞地拒絕了他,「多謝將軍看重,但我不能去,我娘定會罰我的。」
他聽我這麼一說,彷彿興致更濃了,表示他可以登門拜訪,定會說服我娘。我糾結極了,心裡好像出現了兩個小人在打架,一個說「你就就讓他去十二院一趟吧!他親自去,娘肯定會同意的!」另一個說「好呀!」
大將軍果不食言。當晚華燈初上,十二院就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貴客,當朝驍勇大將軍季臨。並且他指名要見十二元的頭牌花見慚。
我不知將軍到底說服我娘沒有,只知道當晚回來我娘不住地嘆氣,還唸叨著什麼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那這事到底成沒成啊?
第二天一早,我剛睜眼,就看見我十一個姨娘還有我娘團團圍在我的床邊。向來多愁善感的撫霜姨娘還在用帕子拭淚,連最愛笑的憐星姨娘都一臉嚴肅。
我慌了,我徹底慌了,我不會得絕症了吧?
正當我顫抖著雙唇想要問的時候,我娘期期艾艾地開口了,「兒啊,從今日起你不必住在十二院了。」
不是絕症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咧著嘴問她我是不是要去將軍府當親兵了。我娘搖搖頭。
還是亦澶姨娘開了口,「墮兒要去將軍府當小姐了呢,日後可千萬不要忘了十二院的姨娘們啊。」
「讓阿墮記得咱們這些人做什麼?」追鶴姨娘嗔怪地拍她。
「什麼小姐啊?昨日大將軍分明和我說好要去當親兵的,還要親自指點我武功呢。」我說道,今日的姨娘們都好奇怪啊。
盼遙姨娘摸摸我的腦袋,「那驍勇將軍季臨就是阿墮的爹爹,爹爹要接阿墮去過好日子了呢。」
「是啊,阿墮離了十二院,就是正經的將軍府二小姐了。」含煙姨娘也用帕子擦起了眼淚。
「我不要去將軍府做什麼二小姐!我就要待在十二院和娘還有姨娘們在一起!」
什麼二小姐,我才不稀罕呢。
可這次我娘一點都沒遷就我,平日裡我站太師椅時幫我說話給我揉腿的姨娘們這次也都沒幫我。連江逐這小子都不知去哪裡了,連著半個月沒見他的影子。我整整哭鬧了半個月,卻還是在十一月初二那天,被接去了將軍府。
在將軍府的第一天,想我娘。
在將軍府的第二天,想我娘想我娘。
在將軍府的第三天,想我娘想我娘想我娘。
我想我錯了,如果要和娘還有姨娘們還有江逐分開的話,我還是不要當什麼小姐,也不幻想著當什麼英雄了。沒有他們,我一人在這華貴的將軍府有何意趣。
我抬起頭,正準備將眼淚逼回眼眶,突然看見門邊趴著一個鵝黃衣裙的姑娘。想來這就是我的姐姐、將軍府的大小姐季韻寒。她狗狗祟祟地溜進來,手裡提著一包糕點,那味道我一聞就知道,定是徐服記。
她麻溜地坐在桌邊,一邊拆著那袋糕點一邊唸叨,「你剛來將軍府就病了,我見你病的都清瘦了。這是我娘特意叫張媽媽去買來的,叫我偷偷塞給你呢。我娘被祖母叫去聽訓話了,她且叫你不用擔心,定想辦法將你娘從十二院贖出來。」她說著遞一塊糕點到我嘴邊。我原本下定決心,不吃將軍府一粥一飯,可這剛出爐的還熱乎著的桂花糕實在是太香了,我的眼淚不爭氣地從嘴角流了下來。
季韻寒見我饞的流口水,不由得一笑,與我七八分相似的臉上浮出兩個小酒窩。她將糕點塞進我嘴裡,給自己也塞了一塊,「你以後就叫我阿姐好了。我一個人在這偌大的將軍府早就無聊啦,來你這麼個漂亮的小阿妹陪我,我定會對你十分好。」
她怕我吃的噎著,還給我倒茶。她給我講將軍府的趣事,講她爹打碎了她娘最愛的煙青雲紋盞,被她娘追著在書房繞了三圈,最後擰著耳朵糾出了書房;講她年幼時愛捉蟲子玩,便猜測祖母也十分喜歡,偷偷捉了一隻藏在祖母的茶盞裡,嚇得祖母捂著胸口喘了好半天才緩過來,最後被罰在祠堂跪了半天;講她偷偷爬到樹上去摘柿子,結果正被祖母身邊的劉媽媽瞧見,一聲呵斥,嚇得從樹上摔下來,足足躺了一個月……
我聽得入了神,若是我早認識季韻寒,定會告訴我娘,這世上不止阿墮一個頑皮的孩兒,也不是人人都像江逐那樣聽話懂事的。想到我娘和江逐,我又傷心了,季韻寒見我又苦了臉,便安慰我,「你放心,爹爹去了邊關很快就回來。等爹爹一回來就把你娘接到府上來。」
「真的?」
「真的!」
可我和阿姐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爹爹的確很快就回來了,但祖母不願意我娘來府上,「煙花之地的風流女子,怎配待在將軍府?」祖母一邊呵斥父親一邊看了我幾眼,「能讓清禾回來,已是被人笑話了。」
對了,現在已經沒人叫我花墮了,我改了名字,叫季清禾。阿姐告訴我,爹爹回來那晚和嫡母在書房想了許久。爹爹說,「不然,就叫季龜,哦不,季歸吧。阿墮現在才歸入我將軍府。」
「……」嫡母沉默了。
「……」阿姐也沉默了。
最後還是身為當朝太傅之女的嫡母謝大娘子謝書宜替我想了這個名字,「官人此生惟願天下太平、海晏河清。不如就叫清河吧。」
「清河,清河。不錯。只是這河……這樣吧,阿墮如此能吃,就叫清禾。」
我&*%¥……#@
從前我娘總說爹爹一介莽夫,胸無點墨,我總不信,現在我信了。
有了祖母的阻攔,娘沒法入府。可後來我和阿姐偷偷鑽狗洞出去過幾次,次次去了十二院,娘總不願意見我,說什麼身份有別,我才知道,不只是祖母不願意娘入府,娘自己也不願入府了。當初和我爹相識,娘以為他是自由身,這才有了我。娘雖為風塵女子,也自有她的一番風骨。哼,什麼驍勇大將軍,我看就是個渣男!身份有別個屁,就算我是當朝公主,我娘也是十二院的花見慚!
嫡母見我興致缺缺,主動提出讓小賀將軍帶我和阿姐去蹴鞠。
可我沒想到,原來小賀將軍就是那個!那個騎馬差點踩死我的少年郎!他還是那麼好看!但他身邊的小公子長得也甚是英俊,玉樹臨風、面冠如玉。
唉?這不是江逐嗎?
他負手而立,一雙清澈的眼含著笑盯著我。可我還沒來得及跟他打招呼,就被阿姐拉走了。
蹴鞠是我的強項,雖然從來沒學過,但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會(比如我)。我在蹴鞠場上大殺四方,那些世家的公子哥和小姐們都不是我的對手。我正準備拿下本場最後一個賽點,突然餘光瞥見賀齊越在和我阿姐拉拉扯扯。阿姐甩開他的手捂著臉跑遠了。
個狗東西!定是欺負我阿姐了,等我這場踢完了,看我不把他……
至於到底要把賀齊越怎麼樣,我想不出來,也沒空想。因為我剛那一分神,對面戶部尚書家的三公子飛來一腳,那牛皮球直奔我門面而來,狠狠砸在我挺直的鼻樑上。雖然這球分量不重,但抵不住三公子力道大啊!我的鼻子頓時痠痛至極,眼淚混著鼻涕一起流下來。不對,這不是鼻涕,我看著手心裡的鮮紅開始犯迷糊,這是血……
我暈倒了。
沒想到堂堂將軍府二小姐,頭牌花魁花見慚之女居然會暈血。我悠悠醒來,看見阿姐坐在我床頭哭泣。我拽拽她的袖子,「阿姐,賀齊越那廝是不是欺負你了。你不要害怕,等我好了定把他打個鼻青臉腫,五花大綁過來給你賠罪。」
阿姐聽我一說,頓時悲憤交加,滿面通紅。
我懂,我都懂。她一定是被我們比金堅的姐妹情狠狠感動了。
嫡母聽了我在蹴鞠場上的糗事,笑得合不攏嘴。她摟著我說,「我們家清禾啊,是最有能耐的女孩兒。你力氣雖大,但不懂得用巧勁。我明日告訴你爹爹,讓他帶你去演武場觀摩,也好學些招式,日後定不叫那些貴公子搶佔了風頭。」
演武場哎!嫡母真是個好人!別家的女子到了我這個年紀,都在閨房裡學習女德女紅,偏偏我和阿姐像兩匹脫韁的野馬,恣意生長。
聽我這麼誇嫡母,阿姐可得意了,「我娘是最開明不過的了。她身為當朝太傅之女,飽讀詩書不說,更是嚮往做蓋世女英雄。那花木蘭、穆桂英、王昭君,都是巾幗不讓鬚眉!」
演武場上,爹爹將我們交給賀齊越。沒想到我竟又碰到了江逐。
「你怎麼也在這啊?」
聞言,賀齊越像看傻子似的看著我,「他可是敬遠侯家的小公子,為什麼不能在這?」
?我真是離了十二院太久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原來在我被接去將軍府沒多久,敬遠侯鄭觀穹突然去往了十二院,說是尋找當年被奴僕丟棄的小公子。當年府上惡僕蓄意報復主家,將侯爵夫人剛剛產下的小公子用死嬰替換,再將小公子扔到了十二院的後門,這才被月槐姨娘撿了去。只是那奴僕臨終前將這個秘密告訴了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偏偏是個賭鬼,為了賭資以當年小公子的去向為要挾前往敬遠侯府索要銀錢。侯府聽此訊息,上下沸然。當時正在敬遠侯做客的賀齊越靈光一現,突然想起月餘前差點踏在馬下的一位小公子,竟然和敬遠侯的長子鄭措有九分相似。
為了不驚動有心之人,老侯爺攜著夫人前往十二院旁邊的茶樓蹲點了足足半個月,終於碰到江逐前往學堂。見著他的相貌,侯爵夫人涕淚縱橫,當下認定這就是自己當年生下的小兒子——鄭兌。
不是,這敬遠侯好歹是書香世家,怎麼起個名如此草率,對啊錯啊的……
「所以,你現在是敬遠侯家的小公子了?」我問他。
他淡淡一笑,伸手過來捏我的臉,「是啊,阿墮的爹爹現在是教我習武我的師傅了。」
「太好了!那以後蹴鞠場上你得向著我,把賀齊越那小子踢得落花流水!」
「我一直也只會向著阿墮。」他還是笑。
晁合二十三年,我及笄了。這一天,將軍府是人頭攢動,往來祝賀的賓客快把門檻都踏破了。阿姐見我不善於交際,便帶著我偷偷去祖母院裡摘柿子。鑑於阿姐摔過,還摔得特別慘,所以我負責爬樹,她負責張著布在樹下兜柿子。分工合作,任務明確。
是而當我嫡母謝大娘子領著敬遠侯夫人和江逐,哦不,鄭兌來給祖母問安的時候,正碰見了我像個猴子似的掛在樹上,阿姐在樹下朝我擠眉弄眼,髮髻裡還有一片枯葉。從我的角度看過去,他一身月白長袍,浮著銀線織繡出的暗紋,漆黑如墨的髮束在一頂琥珀冠裡,臥蠶濃眉,秋水杏眼,明明是男生女相,可他往那一站就無端的生出一股逼人的氣場。
我看呆了,連柿子樹上的毛毛蟲爬到我的手上都不知道,饒我是個少女英雄,但還沒英雄到阿姐那種程度,我最怕毛毛蟲了。頓時我就大叫一聲,鬆了手,直直往下墜。
按照劇情發展,你們是不是以為鄭兌會衝過來接住我,我依偎在他懷裡,旋轉幾圈,我們就此情定終生?
錯了。鄭兌的確衝過來救我了,可我掉下來的太快太突然,他衝到一半我就砰的一聲砸在地上,阿姐為了怕砸壞懷裡的柿子,還很貼心的往旁邊閃了閃。我躺在地上,看著鄭兌尷尬地收回伸了一半的手,看著嫡母快要憋不住的笑,看著目瞪口呆的敬遠侯夫人,還有抱緊了柿子的阿姐。
我哭了,這回是羞憤的。
我整整一炷香時間沒有理門外的阿姐和鄭兌。直到跑腿的小廝拎著徐服記的蜜糖糕回來。
「吃慢些」,鄭兌伸手擦我臉上的糕渣,「你都及笄了,怎麼還像個小孩子。看看你阿姐,她就比你……」他看著同樣狼吞虎嚥的阿姐,默默嚥下了後半句話。
「及笄又怎麼了?」我問。
「及笄了就能嫁人了。」阿姐口齒不清的說道。
「是啊,正如季大小姐和小賀將軍。」鄭兌輕笑了聲,打趣我阿姐。
?什麼?阿姐和賀齊越?他。她。他們。什麼時候的事!
我這回真的生氣了,徐服記的蜜糖糕也哄不好。那賀齊越就知道欺負阿姐,阿姐還要嫁給他!明天的演武場上我定要殺殺他的威風,好叫他知道我阿姐不是好欺負的。
於是第二天的演武場上,我手持一柄烏金窄劍,賀齊越手握一杆紅纓槍站在我的對面。
「喂,小丫頭。我可不想和你比,這不是以大欺小嗎。」
哼,好你個賀齊越,還沒比試就小看我。士可殺,不可辱!
我不說話,提了劍向他衝去。餘光瞥見阿姐和鄭兌立在場邊嗑瓜子。
幾個來回之間,我越戰越勇,但賀齊越明顯不想和我打了,紅纓槍直直奔我左肩而來想嚇退我,我本是想用劍格開的,但鞋突然滑了一下。所以,當我看見紅纓槍的槍頭沒進我的左肩,我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果然不該穿自己瞎找布料繡的“必勝”襪子,太他孃的滑了。
我倒下了,看見鄭兌和阿姐面色蒼白向我奔來,賀齊越像傻了似的站在一邊,手足無措。我瞥了他一眼,不屑的哼了一聲,就這傻樣,還想娶我阿姐。但是紅纓槍刺穿的左肩真的好痛啊,饒是我花墮一世英名,也忍不住哼唧兩聲。
「真……真……」
鄭兌聞言緊緊握住我的手,輕聲細語地安慰我,「阿墮不怕,我在這裡。」
「真……真他孃的痛。」說完這句話,我雙眼一黑不省人事了。
待我醒來,已經是兩天之後了。睜眼看見我久違的娘和十二院的十一位姨娘團團圍在我的身邊,低聲哭泣。嫡母在一旁哭的最大聲,我娘捏著她的手安慰她,「季夫人,你放心,阿墮這孩子從小就紮實,一定不會有事的。」
我艱難地哼唧出了所有病人醒來都會說的一句話。
「水……」
一屋子的女人靜默了一會,紛紛手腳慌亂的開始找東西。我娘遞了一盞滾燙的茶水、嫡母遞了一碗燕窩粥、阿姐遞來了一盅雞湯、秀川姨娘遞來了葡萄、月槐姨娘遞來了糕餅、亦澶姨娘遞來了帕子……
我好幸福!
雖然我傷口撕裂般的痛,但阿姐告訴我,我娘和姨娘在將軍府和敬遠侯府的幫助下離開了十二院,在翠煙巷開了一家叫十二苑的絲竹館,專門教女子聲樂。聽到這個訊息我高興極了,晚飯都多吃了一碗,阿姐見我沒事也開心極了,多吃了兩碗。我爹看著我和阿姐的好胃口很是欣慰,表示不愧是他季臨的好女兒們。
等我能下地走路的時候都已經開春了,先前我一直在母親院子裡養病,病好些了就回了自己院子。
我看著自己屋裡熟悉的陳設,不禁感嘆:我不在這屋裡,連花草都長得格外茂盛些。轉身間瞧見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檀木盒子,開啟是一封信,鄭兌的筆跡:恭賀阿墮及笄之禮。
信下頭是一對水頭極好的翡翠鐲子。再將信紙翻過來,還是他遒勁有力的字跡: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阿姐跟著進來,見我紅了臉便打趣我,「你剛傷的那幾日,鄭小公子可是一日三趟的遞了拜帖,恨不得住在咱們將軍府呢。我瞧著阿禾是女大不中留咯。」
還說我呢,若不是因為我傷著了,阿姐也不會推遲婚期,早就嫁給賀齊越了。我拉過阿姐,拍著胸脯向她證明我早就好了,讓她放心大膽的嫁給賀齊越吧。
阿姐低頭嬌羞,輕輕推了我一把,「你說什麼呢。」
這輕輕一推不要緊,我從榻上滾到了地上,抻到了傷口,痛的直嘶嘶。果然我和阿姐一脈相承,想我當初把鄭兌推倒應該也是如此威力吧。
阿姐出嫁,母親找了汴京城最好的十二位繡娘給她做嫁衣。我看著那大紅繡金線的嫁衣如火如霞,阿姐穿上,纖腰不及盈盈一握,襯得她冰肌玉骨、雪貌花容,梳著花火髻,戴一頂滿是金珠的鳳冠,眉目間的一股英氣渾然天成,看得我直愣了眼。阿姐穿上嫁衣真好看。
出嫁那天,小賀將軍高頭大馬、十里紅妝,好不威風。我看他鄭重對著爹爹母親許諾的樣子,不由得讓我想起鄭兌來,他小時候說要考上狀元郎來娶我的事,不知他還記不記得。若是鄭兌穿上這大紅的喜服,定會比賀齊越還好看,若是我穿上鳳冠霞帔,定也不遜色於阿姐。
混在賓客裡喝喜酒的時候,我看見了鄭兌。他身邊穿柳綠紗裙的女子是誰?他怎麼能跟別人如此溫柔的說話呢?我很生氣,想去找他對峙,可我又有什麼立場、什麼資格呢?想著想著,我鼻頭一酸,眼眶熱熱的就要流淚。
不行不行,今天可是我阿姐的好日子,我可不能哭唧唧的給她添煩惱。再說我可是堂堂將軍府二小姐,汴京城頭牌花魁花見慚的女兒,怎能如此沒出息。
如此憂愁了好些天,我就去十二苑找我娘了。我娘見我欲言又止的模樣,嘰嘰歪歪半天也蹦不出一個字,不僅怒上心頭,又要請我上太師椅。月槐姨娘見狀趕忙來拉她,「阿慚,我看墮兒是芳心暗許,有意中人咯。」說著又來問我,「墮兒瞧上了誰家的公子呀?也叫姨娘們幫你相看相看。」
我……我……
我總不能說,姨娘,我看上了你曾經的兒子吧?
我羞憤地掙脫我娘和月槐姨娘,奔出了十二苑。
跑回家的路上好多人,有人垂頭喪氣,有人興高采烈。
等我噔噔地跑進堂屋,只見我嫁作新婦的阿姐和她的如意郎君立在堂中。見了我回來,阿姐和母親好不高興,阿姐拉了我的手,「阿禾,今日放榜,鄭兌那小子中了狀元呢!」
中了狀元……他真的做到了。
我該替他高興的,畢竟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分。可我想起阿姐出嫁那日,他和別的女子言笑晏晏的樣子,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阿姐拍拍我,擠眉弄眼地繼續說道,「今日大殿上,皇帝陛下高興,當場封了他庶吉士的職位,這可是宰輔之才呢,還說要為他指婚丞相獨女,可他不卑不亢的拒絕了,說什麼‘多謝陛下關懷,微臣早已心有所屬,惟願陛下將驍勇將軍小女季清禾賜婚臣下。微臣若了此心願,此生無憾。’沒過片刻就在整個汴京傳開了,全城的女子都好生羨慕,說若得此如意郎君,便是什麼苦也成了甜,連我都有些羨慕呢。」
一旁的賀齊越拽拽阿姐,暗示她差不多的了。
正當七月裡,我同其他官家小姐泛舟回來,捧了滿懷的荷花。回到家中,遠遠就看見他站在凌波亭邊,等我歸來。亭邊一棵石榴樹正開滿火紅鮮花,襯得新晉的狀元郎眉眼溫潤。他嘴角含笑,遙遙朝我招手。
我走到他面前抬頭看他,盛夏的陽光耀眼、蟬鳴陣陣。我在十六歲的年紀裡問我的少年郎,「你怎麼來了?」
他抬手摘一朵石榴花插在我鬢間,為我擦去額角的汗水,還是那樣溫和地笑,說,「來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