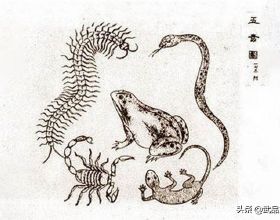外鄉人:
民國時,有一外鄉人,讀了兩年私塾,因為家裡窮,很早就輟學了,稍微大點就外出務工,他來到了上海,那是他第一次出門。上海那是魚龍混雜的地方,幫派林立,沒有背景容易被欺壓,外鄉人住的城中村又恰恰是這些江湖中人安營紮寨的地方。外鄉人為了保護自己,便把自己的頭理了,理得像那些江湖中人,無論是什麼幫會的人,見到就打招呼,別人也會給他點頭,時間久了,大家都覺得他也是某個幫會的人,也沒人來找他的麻煩。就這樣煎熬了好多年,外鄉人目睹過江湖幫派的仇殺,也見證了那些所謂的老大,不是被仇家暗算,就是被巡捕房的人給抓走。他有幾個老鄉,一起殺了某個幫會的老大後逃出上海,幫會的人用錢聯絡各地道上的兄弟,對他們趕盡殺絕,其中一個跑到鄭州被亂槍打死,一個跑到蘇州被活活的淹死,一個跑到天津被勒死。
外鄉人厭倦了和江湖人熱情的生活,因為這一切都不是他的追求,小時候他喜歡看書,學怎麼寫詩,卻因為自己是人家的養子,被村莊的人當成外人欺負,他這才遠走他鄉,過著無家可歸的生活。到了上海後,他一邊打工,一邊買書自學,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經常去圖書館,因為那裡可以遇見很多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遇到了從東北來的蕭紅,又有一次他遇到了海派泰斗魯迅。除了圖書館,他還會跑到大學裡去,他很羨慕那些能上大學的人,有一次他遇到一群學生,還一塊朗誦著徐志摩的詩,他立即跑了上去,可等大家散去之後,他又有了些失落,畢竟自己不是象牙塔裡的一份子。在上海,他也認識了一些文藝青年,偶然也會拜訪這些人,他也愛上了一個女文青,經常在一起討論詩歌,聊著文學,可自己卻不敢表白,可能是覺得自己一無所有,給不了她幸福。他曾和一個老者聊天,老者問道“你為什麼這麼喜歡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外鄉人回答“為了救天下。”老者隨即大笑,說“你救不了,天下已經病了幾千年了,誰也救不了,我年青的時候也很激情,結果滿清誣陷我是孫黨,把我關了半個月。”
城中村裡很多在窯子或舞廳上班的人,外鄉人的鄰居有個交際花,經常會過來搭訕,外鄉人沒怎麼搭理她,只是一笑走開。有次,她突然過來找外鄉人,說“我是四川來的,我叫清秀,大家都叫我淑女,你叫什麼。”外鄉人不想理她,見到桌面書籍有作者的名字,就隨便說“我叫李商隱。”這個叫清秀的女人沒上過學,不知道李商隱是唐朝詩人,就真信了他叫這個名字。有一次,清秀下班回到租房,喝了很多酒,見外鄉人的房間沒關,便過來敲門,外鄉人假裝沒聽見,她直接跑到窗外敲起玻璃,外鄉人已經受夠了她的糾纏,便把油燈一吹,然後躺下睡覺了。外鄉人厭惡這個城中村,也厭惡這裡的人,即使城中村裡也有好人,一些人也是為了生活,但是,他就是厭惡,更厭惡那個叫清秀的交際花,因為自己喜歡的不是她這一類的,自己喜歡的是那種詩情畫意的。外鄉人越是不接受清秀,對方就越得寸進尺,撞見的時候不是拋媚眼,就是故意解開自己的上衣釦子,或是下身旗袍。有一次故意把自己的胸罩掛在外鄉人的窗戶上,有一次故意在門口發出淫穢的叫聲,最後更荒唐,她見人就說自己和外鄉人好上了,還發生過關係,還生了孩子。
外鄉人搬出了那個城中村後,重新找了一個地方住,至少沒有之前的混亂,也找了一份在書店的工作,在書店裡他能接觸到很多讀者,可以和他們交流。不過他對局勢的關注,和一些激進言論引起了特務們的注意,書店老闆也怕出事,就把他給開除了。外鄉人換了很多工作,不是被排擠,就是被開除,他也覺得經常有陌生人在背後跟蹤、破壞,有時候吃東西莫名其妙的拉肚子,上火,他覺得被人下毒。後來他發現,原來是那個清秀在背後搞鬼,為了報復自己的拒絕,她不惜和巡捕房的人發生關係,和流氓發生關係,就是讓他們到單位破壞、恐嚇,要讓外鄉人不能正常的活下去。外鄉人越覺得生活變得危機四伏,也覺得像是道路以目,沒人願意和自己說話,也不敢和自己接觸,自己也不想和別人深交,怕會連累到別人。生活的落魄,他只能把書籍給賣了,越來越拮据,有人勸他去醫院賣血,或是賣腎,他越覺得自己受到威脅,可也沒辦法,知道周圍的人很多都是被安排來監視自己的。
這一年,日軍大舉入侵上海,他一直躲在家裡,每天外面都是狂轟濫炸,越是繁華的地方越容易被炸掉,他看著日軍的飛機飛過,心裡立即有了一種想法,炸了最早住過的城中村,炸死那些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炸死那個人儘可夫的交際花。似乎,眼前都是自己想看到的,成千上萬的流氓和黑警被炸死,清秀也躺在血泊中,口中不段的湧出鮮血,身體在那裡抽搐著,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不過這些都是他自己的幻想,除了看到日本人的飛機,他也看到曾經大學裡遇到的學生,他們冒著日軍的炮火,給前線送彈藥,給傷員包紮傷口,把傷員抬下戰場。外鄉人心想,自己也該做點什麼,於是他也跑出去,和他們一塊,在炮火中搶救傷員,現在,一切都不是幻想,都是真實的畫面,血淋淋的。他目睹了國軍身上綁著手榴彈衝向日軍的坦克,看到很多軍人被打死,卻義無反顧的一個接著一個衝鋒。他也邂逅了那個自己喜歡的女文青,當看到一個人時常在她的身邊噓寒問暖,他就不好意思敘舊了,只能隨便打下招呼,叫他也都是拒絕了。
幾個月後上海淪陷,外鄉人也跟著逃散的人到處找地方躲藏,他和女文青失散了,外面還有槍聲,有人說是從四行倉庫傳來了,沒過幾天,槍聲也停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外面也傳來南京淪陷的訊息,說死了很多人。為了生活,外鄉人和熟人一塊到碼頭幹活,有次他下班回租房的路上,看到對面的小巷裡很多交際花在朝日本兵打招呼,其中一個就是清秀,她一點也不覺得可恥,拼命的和日本兵拉拉扯扯,賣弄風騷。這時,開來一輛車,下來幾十個日本兵,都色眯眯的跑進去,清秀看到,反而比剛才更風騷起來,拉著他們就往裡走,這些日本兵也跟丟了魂一樣,黏糊糊的。外鄉人看到這裡,心裡就是一肚子的火,小聲的謾罵“你就是一個破鞋,你永遠都是破鞋,你們都是破鞋。”外鄉人不想呆在上海了,便收拾東西離開,可也不知道上哪,到處都是兵荒馬亂的,他就破罐破摔,隨便上哪了,不知不覺到了一個小城市。雖然也是淪陷區,好在沒有戰火蔓延,秩序也基本恢復,也能填飽肚子。過了幾年日本就投降了,外面到處都在敲鑼打鼓慶祝,可沒過幾天,就有大批人來接收,不是亂抓壯丁,就是搶東西,還開槍殺人,比淪陷區的時候還混亂,一些人居然懷念起淪陷的時候。
又過了幾年,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很多人都在議論他們不得人心,由於外鄉人是窮苦人出生,受到了關照,被送到工廠裡面做學徒,讓他學些技術以後好養活自己。又過了一些年,外面貼滿了大字報,很多人被批鬥,甚至連幫助過自己老幹部也被批鬥,外鄉人很困惑,他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他知道里面有些人是好人。有次他出門,看到一群紅衛兵押解幾個婦女,脖子都被套上一個牌子,寫著“打倒舊社會的破鞋。”突然,他發現裡面就有清秀,他很詫異,心想,怎麼會是她,他怎麼也在這裡。清秀也認出他來,不停的看他,外鄉人怕惹麻煩,轉身就走了。可這一切都被人發現了,覺得其中肯定有問題,於是就找清秀問話,清秀便誣陷外鄉人是自己的舊相好。造反派很快就把外鄉人給帶走盤問,一個問“你們屬於什麼關係”,一個說“她是不是你的相好”,一個說“她是舊社會的破鞋,你在舊社會搞過破鞋”,很多人一致的問“你和破鞋是不是一家人。”
外鄉人不停的解釋“我沒有,我不認識她,我和她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們不是一家人。”紅衛兵不信,不依不饒,最後把他和清秀她們一塊拉去遊街,外鄉人被迫把頭低下,耳邊傳來亂哄哄的叫喊聲“打倒舊社會的破鞋”,大夥也跟著喊,一個又喊起來“打倒破鞋”,大家還是跟著喊。隨後,外鄉人不能去工廠學技術了,被安排到農場幹苦力,他討厭的清秀也在這裡面,外鄉人只要一見到她就立即轉身,怕再惹麻煩。有一天,他幹活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個女人在艱難的搬運木頭,他覺得有點眼熟,便走了上去,一看,原來是曾經在上海認識的,也是自己喜歡的那個女文青。故人相見,百感交集,彼此都熱淚盈眶,女文青哽咽的說“是你,你還活著。”外鄉人一聲嘆息,說“是,還活著,還活著。”外鄉人說完,便幫忙她幹活,這一切不僅被清秀看到,也被幾個小將看到。小將們大搖大擺的走到清秀的面前,挖苦道“看見了沒有,原來他不是喜歡你這樣的破鞋,人家喜歡的是她那樣的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