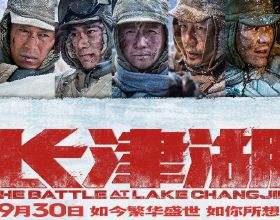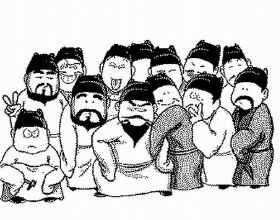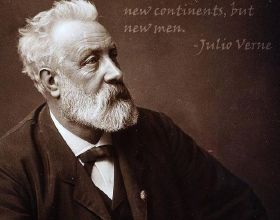本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1.10.18總第1016期《中國新聞週刊》
“拜託,別瞎扯了!不要煩我。”
接到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馬茨·馬爾姆的電話時,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正在泡茶,對於自己獲得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訊息,他以為只是有人在搞惡作劇而已。直到十幾分鍾以後,諾獎官網主編亞當·史密斯再次致電,他依然在電腦上確認著這件事的真實性。
圖/視覺中國
不相信這個結果的,其實不只古爾納自己。在早先甚至歷年的博彩賠率榜和全球媒體預測中,他的名字都從未被提及過,何況自1986年沃勒·索因卡以來,諾獎就再也沒有頒給過非洲黑人作家。作為客居英倫的移民作家,古爾納在英國的名氣遠遠不及“移民三傑”石黑一雄、奈保爾和拉什迪,英國之外的地方更是鮮有人知,美國專門追蹤實體書和電子書銷售資料的NPD Bookscan資料顯示,其作品《拋棄》自2005年在美出版以來,在向該服務報告的銷售點只賣出了不到2000本,甚至公佈結果當天,諾獎官方發起的投票尷尬地顯示,超過九成讀者都沒讀過他的文字。
儘管古爾納此前憑藉《天堂》《拋棄》《海邊》入圍過布克獎、惠特貝瑞圖書獎和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的名單,卻並未真正摘得哪頂桂冠。正如他的編輯亞歷山德拉·普林格爾所說:“他是在世的最偉大的非洲作家之一,但從來沒有人注意過他。這讓我很難受。這簡直要了我的命。他是那種被忽視的人。”
而在中國,除了一本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中收錄過其兩個短篇,再沒有任何作品被翻譯為中文,以至於準備報道的媒體在第一時間都無法準確寫出他的譯名,所有人的腦袋裡都打著同一個問號——這個人是誰?
比起作家,他更出名的角色是評論家
臨近東非大陸的印度洋西部有一座小島,名為“桑給巴爾”,阿拉伯語意為“黑人海岸”。公元5世紀前後,躲避戰亂的阿拉伯半島居民開始向這裡移民,到1505年基爾瓦王朝被葡萄牙艦隊擊潰,這裡已經充分伊斯蘭化,並由土著文化與阿拉伯文化的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斯瓦希里文化。
1948年,古爾納就出生在這座小島上。彼時的桑給巴爾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中,因此說著斯瓦希里語的古爾納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習英文。在他15歲那年,桑給巴爾經過數次抗爭,終於宣告獨立,成為蘇丹王統治的君主立憲國家。然而誰也不會想到,少年古爾納的厄運卻從這裡開始了。
1964年1月12日清晨,在非洲大陸黑人和設拉子人組成的反對黨——非洲設拉子黨——的動員下,600~800名革命者襲擊了警察部隊並奪走武器,前往桑給巴爾鎮推翻了僅僅成立一個月的蘇丹王朝及民族黨和桑奔人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由於英國殖民者離開這裡時,留下了一個少數阿拉伯裔統治多數非洲裔的政治結構,因此革命者建立的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隨即對島上的阿拉伯和南亞裔平民進行了報復,數百至兩萬人(人數尚有爭議)被屠殺,許多阿拉伯和南亞婦女遭到輪姦,財產被洗劫。
在古爾納的回憶中,這場暴亂是可怕和令人震驚的。2019年,他面對《Wasafiri》雜誌的採訪時說到:“我那時是一個學生,我們學校被關閉了,我們大部分的老師是歐洲人,僅僅一個月時間,他們就不得不按要求離開。到處都是槍,革命以前我們從沒見過槍,哪怕是在警察身上。現在一個帶著槍的人可以走進一個小商店,就像一隻野生動物走進去一樣。”
面對充滿艱辛、焦慮、國家恐怖和蓄意羞辱的生活,古爾納在18歲時選擇離開桑給巴爾島。他在肯亞停留了一段時間,並於1968年以難民身份抵達英國。此後十餘年,他都未曾再回過故土,直到1984年才在父親去世前不久歸鄉見了最後一面。
1976年,古爾納從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學院畢業,獲得倫敦大學教育學士學位,隨後在肯特郡多佛市的阿斯特中學任教。1980年,他開始執教於奈及利亞的巴耶羅大學,同期攻讀英國肯特大學博士學位,並於1985年進入肯特大學任教。這份教職成了他終身的事業,直到退休,古爾納一直在肯特大學擔任英語和後殖民文學教授,從事與非洲、加勒比、印度等地區相關的後殖民文學研究。
從1987年開始,古爾納還一直兼職《Wasafiri》雜誌的編輯工作,並先後主編過兩卷《非洲文學文集》,發表了一系列論述當代後殖民作家及其創作的文章。頗為有趣的是,奈保爾、索因卡、拉什迪、提安哥這些移民作家都是他所關注的研究物件,而他們的“離散寫作”遠遠早於古爾納自己的文字得到了世界文壇甚至諾貝爾獎的認可。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的副教授張峰,自2010年左右便開始對古爾納的文學進行研究。在他看來,古爾納的作家身份之所以不太被人熟悉,正與其學者和評論家的身份有關。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種多重角色可能是一個好事,但同時也會淡化他的作家的這種角色,在英語文學研究界更多是把他看成一個評論家。”這並非孤論,《新共和》的專欄作家亞歷克斯·謝潑德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古爾納最出名的可能是他作為評論家的工作。”
或許就算古爾納本人也不會對此提出太大異議。在2010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曾說過:“當你從事你的職業,並且到達更高的級別,也就不得不承擔更多與教學、書籍等等無關的機構職責,這就是矛盾所在。也就是說,你的腦子裡充滿了其他東西,很難找到空間來安放那些你感興趣的東西,比如寫作。”
難以抗拒的記憶與甩不掉的孤獨感
事實上,對於古爾納而言,從事寫作原本就是一件偶然之事。2004年,他在《衛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到,自己在桑給巴爾生活時並沒有打算成為一名作家。“在那之前我寫過東西,雖然彼時我還是桑給巴爾的一個學生。但那只是鬧著玩的,為了娛樂朋友和在學校的諷刺劇中表演,不過是心血來潮或者打發時間或者炫耀。我從不認為那是在做什麼準備,也不覺得自己要立志成為一個作家。”
真正促使他拿起筆來的,是到英國後產生的一種被生活拋棄的失重感。這是異鄉人和無根者才有體會的感受,對外部世界的陌生以及自身與周遭無法彌合的差異,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著你已經失去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漸次累積的漠視、孤立甚至侮辱,則不斷勾勒並強化著內心的某種記憶——它來自失去的地方和生活,或者僅僅是一個與現實不同的地方、一個足夠安全的地方。
當然,一切的開始並未如此思路清晰。最初的古爾納只是漫不經心地寫著,在日記中寫下關於家的小片段,然後是其他人的故事。後來他才慢慢意識到,自己是在憑記憶寫作,那種記憶如此生動又難以抗拒。於是他正式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取名就叫作《離別的記憶》,講述了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試圖擺脫故鄉的困境,卻最終歷經羞辱後回到了破碎家庭的故事。
顯然,這是一次失敗的出走,多少摻雜著古爾納自己在英國的最初歲月的不適。到了第二部作品《朝聖者之路》,他則開始嘗試尋找和解的可能性。流浪到英格蘭的主人公達烏德,努力隱藏著自己過去的一切,最終卻還是在一份異性之愛面前講述了那些創傷的記憶。小說結束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達烏德驀然發覺原來自己曾反抗的那些東西,竟然散發著觸手可及的美。
1990年,古爾納寫出了迄今為止唯一一部以女性為主角、也是唯一一部主角出生在英國而非桑給巴爾的小說《多蒂》。作為生長於充滿種族歧視的1950年代英格蘭的黑人女性,多蒂既在這裡感到無根,又因為母親的沉默而與自己的家族歷史缺乏聯絡。她試圖透過書籍和故事創造自己的空間與身份,並且逐漸在探索中發現自己的名字背後隱藏著一段悲慘的家族史。如果說達烏德的“朝聖之路”尚且還帶有一絲絕境求生的不得已,多蒂的身份認同則增添了幾分自我建構的主動性。
儘管這三部作品從不同的敘事視角記錄了移民在英國的經歷, 探討了遷移到一個新的地理和社會環境對人物身份帶來的影響。但顯而易見的是,此時的古爾納還未能跳出個體視角和區域性剖解的框架。直到1994年《天堂》的出版,才標誌著他作為一個成熟作家的自我突破。這部同時入圍布克獎短名單和惠特貝瑞圖書獎的作品,透過男孩尤素夫的眼睛看盡了部落爭鬥不斷、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隸貿易猖獗的非洲。比起前作,《天堂》擁有了更廣闊、宏觀的視野,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部龐大的非洲編年史。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的副教授張峰認為,這種由現實向歷史擴充套件的創作譜系,似乎是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在創作上的一種共性。作家克萊爾·錢伯斯則在《英國穆斯林小說——當代知名作家訪談錄》一書中,指出了從《天堂》開始古爾納創作的另一顯著轉變:“在寫作《離別的記憶》的時候,他嘗試寫出主角對於離開的渴望,而如今他想寫作的內容卻是主人公雖身在國內仍有一種甩不掉的孤獨感。”
儘管諾獎在授予古爾納的頒獎詞中,著重強調了其寫作對殖民主義的探索和難民命運的關切,但或許“孤獨”更能概括他文字中那個縈繞不散的核心。正如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在評述中所寫:“古爾納在處理‘難民經驗’時,重點是其身份認同。他筆下流動的人物常常發現自己處於文化與大陸、過去的生活與正在出現的生活之間——一個永遠無法安定的不安全狀態。”
2011年出版的《最後的禮物》是古爾納的第八部小說,同樣延續著移民主題。不同的是, 它聚焦於移民經歷對移民自己及其後代的無盡影響。而在第九部小說《碎石之心》中,主人公在母親去世後再一次面臨著那個艱難的選擇——應當留在桑給巴爾,還是回到倫敦?在一次採訪中,古爾納說:“在危機時刻,人們會一次又一次重返 ‘我應當在哪裡’的問題。”
在張峰看來,這恰恰是後殖民文學的意義所在。“後殖民並不意味著殖民主義思想的終結,因為殖民統治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宗主國或殖民文化的終結,它在殖民地上已經紮根了,而且在很長的時間之內都會影響殖民地人的方方面面。後殖民文學與殖民文學不是截然分離的兩個階段,而更多意味著一種延續,以及這些來自殖民地的人和來自殖民地又遷移到宗主國的人對於殖民意識形態的不斷反思,包括對獨立之後的後殖民身份的不斷考量。”在一篇題為《An Idea of the Past》的文章中,古爾納也對殖民主義的當代性問題做出過他的闡釋:“對非洲人來說,歐洲殖民主義及其影響是當代事件,重點正在於其當代性,殖民主義構成了許多非洲國家的過去,也形成了它們的當下。”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願意接受“後殖民主義作家”這樣一個標籤。他明確表示過:“我不會使用這些詞,我不會讓我自己戴上這樣一個簡單化的標籤。事實上,我不確定除了我的名字我還會怎麼稱呼自己。”與此同時,古爾納對於後殖民寫作也保持著清醒的警惕,他認為將矛頭單單對向曾經的殖民帝國、將所有社會癥結歸結為殖民統治的毒害是一個陷阱,非洲內部民族和部落分裂所帶來的危害一樣可怕。並且“對後殖民主義作家來說,危險似乎在於,這可能會在一個歐洲外來者疏遠與孤立的生活中已經或將要產生作用。如此,作家很可能成為一個憤憤不平的移民,嘲笑留下的人,並得到那些出版商與讀者的歡呼——他們對殖民地人民仍存有隱秘敵意,且樂於獎勵讚揚對非歐洲世界的任何苛責。”
與中國的奇妙連線
去年9月,古爾納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來世》,以1907年反抗德國殖民者的起義為開場,展示了幾代人歷經德意志帝國統治與英國殖民,努力維持著他們位於坦尚尼亞大陸一個沿海小鎮上的家庭與社會。許多評論將之視為《天堂》的續作。
然而最重要的始終是古爾納想要表達的思索。《衛報》的一篇書評說,“大部分有關歐洲在非洲殖民歷史的討論都將德國排除在外,但實際上建立於19世紀末的德意志帝國,殖民過今天的奈米比亞、喀麥隆、多哥、坦尚尼亞和肯亞的部分地區,並最終奪取了盧安達和蒲隆地,其殖民統治是殘酷的。古爾納在這本書中思考了殖民主義和戰爭的代際影響,並促使我們思考在如此巨大的毀滅之後還剩下什麼。”這的確是古爾納所在意的。
可以想見的是,在諾獎的加持下,這本《來世》必然要比古爾納的幾部前作更快更廣地傳遞到讀者手中。對於尚無譯本可讀的中國讀者來說,與古爾納的相遇相信也不會太遠。一個有趣的例子或許可資證明:上海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盧敏,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的成員,負責東部非洲研究的她從2019年起就開始研究古爾納。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國慶節前自己剛好分給學生一個任務,每人讀一本古爾納的小說然後寫出作品簡介,結果諾獎的新聞一出,許多媒體便找到她索求資料,於是學生們這幾天都在拼命趕稿。
同時,在盧敏的研究中,她還發現了古爾納與中國的一個奇妙連線:“他幾乎每一本書裡都會提到中國或者華裔,也會提到中國建鐵路,還會提到中國的一些產品。他在《多蒂》裡面反覆講到一箇中國公主,就是《一千零一夜》裡面的巴杜拉公主。”
我們尚且不知這種連線在古爾納的內心從何而來又意在何為,只曉得這份緣分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就種下了。據古爾納在BBC的一檔歷史系列節目中回憶,自己年輕時在桑給巴爾島上發現過幾片中國瓷器碎片:“直到當你參觀博物館,或者當你聽到那些關於中國艦隊遠赴非洲探險的偉大故事時,這些小物件才變得有價值,成為某個重要事物的象徵,或者說是一種聯絡。然後你就會看到這些物件本身,看到它的整體性、它的重量、它的美。一切都是環環相扣的,像中國這樣遙遠的文化,在遠隔幾個世紀之後出現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