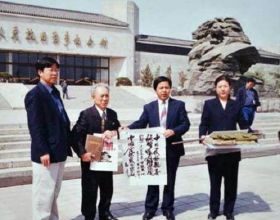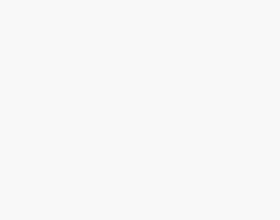我剛滿15歲,父親給我報了名,讓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參加了當年的高考。

沒幾天,父親就帶回來了高考結果:我語文考了86,數學只有39,總分離錄取線還差17分。父親很高興,我高中剛讀了一年,就能考出這樣的成績,明年可謂十拿九穩。
父親四處打聽,得知我們高中當年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後,便決定讓我轉學,費盡周折,硬是找關係把我送進了祖母家附近的華容四中。

報到後,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師就把我叫到他宿舍裡,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你參加過高考?聽說考得還不錯,就差十多分上分數線?今天劉副校長從縣教育局開會回來,還為你的事專門召開了會議,校方接納你,頂了很大壓力。你之前的學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實現高考零的突破,爭議好大呢!”
從此,我正式成為華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陸陸續續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終考的成績出來了,我總是名列前茅,特別是語文,單科長期駐在榜首,引得同學們驚訝羨慕。
一個學期接近尾聲,迎接高考的緊張氣氛也越來越濃了。就在我生疔的頭一天晚上,我還跟一位同學(他後來當屆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我們當地的美談)臨時擠在學校寢室的一個鋪位上。那晚,我們暢談著各自的理想,規劃著未來,幾乎一夜未眠。
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數學課上,我忽然感覺離太陽穴不遠的地方,似乎長了一個又腫又麻又木的東西,伴著持續的低燒,整個人的狀態十分萎靡。整堂課都趴在課桌上,老師佈置的作業也無心去寫。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覺得我的情況十分不妙,趕緊跑到糧食管理總站撥通了我家那邊糧管站的電話——就在1978年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母親接到糧管站的人送來的口信:你的兒子臉上長了一個疔,蠻危險,你們趕快去!
父親後來對我說,他趕到伯父家時,遠遠就看到我的整個頭腫得毛線衣都脫不下來了,鼻孔裡噴著陽塵灰,七竅都流血了,兩隻眼睛腫得似燈籠,左額的疔傷口還有少許的血膿水排出,喉嚨都腫大了。

父母趕快把我送到醫院。醫生會診後說,這是疔毒引起的敗血症。
那些天真是難熬,整個白天,我的點滴沒有斷過,姑媽坐在床頭,把我腫得不像人形的頭摟在懷裡。母親用調羹把水一點點滴在我乾燥的嘴唇上。夜深時,她就一個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靜處,向著曠野絕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來送開水的食堂師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們又要早起,誰受得了?”
校領導、班主任周老師都來醫院看望我,周老師看著眼前的一切,連聲搖頭:“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個禮拜之後,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來。我問母親:“這是在哪裡?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掙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腳卻癱瘓了,一點都不聽使喚。
我勉強睜開腫得如桃子般的雙眼,眼中的世界卻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醫生跟我說:“這在醫學上講,是一種複視,要想身體狀況完全恢復,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歲月之歌
1978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日,除夕在即,我必須出院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無論多忙,母親都要回家把從郎中那裡開來的中草藥,一天一服煎好,定時盛一大土碗,讓我喝掉。父親也會去大大小小的醫院找“加蘭他敏”和“新斯的明”,藥價二三十元不等,時常要向公社打報告才能批下來。
我一般早晨六點半左右起床,進行簡單的跑步訓練。湖區的田野自然而舒適,時不時會有小青蛙驚恐地從我腳邊跳入溝渠裡、荷葉縫裡、高筍莖上。那些夾雜著農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擊著我的嗅覺——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與珍惜的理由,季節的解凍已是勢不可擋,春天以雷霆之勢蓄勢待發。

再往後,我也可以自己一個人搭機帆船到地區醫院做理療了。有個與我父母年齡差不多的周醫生,曾以“文紅年青大有作為”作為字首字,讓我吟詩一首,我隨即胡謅一首,他拿著寫在處方單上的答案面露驚訝之色,將我會作詩的事逢人便講。
為緩解家裡的經濟壓力,父母還買了一臺二手壓面機,起早貪黑,和麵粉、壓粗坯、壓細坯、出面條,一個接一個的客戶就在一旁候著等著。很快,我家麵條的名聲傳遍了十里八鄉,“個體戶”這個新名詞也出現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嶺,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學幾乎全部進入大學深造,而我,只能四處求醫問藥、堅持鍛鍊,甚至在手搖壓面機手把前流著黑汗。

右手不靈便,我就開始練習左手書寫,我躲在角落裡,寫下了不少詩歌、散文和小說,然後去找字跡工整的夥伴們幫忙謄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後,我左手書寫的字,獲得了市級書法家協會的大獎。到80年代末期,我終於考入湖南江南工學院學習機械製圖。
此刻,我終於不再抱怨命運所賜的痛苦和災難了。彷彿流浪的水手重回戀人溫柔的懷抱,我將歌唱——用拙劣、嘶啞的歌喉縱聲唱出注滿海水的歌謠。像遙遠的燈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隻,我也將努力找回那個迷失人間的自己。
我終於可以對1978年說一聲:再見,我的人生從此不再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