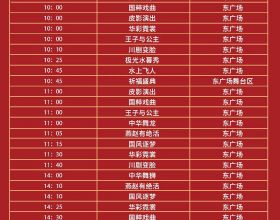來源:綠色中國
在許多人的眼裡,十羅洋茶場,是一個披著神秘外紗的茶場。多年來,我的心中一直有個強烈的願望:擇機到那裡“看個究竟”。
暮春的一天,風輕雲淡,陽光明媚。我終於在“資深茶友”柴君的牽線與陪伴下,如願以償地坐上了“茶場主”的車子,向夢裡尋她千百度的茶場進發。
沒走過這條路,慢點說你不會暈車
論路程,茶場也不怎麼遠。從江山市區出發,到茶山的山腳下,不足70公里。然而,大部分走的是山間公路,崎嶇坎坷,蜿蜒曲折,驅車一般要一個半小時才能到達。坐在車上,顛來簸去,腦路似乎總跟不上Z字型山路的拐彎節奏。若非久經考驗,暈車是自然的,不暈車倒有些反常。沒坐多久,我與柴君就感到噁心、胸悶、頭暈,只想嘔吐,連經常在這條路上跑的廖鵬飛也說,要不是把著方向盤開著車,他也會暈車的——嘿嘿,坐車要暈,開車不暈,我也有這樣的體驗。他不這樣說,我真的有想法從他的手中“搶”過方向盤的。唉,若沒經歷過通往十羅洋茶場的山路,最好慢點說你不會暈車。
薑還是老的辣。與我同坐在後排的廖松柏,是廖鵬飛的尊翁。他不僅一點暈車的感覺都沒有,一路上還談笑風生,滔滔不絕。
上陣父子兵。“尊翁”乃十羅洋茶場的場長,“兒郎”則掛個副場長的頭銜。前者在茶場所在地的大山深處長大,後者則從上幼兒園起就在城裡生活。他們的家,早就搬到了城裡。而今,一老一少,攜手往來於容易讓人暈車的山路,再度鑽進大山深處辦起高山茶場,這在許多人的眼裡,簡直是一種不太明智的逆行。
年近花甲的廖松柏,三十掛零走出大山做木材生意,已在商海里浸泡了幾十年,但至今仍未脫去“山娃子”的質樸與豪爽。聊起創辦茶場過程中的一波三折,每每講到緊要處,他就會拍起我的肩膀或膝蓋,給人喜形於色、怒喝於顏的直爽印象。
不過,他的眼光卻是堅毅的,遠大的,像個見過世面的人物。
早年,每到春茶上市,他就從老家那個稱為十羅洋的地方買些十幾元一斤的手工茶送給城裡的朋友。他回憶說:“最初覺得這茶外形不太好看,有些拿不出手,可奇怪的是,朋友們喝過之後都讚不絕口,有的甚至說比那幾百元一斤的名茶還要好喝,又特別經泡,來年就主動向我討要了,哈哈哈……”
世間有些好東西只能靠天賜,人力不可為,這就像一個人,最頂尖的美容師也無法改變你的身高,而天賜的好東西沒有加以利用,這就像永遠埋在地底下的黃金,與一般的泥土沒什麼兩樣。漸漸地,廖松柏意識到十羅洋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是一個可以做出高檔茶葉的絕好地方。這樣的地方,若不種茶,不出名茶,豈不辜負了上蒼的恩賜!
這裡的氣候適宜種茶,可產茶卻沒有形成氣候。茶園零零星星,很不起眼。即將跨入新千年之時,廖松柏立下誓言,一定要攜手鄉里鄉親,將十羅洋打造成一個出產高階茶的地方。門到戶說,足趼舌敝,歷經兩個多月的遊說,他終於動員了8戶山農與自己一起幹,以開發300畝茶園作為起點。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幾年,9位合夥人就“一拍九散”,讓他獨自成了風雨中的孤雁。
“這是怎麼啦?”聽到這裡,像是某根敏感的神經受到了刺激,我一下子來了精神,頭也不覺暈了。
“唉,一言難盡啊!”廖松柏拍了拍我的身子說。
種茶,是一種長線投資。下種時,誰都沒數,將來會怎麼樣。因而,一說起花錢的事,股東們總是心裡打鼓。茶園裡還沒產出幾片可以採摘的茶葉,廖松柏竟然在市科技局領導的“攛掇”下,泛起了與浙江大學合作研發高階茶的念頭。十羅洋的茶葉,祖祖輩輩不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嗎?還沒有一分錢進賬,又要花錢請大學教授做師傅?“不幹、不幹!”結果呢,9位合夥人,反對的有6人,支援僅3人——除了他自己,另兩位還是經他反覆遊說才勉強點頭的。幸好,在股權上,佔了大頭的廖松柏,加上另兩位投贊成票的股東,佔了總股權的85%,合作決議最終以股權表決得以“順利”透過。不過,這次的分歧,卻也埋下了散夥的伏筆。
又過了一年,新茶如願面世。然而,廖松柏還沒來得及開懷笑出聲來,悲催的事兒便悄然而至。他揹著新茶樣品,南至廣東深圳,北至遼寧丹東,到處兜售十羅洋的茶葉。然而,他對茶葉市場,兩眼一抹黑;上當受騙,便成了家常便飯。有的“主兒”,吃了拿了之後,轉身電話就中斷;有的“出口商”,要了昂貴的外國認證費,到頭來一兩茶葉的生意也未做成;有的“業界大亨”簽了購銷合同,卻遲遲未依約付款提貨,以致大量高檔新茶堆放在倉庫裡,到頭來變成了劣質陳茶……翻開賬本一算,喔喲喲,虧損了一百多萬元,多年做木材生意積攢下來的錢一朝化為烏有,還到銀行貸款抵債……
“你說,不賺錢,還虧本,誰還會跟著你幹呢!”廖松柏又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身子說。
是啊,暫且慢說股東們不夠意思。如果今天這輛車子,行駛在他那曲折坎坷的創業之路上,我也會暈倒的。
他的故事沒講完,車子已到了目的地。開啟車門前,廖松柏又說道:“不過,我從來沒有失去信心。我這羅洋曲毫,可以說‘茶過七道,空杯留香’,還怕一直沒人識貨?”
茶過七道,空杯留香
車門一開,山風拂面,感覺涼颼颼的。這裡的氣溫的確比城裡低了許多。下車後,我又急忙回身從車上取出“備衣”,當即加穿了一件羊毛衫。要不是事先做了功課,憑自己的身體狀況,我沒準就會著涼感冒。
緩步走進一幢四層辦公小樓,坐在一張長條型的大茶几前,我一半玩笑一半認真地嚷開了:“茶過七道,空杯留香,真的假的?我要驗證一下。”廖松柏笑笑說:“這個沒問題,可以當場驗證。”他努努嘴,讓小廖來操作。
廖鵬飛的手裡擺弄著一個白色加蓋茶杯。他在投入茶葉前,先用滾燙的開水將其衝淋了一遍。懂茶的柴君作解說,這叫“溫杯”,能夠提升茶具的溫度,讓泡出的茶更加好喝,當然,這也是一種待客的禮儀。我會心一笑:挺有儀式感的,呵呵!
小廖又衝淋了4只白色盞形小杯,分別在我與柴君、他與父親面前各擺放了一隻。幾分鐘後,“驗證”開始。倒幹一次,加一次水,算一道茶。正好,倒幹小廖杯中茶,剛夠每人喝一小杯。茶過五道,柴君忽然問我:“喝出茶中的慄香了嗎?有沒有回甘的感覺?”哈哈,我已口渴難耐,舉杯即飲,儼然喝一小盅酒,脖子一揚就幹完。他不說,我只覺得挺香、挺好喝,別的就說不上了;經他一說,我再去感受,的確齒頰留香,回甘綿長。
說起茶香,我回想起了前些年的一件趣事。有一回,家人嚷著要吃茶葉蛋,我便從櫥櫃裡找出兩盒陳茶,一看是“羅洋曲毫”。茶葉筒上寫著:浙江大學茶學系研製,江山市十羅洋茶場出品。記得已存放了一兩年了。不想,如此陳茶,鋁箔袋封口一開啟,但見茶形細緊勾曲,顏色黃淡綠濃,其茶香撲鼻而至。那種香味,我說不出什麼香型,只覺得非常好聞。當即深深吸了兩口,頓覺神清氣爽。哇,這麼好的茶葉拿來煮茶葉蛋,豈不是應了家鄉那句歇後語:打破五石缸做硯瓦——因小失大?哈哈,我隨即又“發明”了一個歇後語:羅洋曲毫煮茶葉蛋——暴殄天物……
回到正題。當下“驗證”,茶過十道,仍有慄香。不過,經我觀察靜思,這與茶葉和水的比例多少,還有上一道與下一道間隔時間的長短,皆密不可分。像我平時喝茶,一大杯水,僅像燒菜放蔥花那樣投入少量茶葉,且一杯茶要喝個把小時,何言茶過七道?
無疑,羅洋曲毫是相當經泡的。“茶過七道,空杯留香”,並非浪得虛名。
“經泡本來就是高山茶葉的特性。”小廖解釋說,“經泡靠的是茶葉的內質,當然也要輔以恰當的揉捻工藝。”
說到工藝,我急著要到車間裡看一看。穿上鞋套,換上白色工作服,我與柴君隨廖家父子來到了茗香瀰漫的製茶車間。一臺臺殺青機、揉捻機、曲毫機、烘乾機、提香機,各就各位,井然有序。說起羅洋曲毫的一整套工藝技術,廖松柏滿心都是感恩之情。
十七八年前,茶場的生活苦不堪言。住的是簡易房,吃的是粗茶淡飯,偶爾才能吃到一點豬肉。那時,還沒有智慧手機,住地又不能上網,讓人悶得慌。更要命的是,宿舍沒有浴室,只能擦身,無法洗澡。然而,浙江大學的教授卻在這樣的地方安營紮寨。茶學系的系主任龔琦教授,在這裡一呆就是一個星期,而蘇祝成教授帶了3名研究生,一住就是3個月,苦得兩位女生幾乎掉下眼淚……
“那個蘇教授,真是了不起啊!”廖松柏深情地回憶道,“那時,白天要評比茶樣,驗收茶青,做茶都在夜晚,我們幾乎天天干到天發亮,一天只能休息三四個鐘頭,有時一天24小時也沒合過眼,可為了做出心中期望的好茶,蘇教授一刻也沒離崗,全身心的投入。”
“茶過七道,道道都有浙大師生灑下的情意啊!”聽了廖松柏的深情回憶,我由衷地感嘆。
高山茶場
很有個性的茶園,是這個樣子
在茶場食堂吃過中飯,我和柴君都鉚足勁兒,隨即動身,向心馳神往的十羅洋高山茶園進發。
憑我等的腿腳,徒步上山當然是困難的。廖松柏欠欠身子說,上午進車間時,看到攤青房裡,有一批青茶殺青殺得很不理想,他要留下來琢磨琢磨,看看有沒有法子補救,因而,只好讓小廖用皮卡車送我們上山,他要失陪了。
殺青怎麼啦?我帶著心中的疑團,若有所思地坐上了皮卡車的副駕駛位。
那盤山車道,似乎專為這皮卡車量身定做的,可謂少一尺則太窄,多一尺則富餘。隨著車子盤旋而上,我的心漸漸收緊,只覺得隆隆的車聲裡,散發著一種濃濃的險味。一路上,我很想與把著方向盤的小廖說說話,可又怕他分了心而馬失前蹄。哇塞,一腳不慎,車輪子滑出車道,那就……
反觀小廖倒是泰然自若,有問必答,應答如響。
剛過而立之年的廖鵬飛,眉清目秀,一表人才。說起話來不緊不慢,有板有眼,並不像其父那樣風風火火,轟轟烈烈。聽他說,他走出大學校門,就跟父親進山學做茶,然後又脫產到浙江農林大學進修了兩年半。看這架勢,廖氏茶人後浪超前浪,自是一種必然。
車子在山坡上爬行了大約10公里的路程,我終於見到了魂牽夢繞的十羅洋高山茶園。
十羅洋,真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茶園。若說雲霧繚繞,高山就是這樣,並不稀奇;若說茶苗蒼翠欲滴,哪個茶園也都這般,司空見慣。可這裡,前後左右,層巒疊嶂,山澗泉水叮咚;臨近山巔處,還鑲嵌著一個高山湖,遠看湖面蔚藍如鏡,近看湖水清澈見底。她南邊的不遠處,是千畝原始次生林;她西邊的不遠處,是一個總庫容達2.48億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庫。茶園的最上端,海拔達1275米。熟稔茶業的柴君說,在這麼高的海拔上,冒出近千畝連片茶園,這在浙江省範圍內,可謂首屈一指。
啊哈,茶園隱於仙境!難怪神秘!
“也有不好的地方。”看我一聲讚美一聲嘆,小廖不無遺憾地說,“在忽冷忽熱的日子裡,一陣冷空氣襲來,城裡人就是多穿一件衣服的事,可這裡卻要凍壞大量茶芽。”
是啊,城裡或已春暖花開,這裡依然冬意綿綿。幸好,春姑娘只是姍姍來遲,不會始終不到。
“你們施化肥、灑農藥嗎?”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我們的茶園肥料靠菜籽餅和桐籽餅當家,配合少量的高檔複合肥。”小廖指指像哨兵一般立在茶園的太陽能殺蟲燈說道,“主要靠這些玩意兒對付害蟲。這裡氣溫低,春茶發生病蟲害的機率接近零。春茶後,萬一遇到特殊情況,非施農藥不可,那也會按照綠色食品的要求用藥,況且,我們只採春茶,不採夏茶與秋茶,冬季更是封園的。”
茶園裡,有幾十個採茶工在晃動——據說,最多時有一百多位。在一條小道旁,有位頭戴斗笠、身挎竹簍的女工,一雙靈巧的雙手左右開弓,我湊上前去問她一天能採多少斤。她莞爾一笑,說:“說不準,三四斤吧。”她又補充說:“採不快的。採快了,不符合標準,驗收通不過的。”
果然,在茶園旁的一座小屋裡,一位採茶女正低著頭挑揀驗收沒過關的茶青。站在一旁的驗收員頭髮花白,卻聲若洪鐘:“不是一芽一葉的,芽頭採壞了的,用指甲採下來的……統統要揀出來扔掉。”
說起採茶與驗收的矛盾衝突,小廖說,現在平靜多了,早年出現過的情景是,妻子送茶驗收,丈夫則站在旁邊持刀威脅,但就是這樣,那也沒有敷衍了事,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麼,採一斤茶青,付多少工錢呢?小廖說,前期採的50元,後期採的45元。這讓我不禁咋舌:大約四斤半茶青才能做成一斤羅洋曲毫成品茶,一斤茶的採摘費就要數百元啊!
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
走出驗茶小屋,一棟白牆青瓦二層樓映入眼簾。小廖說,除給採茶工按量付酬外,還要在山上給他們蓋宿舍樓,辦食堂,配備洗衣池、洗手液,管吃、管住還“管手”。
“管手”,這話怎麼講?小廖解釋說,進茶園前,採茶工的手,必須一乾二淨;如果用上洗手液,還得用清水反覆沖洗,否則,有可能將手中殘留的化學異味、香味,傳遞到茶芽上,壞了茶葉天然的香味。都精細到這個分上了?這在先前,我是不可想象的。這也難怪小廖說,即使茶葉賣上高價也未必賺大錢。年產量兩三千斤的羅洋曲毫,500克茶最高價達5800元,次高價3000元,最低價60元,總均價在1000元以上,如此價位,按小廖的說法,一不小心,仍可能入不敷出。
嗨,有個性的茶園,有個性的茶人!
十羅洋茶場
誰知杯中茶,葉葉皆辛苦
下得山來,陽婆已將金光收在了半山腰。
廖松柏匆匆從車間裡走出來,一臉真誠地挽留我與柴君在茶場裡住一夜。我說,住夜就不住了,就是有個小小的想法……
“啊,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廖松柏眉頭緊鎖,神色凝重,“本來你們難得來一趟,應該包點新茶給你們帶回去,可是最新一批殺青不到位,產品不理想,拿不出手啊……”
的確,來前就有想法,一定要買個半斤八兩新茶回去,請家人、請友人一起品嚐品嚐,從中分享這次十羅洋之行的深切感受。可看這情景,只得空手而歸了。
小廖駕車送我與柴君回城。廖松柏則留在了茶場,說是要與員工一起熬夜做新茶,以免再次出現操作失誤。
一坐上車,我就問小廖,這批殺青沒殺到位的茶葉,最終的命運將會如何。小廖嘆了口氣說,300多斤茶青,都將化為塵土。
這多可惜啊!
當然可惜!然而,為了捍衛十羅洋茶葉的光輝形象,他們似乎別無選擇。或許,這也是羅洋曲毫能賣個好價錢的一個秘密!
聽小廖這麼一說,我空手而歸,沒有失望,卻心悅誠服。
據小廖透露,其父早年銷茶受挫之後,痛定思痛,轉而埋頭打造過得硬的品牌,哪怕血本無歸,也不讓一葉不合格的產品流向市場。漸漸地,羅洋曲毫得到了江山本地茶友的追捧,繼而得到了在外地生活的江山籍茶客的垂青。交口讚譽,口口相傳,外地客商也聞香而來。近幾年來,銷路已不是事。
“嗯,那殺錯青,是怎麼回事呢?”惋惜之餘,我滿腹狐疑。
“殺青殺過了頭,芽葉可能被烤焦;沒殺到位,則香氣不足,口感苦澀。”小廖不無感慨地說,“茶葉是有靈性的,機器並不懂這種靈性,還得人去與她對話。”
是啊,有哲人說過,世界上找不出兩片相同的葉子。茶仙子們,一離開茶樹,雖然共享一個名字叫“茶青”,其實芽葉有長有短,有胖有瘦,有濃妝有淡妝;今天下山的與昨天下山的,早上下山的與下午下山的,大晴天下山的與陰雨天下山的,也是千媚百態,各有各的個性。然而,卻要殊途同歸,一樣經歷採摘、攤青、殺青、回潮、揉捻、做形、初烘、復烘等等磨練,最終以同樣的姿態投入人們的茶杯中,這多不容易啊!
車窗外,一座座山峰徐徐而過。在車輪的顛簸中,我恍恍惚惚,彷彿覺得一縷茶香過了千重山。
唉,世人皆以一杯清茶之說,隱喻自己的清貧生活而自我陶醉,可曾想過茶之不易呢?
誰知杯中茶,葉葉皆辛苦啊!(文/肖梁 《綠色中國》2021.7A)
本文來自【綠色中國】,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