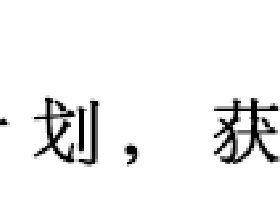走著走著,我的腳變得很沉。腳趾像陷入了細細的沙灘裡,我低頭一看,在小商販手裡買的八塊錢的一次性鞋套腳背處破了三個洞,我解開繩子系的結,把鞋套丟掉。在沙漠裡行走,鞋子總是很快就灌滿了沙子,戈壁荒漠的沙子很細,細得如流水,機靈得如小鬼,你不覺得硌腳但也發現它們總是無孔不入。以至於到了蘭州,我時不時還要把鞋子翻過來,倒出一揪細沙。
來敦煌算圓夢。有段時間我常常覺得生命虛無,自己有些無力感,把這種感受說出來的時候有人懷疑我得了抑鬱症。 每當我陷入這種不良情緒的時候,我有自己研究出來的一種解脫的方法——學新東西。我請了網球教練,打網球的時候,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一顆綠色的小球上。另外就是買了大量的與莫高窟有關的書籍,學習中國藝術。
離開敦煌,在蘭州轉機,我棄掉後半程,在蘭州住幾天,沒有任何任務,只是來看看韓松落老師,見見朋友,朋友也是以韓老師為中心建立的,自從去年來過蘭州,對這裡就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這會兒一見面他就跟我坦白了自己有抑鬱的情緒,就是那種覺得做什麼都覺得沒意思,但又沒到生病的程度,一種間歇性的狀態。我才知道不是隻有自己才這樣,幸運的是我們都很警覺,願意承認和麵對自己不同的狀態,食慾很好,也不失眠,當然還沒有進入大家所說的那種病理的狀態,就看我們在西北啃羊肉的樣子都能確信一定沒有抑鬱症。可是我們又都恥於向外人談起,我怕得不到理解,或者被看成矯情。
見到韓老師,我無法抑制地流露出對敦煌的喜愛,像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興奮地描繪著戈壁和莫高窟裡的景象。別笑我,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直到敦煌,我準備的書還沒看完,加上路上又添了一些新書,箱子越來越沉,還有一些朋友得知我的喜好,這個塞一本《絲綢之路》,那個塞一本《馬家窯文化》……包裡鼓鼓囊囊的,每本又都愛不釋手。蔡景暉老師回了北京又給我找出一些寫敦煌的書,快遞到家裡。
有些地方你直接去就可以,但是敦煌絕對不行。瞭解敦煌是有門檻的,只是來了,只是看過,遠遠不夠,就連莫高窟裡的講解員也“看人下菜碟”,遇見你懂一些,便多講一些,講得更仔細一些。
生活裡充斥著大量資訊,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這件事好像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必要了。我有意訓練自己專注於一本書或一幅畫的能力,在閱讀中瞭解世界。在每個窟的時間有限,可以看的細節太多了,你必須全神貫注,把“痴迷”狀態獻給每一個手電筒照耀到的細節。
回想起剛落地了敦煌,看到機場上空兩個碩大的紅色大字,內心一陣澎湃。一大早的飛機,其實沒睡幾個小時,我從上海出發,在蘭州轉機,中午抵達敦煌,立刻感到空氣變得稀薄了,視野無比開闊。按理說我應該旅途勞頓,應該需要在酒店休息一會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敦煌的炙熱的陽光有傳導能量的魔力,我下午就找到司機出發了,在路上特別興奮,如一隻放出籠子的鳥兒,眼睛如飢似渴,貪婪地看碧空如洗的天,看一排排高聳的白楊樹,看遠方層層疊嶂的山。
我喜歡北方的白楊樹,不論粗細,統統直挺,彷彿站崗計程車兵,永不低頭,也不妥協,就像外公以前說的“人活一口氣”,白楊樹就有那口氣,讓我覺得高貴。司機告訴我,白楊樹前一團團毛茸茸的樹是饅頭柳,沒有垂下來、搖曳的柳枝,而是一顆顆像兒童塗鴉出來的圓球似的綠色,樹冠呈半圓型,狀如饅頭。
一條筆直的公路通向金色的沙漠,我欣喜不已。進入鳴沙山有幾種途徑,駱駝、馬、四驅車、直升飛機、徒步……我買了一張駱駝票,流程非常市場化,跟著工作人員走進一大片駱駝休息的區域,挑選一隻我喜歡的駱駝坐上去,整個身體被夾在兩座駝峰中間,那過程就像在西域王國某個市場上的買賣。駱駝站起來的時候讓我嚇了一跳,起伏非常大,它們排成長線,搖搖晃晃向前,行進得比馬慢,脖子上的鈴鐺跟著起伏的身體發出叮叮的駝鈴聲,我們每個人都像在盪鞦韆。
駱駝滿足了我對行走絲綢之路的想象。駱駝看上去如此溫順和勤奮,讓人忘記它們發起脾氣來也是很不好惹的動物。騎駱駝實際非常顛簸,那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時候,我感受到屁股一陣火辣辣地疼,才知道磨破了皮,不敢把水淋上去,可想而知有多顛簸。
又一日去沙漠營地,屁股還沒好,選了四驅車,戴上頭盔和防沙眼鏡,繫好安全帶,我扭頭對司機說,不要給人刺激,開慢一點嘛。司機那表情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只能透過頭盔的縫隙看到他的眼睛和嘴巴。他一臉不屑地說,那還有啥意思。
啟動馬達,我們藍色的戰車歡呼著向沙漠裡奔去,沒有地圖,路線都在司機的腦子裡,黃沙四溢,車輪奔騰,一個大油門踩上去,我們上了陡坡,到了坡頂,懸停一下立即縱身躍下,我整個人都失重了,雙腿無力,心裡發慌,張開嘴情不自禁地喊了出來,吃了一口沙子,又趕緊閉上嘴。
我猜司機心裡這下可得意了。沙漠是他的主場,好好耍一下這些從東南地區來的人。沙漠一望無邊,與天相連,彷彿什麼都沒有,只有黃沙和藍天,偶爾能看到一些植被,是難能可貴的綠色。
我們的車像一隻鋥亮的藍色遊隼,張開翅膀,衝進餘暉下的山谷裡。沙漠在夕陽中閃閃發亮,我們只是這沙漠中的一道弧線,所到之處,在平滑的沙面上刻出一道深深的大地紋理。又是一個上坡,我們的車像沿著碗的內壁滑行,拐一個優美的大彎,向心力把我們拉進谷底,我們的車揚起沙塵,就像海浪激起的白色浪花,浪花一朵朵飛濺。
我看到盆地相對平緩的地面上已經支起了白色的帳篷,那是我們的目的地,也是夜棲地。就隔一座沙丘,隔壁的盆地是一汪綠色,盛著月牙型的湖,在乾燥的沙漠裡怎麼會出現清水呢,看到湖彷彿看到海市蜃樓。
在大漠風光中,我對每個事物的尺寸沒了概念,看什麼都覺得渺小。想起自己曾在一本書上讀到,人在沙漠,看每件事物都覺得事物的形狀消失了,變得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與無邊無際的蒼茫大漠融為一體。這與事物本身的真實大小無關,而是因為人很難在腦海裡想象出這片荒漠的面積和邊界,只有走到荒漠盡頭的時候,才能察見端倪。
我覺得司機調皮得很,明明不遠的路程,被他開得七葷八素,彷彿道路有多麼險阻似的。他耍夠了,最後一個極速俯衝,我們像凱旋的老鷹降落到一小塊平地上。真的停下來,才發現自己腳下的沙漠多麼遼闊。
跳下車,我覺得一陣頭暈眼花。敦煌研究院的謝老師塞給我兩顆硬邦邦的梨。敦煌的梨硬邦邦的,但是日照時間長,非常甜,在沙漠裡吃梨覺得甜上加甜,吃完連空氣都有了梨子的香氣。
口乾舌燥,大家總是仰著脖子往嘴巴里灌水,喝了水就要解手。要去廁所,需要重新上車開出沙漠,我不願意。男人簡單,可以翻過一個山丘,就地解決。有時不幸被唐突開來的四驅車撞見,防不勝防。我就靜候著天黑,觀察四周,想好躲到哪個山丘後面。
敦煌的夜晚總是很晚到來,至少要到7點半之後才覺得白晝要退場。走在沙漠上,我喜歡看自己的影子,像皮影戲一樣。毫無遮攔,大漠風景盡收眼底,大家紛紛脫掉鞋子,赤腳走在沙子裡。上一秒還被太陽烤得面板生疼,日落總在一瞬間,氣溫驟降,大家紛紛披上外套。後來我們就躺在沙子上,仰面朝天,星河如棉被,我太久沒有看過這麼多星星了,夜空如巨大的螢幕閃動著雪花,星光牧野,不可思議。
蒼茫寂寥的沙漠中,人與人的情感顯得格外顯眼,彷彿在緩和著大自然的荒涼。火把點燃了我們提前搭起的幹樹枝,燃燒成一個散出熊熊熱烈火焰的篝火。
這是我在敦煌的最後一晚,大家都喝了酒,我看到從廣州來的朋友勾住當地朋友的脖子,他們幹了一杯酒,當地朋友說,只要你來敦煌,就必須告訴我。兩個人不斷重複著相似的話,手緊緊握在一起,格外用力。這樣的畫面我已經太久沒有看過了,竟覺得又感動又唏噓。對我來說,熱烈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會覺得尷尬,我好像退化了這部分當面表白的功能,常常在喜歡的人面前憋得面紅耳赤,語焉不詳。
我將心中部分潮溼陰冷換成了大漠黃沙。
在沙漠腹地,我們像被遺忘在另一個星球的人,與世隔絕,用喧鬧放肆的歌聲和舞步回擊著空曠寂寥。夜的黑絲絨布把我們裹得更緊了,於我只是一場開始,於很多人都是無眠。
吃飯前摔了一跤,我拖累了小鵬,手裡還舉著莫高窟冰棒兒。
達叔給每個人拍了最唯美的一張照片
喜歡就關注我吧[可愛]
喜歡此內容的人還喜歡
- 眾人皆睡我獨醒:身體沉重,精神清醒,失眠新手的不習以為常
- 簡·奧斯汀小說《愛瑪》:一個時代的縮影,一位女性的“覺醒”
- 平凡中各種最幸福的時刻:幸福總在不經意的發生,只是沒有去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