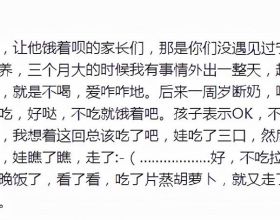安德烈·魯布廖夫代表作《聖三位一體》
《鄉愁》
《犧牲》
名人的觀點通常被我們用來作為重要的參照點。比如齊澤克在分析塔可夫斯基的《飛向太空》時認為父親的隱喻是該片的核心:英雄重新與他的父親,亦即律法的象徵界形象結合,從而重構了現實與父親領域的關聯。但同時,齊澤克(以及弗雷德裡克·傑姆遜)對老塔作品的某種精神旨歸又嗤之以鼻——將其迴歸家庭的取向與好萊塢閤家歡肥皂劇等同,並將其精神懺悔、告解、祈禱視為說教,視為過時的、令人不耐煩甚至迂腐、可笑之物。考慮到“齊大爺”是斯洛維尼亞人,從斯拉夫民族的整體來看本來會與老塔有某種同構性,但事實顯然是無情的,利己主義早已是當今知識人的思想主流底色,並由此必然產生了種種虛無主義問題,當然與此同時沒有人會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這就好比世間人不斷追逐快樂,卻不知道自己是在不斷製造痛苦的因。
“俄羅斯使命”
涉及到對老塔作品的評價傾向,這當然會導致一種方向性的顛倒,即將他看作一個形式主義者,並破解其電影裡的各種“密碼”:泥土、水、火、漂浮……而將最主要的、最有價值的東西當作一種時代或個人的“侷限”。
沒有比老塔的兒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塔可夫斯基(即通常所說的小安德烈)對父親的作品更有發言權的了。這不僅因為血緣的紐帶。他是老塔最寵愛的兒子,從小父親就帶著他拍片,並有意識地教他拍電影。在瑞典拍攝的《犧牲》的劇組中,英格瑪·伯格曼特地安插了自己的兒子,那個時刻老塔恐怕是希望自己的小安德烈快長大,也可以跟著伯格曼“偷師”。雖然小安德烈長大了並沒有走上這條路,但是他擁有最完整的老塔的文化遺產版權,包括超過600小時的影像資料。兩年前,他用這些素材剪成了一部紀錄片在威尼斯電影節展映,片名就叫《在電影中禱告》。
“禱告”這個詞不會有歧義的,也不象徵或隱喻什麼。老塔有記日記的習慣,並將自己的日記稱為“殉道記”,“殉道”的意思也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問題也出在這裡。這不僅對於咱們來說是一種“隔”的思想文化(例如電影《安德烈·魯布廖夫》的一個重要章節,被翻譯作“安德烈的激情”,實際上那是“安德烈的蒙難”,跟“聖女貞德蒙難記”一個道理),在西方也陌生已久,大多數人的態度就像《鄉愁》中的女翻譯,在教堂裡好奇地張望、質疑,在自己有限的知識體系中批判。但正如教堂裡的神父溫和地向她指出的,真想得到什麼加持,首先得學會跪下來。
但是這一點又何其困難。更何況,俄羅斯文化本身就是獨特的。這裡的獨特,並不是我們平時理解的“和而不同”或“各美其美”之意,而是要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去看。俄羅斯民族在一千年前經過了聖弗拉基米爾的施洗,這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大事:為什麼是俄羅斯?簡單地說,千年以來,俄羅斯知識分子關於自己道路、命運的思考,包括很多影響全人類的重大歷史事件,都與此有關。
這種思考首先是一種猜測,即猜測俄羅斯民族在全人類共同命運中所承擔的“使命”是什麼。按照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說法,就是“在人間恢復神的三位一體的真正形象”。這個說法很深也很複雜,無法展開說,但可以明白地指出,三位一體,包括了身體(這裡不僅是肉體)和靈魂的統一。千年以來,關於身體和靈魂的思考,賦予了俄羅斯文學藝術以深度,在各個歷史階段都不例外。世世代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在這個方面似乎有一種傳承性,從這個角度看,蘇聯詩人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和他的兒子、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之間,就有這樣一條精神紐帶。
家族精神紐帶
俄羅斯作家、導演馬克西姆·古列耶夫的《塔可夫斯基父子》(也可譯為《塔可夫斯基宇宙》),不僅是一出關於家長裡短的八卦肥皂劇。誠然,阿爾謝尼本人的三次婚姻,那些戲劇化的“狗血”情節(割腕、疑似PUA、跟蹤……),足以坐實其“渣男”名頭。但是,這些都不是他寫作的真正意圖。既然現實生活中是如此一地雞毛,那麼精神生活中又是什麼讓他們這個家族的成員如此接近?
雖然瑪麗亞·維什尼亞科娃(即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母親)算得上是“喪偶式育兒”,但安德烈並不是孤兒。他有一個大詩人父親——這一點對他而言非常重要。在他的童年時代,亦即衛國戰爭期間,真正的孤兒反而比比皆是。德米特里·利哈喬夫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蘇聯知識分子經受住了嚴酷的考驗。相比較同時代蘇聯詩人,阿爾謝尼更是傳統的(這個詞是多義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他的老師包括勃留索夫、索洛古勃這些白銀時代的精英。
人的生命與基督的生命,此岸與彼岸,宇宙論,身體和精神,都是他詩歌的重要主題。“我比死人更知曉死亡,我是活人中最活的生命”,其中的意思很清楚,但是沒有過靈性生活的人就會對此茫然不解。而瑪麗亞·維什尼亞科娃恰恰是深諳此道者。她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盡其所能給兒子的教育——童年就開始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要說普希金了),鋼琴,都是非常精英知識分子式的,福音書一定也是其中重要的內容。有一點我們不可忽視,即她知道父親對於一個兒子成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她懂得這個父親精神價值的前提下。我們不難猜想,她不但沒有給兒子灌輸對父親的恨,反而很可能給他解釋過阿爾謝尼詩歌之於那個時代的意義。
先賢範本
安德烈的精神來源非常複雜,但神奇的是,像《安德烈·魯布廖夫》這樣的電影卻獲得了來自宗教界的肯定。我們只要讀一下這個劇本,就會驚歎於作者對古羅斯文化、對基督精神的準確理解。舉這個例子對我們理解安德烈的“使命感”是很有必要的。他絕對把藝術創作看作一種使命。但自己是否就是那個“天選之人”,直到後來他才確信。藝術就是要表達崇高人類理想的典範——這個他從來沒有懷疑過。但今天觀眾理解老塔的另一個難度在於,今天很多藝術(包括文學)從業者,似乎從來不考慮自己創作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甚至都不考慮是否會給受眾造成很大危害,他們所關心的無非是自己——自己滿滿的貪嗔痴,稍微探究一下就能看見其中利己主義的本色,很多有害人類的東西,卻被當作“有個性”的證明(想想在《雕刻時光》中,老塔說,在這些作品中只聽得到“我、我、我……”)。
而老塔的“典範”是達·芬奇,因為達·芬奇的創作是人類崇高的精神之美的體現,真善美的高度統一。而按照利哈喬夫的說法,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樣的典範主要體現在兩個人的身上,一個是大詩人普希金,另一個就是聖像畫家安德烈·魯布廖夫。可以說,年輕的老塔拍這部電影是有些“神助”的。安德烈·魯布廖夫代表作《聖三位一體》可以視為這部電影的中心視覺影象(後來也作為這部影片的海報主視覺,並出現在另一部影片《鏡子》當中——和該片中“普希金的書信”環節,那是一個關於“俄羅斯使命”的重要文字),在電影劇本中,聖三一修道院院長有著重要分量,他是德米特里·頓斯科伊大公的“老兄”,是對俄羅斯精神文化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也是一個“自我犧牲”的榜樣。這幅名作畫的是聖父、聖子、聖靈以三位天使的形象來到亞伯拉罕面前。他們共進亞伯拉罕為他們準備的聖餐。這幅畫的每一個細節都有明確的聖像畫影象學解釋,在此不贅述。但是安德烈·魯布廖夫用明亮、輕盈、柔和、清麗的筆觸和圓形的構圖傳達出一種友愛、和諧、統一的意義,天使們的安寧、寧靜、沉思,給觀者帶來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
只有心懷歡樂與光明,才能描繪出這種智慧的寧靜,傳達出博愛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讓人們瓦解彼此的敵意,放下彼此的仇恨。《安德烈·魯布廖夫》這部影片所傳達的正是不和諧時代對和諧的號召——而這一點只能透過沉思和靜修,內心的自我深化、思考來完成,它不是藝術家恣意的個性表達,而是沉潛思索的顯現。可如果以上這些您都不瞭解,但是觀看過程中體驗到一種寧靜而崇高的、略帶憂傷的感受,那您已經抓住了這部影片最重要的精神氣質。
《塔可夫斯基父子》告訴我們,老塔在這一階段讀了很多關於雅典思想家、聖者亞略巴古的丟尼修的著作。他的思想在安德烈·魯布廖夫的年代有著廣泛的傳播。這種思想本身就帶有一種基督教與泛神論結合的特點。我們在影片中感受到的那種氛圍是準確的,所有的形式都是為了影片的中心意義服務的。這一點也體現在老塔後來的其他幾部作品中。
他的電影確實有觀看門檻,對於電影這種大眾屬性極強的藝術而言,確實有點不可思議。所以說看他的電影需要我們換一種觀看方式,訓練一種新的觀看技能。總體來說,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崇高感”經由對俄羅斯特殊使命、人類整體命運的思考,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統一,即使在電影發展的黃金年代,也屬於極為稀有的文化瑰寶。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