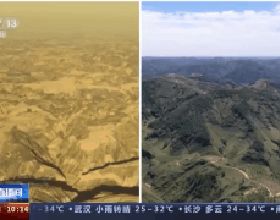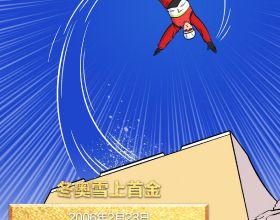作者:蔣巍雪揚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華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戰的怒潮。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愛國志士和熱血青年紛紛投奔延安,要求參加抗日隊伍。其中有家資鉅萬的豪門閨秀,有住洋樓、坐洋車的大軍閥之女,有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女。曾在中國婦聯擔任領導職務的王雲告訴我們,延安時期分配到中央婦委工作的25位女青年中,有24位出身地主、資本家家庭,一位出身富農。“畢竟,只有富貴人家的孩子才能讀上書嘛。”她說。
資料圖片
延安一下子湧來那麼多女青年,於是毛澤東提議,辦箇中國女子大學。
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國女子大學的開學典禮在延河邊新建設的校園廣場上舉行。身穿藍灰軍裝的近千名女同學坐滿會場,各班互相拉歌,歌聲一浪高過一浪,會場一片歡騰。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八路軍代表鄧小平、新四軍代表張鼎丞等魚貫走上主席臺。時年46歲的毛澤東走在最前面,他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濃密的黑髮很長並向後掠去,褲子上綴著補丁,舊上衣顯得很寬大,口袋裡塞了些書報。校長王明作報告時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陳雲、鄧穎超等領導同志,將他們擔任重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薪水捐獻給女大以購置圖書,林伯渠捐贈了一批油燈,鄧小平捐贈了十幾匹戰馬。會場一次次響起熱烈的掌聲。接著,毛澤東講話,他的著名論斷“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便是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的。
晚飯是難得的大會餐。有饅頭、“國共合作飯”(大米和小米混合)、豬肉、牛肉、羊肉,還有又香又脆的“列寧餅乾”(小米鍋巴)。飯後,舞臺上舉行歌舞晚會,不少老鄉也圍攏過來看熱鬧。一個女同學表演口琴獨奏,有老鄉驚異地說:“這個啃骨頭的節目真好聽咧!”著名紅軍女將領、女大教務長張琴秋穿一身紅綢衣,抱著一個穿西服戴禮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誼舞,席地而坐的毛澤東和全場觀眾笑得前仰後合。
女大校舍是沿楊家嶺延河東岸新挖的窯洞,層層疊疊,排列齊整,大約百餘孔,對岸是中央黨校和青幹校。每天清晨5時,伴著嘹亮的軍號聲,女孩們迅速到延河邊集合跑操習武,喊殺聲響徹天地,過後端上臉盆、牙具到河邊洗漱。姑娘們嫋嫋婷婷地下山,遠遠望去,就像一條藍色的小溪順坡而下,形成一道美麗的景觀。
女大的窯洞每孔不足20平方米,8至10人擠一條長長的板鋪。夜裡起身上廁所,回來後常常就沒空位了,要拱進去慢慢擠幾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廁所在山坡上,這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卻害怕“鬼”,天一黑就不敢上山解手。一天夜裡,一個女孩出來方便,剛蹲下,猛地發現對面草叢中有一個黑影,嚇得汗毛倒豎,喊了一聲“有鬼”,便撲上去廝打起來。大家聞聲跑出來一看,原來是另一個窯洞的女生,因為怕冷,從頭到腳裹了一條毯子。大家笑得人仰馬翻。
女大的教員隊伍絕對超一流,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張聞天等領袖人物都來講過課,教員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講哲學的是艾思奇,講革命理論的是陳伯達,講音樂的是冼星海、鄭律成,講文學的是丁玲。講課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次他總讓警衛員抱來一摞馬列著作,講課時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便說不用記了,你們去查第幾卷第幾頁好了。姑娘們驚得五體投地,都以為遇到了“真馬列”。後來透過整風運動才明白那是不管用的教條主義。
青年們初來時並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和組織紀律,因此發生了許多趣事。
湖南姑娘艾森原名歐陽中道,系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後裔。她聰慧勇敢,中學時就讀了很多進步書籍,成為當地學運領袖。地下黨組織悄悄接近她,動員她加入中共。一直做著“延安夢”的艾森不屑一顧地說:“我才不入你們的‘雜牌軍’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個正宗的共產黨。”上世紀90年代我們採訪她時,白髮蒼蒼的艾森笑著說:“就因為這個,我的黨齡短了好幾年。”
愛國將領杜漢三的女兒翟穎投奔延安後,表現優秀,卻長期沒提出入黨申請。組織上問她為什麼,她認真地說:“共產黨員必須是不怕死的英雄,砍頭槍斃我肯定不怕,但萬一受到敵人的嚴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鍛鍊呢。”這期間翟穎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術,“鍛鍊”的機會來了:她堅決拒絕打麻藥,讓幾個護士死死按住她。到了冬天,她跑到延河邊鑿開一個冰窟窿,把雙手伸進去咬牙凍,結果手背上的兩個大凍瘡跟了她一輩子。
女大還辦了陝幹班和特別班,前者負責培養當地女幹部,後者給沒上過學的長征女紅軍掃盲。陝幹班有個折聚英,6歲就給一家皮匠當童養媳,挨打受罵,吃盡苦頭。紅軍來了以後,折聚英從村裡帶出十多個童養媳報名參軍。進入女大後,折聚英最愁的就是學文化。也是怪了,她一見那些橫橫道道的字,手就哆嗦得握不住筆,渾身痙攣得像打擺子,有兩次還一頭栽倒昏了過去。有一天指導員薛明拿來一張地圖講長征。折聚英一見地圖就跑了,那些長征過來的女兵也炸了,橫眉立目地喊:“我們爬雪山過草地,走了二萬五千裡,你一條小線線就給嚇跑了?”後來,折聚英因為沒文化,做了幾十年的幼兒保育工作,組織上要提拔她,她堅辭不受。有趣的是,離休後她倒是把老年大學的畢業證拿到手了。
那時陝北生活的艱難困苦是外人無法想象的,但女孩愛美的天性沒有改變。生活安定下來後,姑娘們首先就想照鏡子。當過電影演員的蘇菲恰好帶來一塊鏡子,見同學們不時跑來照照小臉蛋,於是說咱們還是“共產”吧,接著把鏡子“啪”地摔碎,每個窯洞分得一小塊。入夏部隊只能發一套軍裝,沒有襯衣。女孩們覺得脖頸處太空蕩也太難看了,不知是誰靈機一動發明了假領子:用白線織成一條領襯,縫在領子裡面,看起來就像穿了一件白襯衣,又整潔又美觀。這個風氣一直傳到五六十年代。
1941年9月,為貫徹精兵簡政方針,女大與其他幾所大學合併為延安大學。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女大為我黨和我軍培養輸送了上千名婦女幹部,她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卓越貢獻,書寫了許多或傳奇或動人的故事,也有人為了革命事業英年早逝。
——成都女孩呂璜後來進入延安保衛部,和丈夫布魯(又名陳泊)成功破獲了震動整個延安的“軍統特務案”,一舉抓獲60多名潛伏在我黨政軍及各行各業的特務。
——蒙古族姑娘烏蘭少女時代就入了黨,曾按照地下黨的安排,隻身炸過天津的日本商場和貨輪。後來,她回到家鄉,成為馳名大草原的雙手打槍、威震敵膽的“飛將軍”。
——重慶女孩丁雪松後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駐外女大使。她的丈夫鄭律成先後創作了中國和朝鮮的軍歌。
——來自上海的蘇菲和來自哈爾濱的於藍,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
——侯波,一路靠乞討投奔延安的苦孩子,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女攝影家,為毛澤東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
——茅盾的女兒沈霞為奔赴抗戰前線,毅然在延安醫院做了“人流”手術,結果因感染去世。
——董邊和田家英(曾擔任毛澤東秘書)婚後生了一個男孩,因戰事緊張把孩子送給當地的一位農民。這位農民要求董邊立下字據,以後不許來要孩子。十多年後,母子之間相互知道了資訊,但董邊信守諾言,到老了也沒見孩子一面。
——康岱沙出身重慶豪門,離開女大後回到“陪都”重慶,從事地下黨工作,五年後再返延安。新中國成立後,她和丈夫陳叔亮成為外交戰線上的優秀領導幹部。採訪時,岱沙老人給我們看了夫婦共立的遺囑,最後一句是:“骨灰可撒到香山,做綠化肥料,也算最後的廢物利用。”
上世紀90年代,我們走了許多城市,採訪了近百名女大出身的老戰士,包括賀龍的夫人薛明、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她們的家,清一色的簡樸、清貧。呂璜家是水泥地,放電話的地方是一隻紙箱;我在王定國家剛剛落座,就從椅子上倒仰過去——一條椅腿因過於陳舊而折斷;在薛明家,沙發是破的,露著鋼圈。杭州大小姐出身的陸紅,晚年無數次將工資捐給災區和學校,自己居住的院子卻極為簡陋。我們坐在門口訪談時,她忽然衝屋裡的外孫喊:“那是公家電話,不許你用!”
時光荏苒,如今,我們採訪過的女戰士都已過世。但她們並沒走遠,她們就坐在街邊淡綠色的長椅上,微笑著,慈祥地、欣慰地注視著我們,注視著今天的年輕人,注視著美好的一切。
是呵,她們也有過花季——那是擔起民族救亡之重任、帶著血與淚的別樣的花季。
《光明日報》( 2021年09月17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