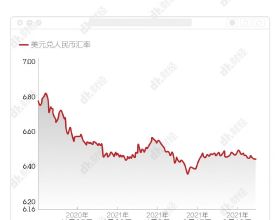如果普魯士作為政治地理概念,那麼它就有三個含義:第一,中世紀曾在德意志騎士團統治下的、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人領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倫家族統治下的普魯士王國,它是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聯邦內的一個邦國;第三,1918年德意志帝國覆滅後所設的德國的邦。
上述三者之間,存在著領土的、歷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續性。而真正充當德國曆史上正經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魯士王國。很難想象到,普魯士是從一個小小的、荒蠻的、窮困的東部邊區馬克,一個被人輕蔑地叫做“神聖羅馬帝國(即德意志第一帝國)的砂石罐頭”發展起來的。透過五個世紀奮鬥,普魯士成為德國的絕對領袖,歐洲的強權以及爭霸世界的龐然大物。在每次涉及到疆土的關鍵時刻,普魯士都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進行戰爭。也正是這種過度物化的自我膨脹,最終導致自己的被消滅,湮滅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顯而易見,在歷史上,普魯士問題是一個德國問題,一個歐洲問題,乃至一個世界問題。普魯士早已經不存在了,人民對它的很多過往記憶,已經相當淡化和模糊。如果人們對“普魯士”的記憶和了解只剩下,悲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世人對它抱有某種“深仇大恨”、乃至“談虎色變”非欲置之死地不可。1943年.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說:“我想強調,普魯士是萬惡之源。”這句話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責和納粹暴行歸之於普魯士。蘇聯紅軍在向柏林進軍時奉命徹底摧毀德國東部土地上普魯土容克的莊園。當第三帝國整個被摧垮後,1947年2月戰勝國在德國建立的最高機關“盟國管制委員會”公佈第46號通令,用英語、法語、俄語以及德語向全世界宣告:“普魯士邦,它的中央政府和屬下所有官廳至此全行解散。” 正是一項具體的措施,自此以後,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家,一個邦國,一個邦,從歐洲政治和世界歷史中消失了。
但是在今日世界的現實中,卻依然存在著眾多的“普魯士人"和“普魯士物”。普魯士的精神、文化和傳統,並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予以消滅。上世紀70年代後期,聯邦德國曆史學界首先發難、翻“普魯士是萬惡之源”的案。塞巴斯提安和烏爾利希合撰了《並非神話的普魯士》,提出普魯士並非因其“軍國主義”而威脅鄰國,普魯士只是由於它的“廉潔的管理機構和獨立的司法、寬容的宗教和開明的教育”而使其鄰國深感不安;普魯士在當年是歐洲最新式的和現代化的國家它比歐洲的任何國家更富有遠見,是純釋理性國家。
特別有意思的是當時民主德國的歷史學界對普魯士評價的“微妙”變化。70年代中期出版的《德意志人民歷史綱要》一書,還強調普魯士軍國主義鮮明的反人民性質,它代表普魯士貴族反動階級的利益。但自1978年起,民主德國曆史學家修正了以往那種簡單而僵硬的評價,提出要辯證地看待普魯士遺產,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一分為二。民主德國曆史科學8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闡明瞭普魯士在歷史上的進步方面。
新評價大致有五個方面:
一、普魯士的歷史不僅是霍亨索倫家族和容克的歷史,人民群眾為普魯士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最終迫使普魯士統治階級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中,順應歷史的程序發展。
二、普魯士也具有進步的傳統,它既是一個軍國主義和侵略性的國家,又是18世紀末和1848年革命中發生過大規模群眾起義的國家,是德國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最迅速的地區,是德國工人運動的發祥地。
三、在18世紀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普魯士具有“極富活力的國家制度”它十分善於使舊的封建制度適應於新的資產階級的發展條件。普魯士個別統治者採取了推動社會進步的措施,有限度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有條件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繁榮。這些統治者建立了一個具有高度集中的、合乎理性的、有秩序地和廉潔的國家機器。
四、普魯士貴族中的一些進步人物,特別是19世紀的“自由派”,促進了德國1807年以後的改革,為在普魯士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開闢了道路。普魯士在當時被德國資產階級愛國者看作是“進步的搖籃”,反拿破崙統治的民族反抗中心。普魯士在1813年的解放戰爭中起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
五、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在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尤其在準備和實行1848-1849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作為進步的階級力量,起過重要的作用。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資產階級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在蓬勃發展的革命群眾壓力下,進行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貫徹了1848-1849年統一的革命要求。
民主德國的歷史學家對普魯士所尋求的肯定,同聯邦德國的歷史學家為普魯士所作的辯護其角度雖然不一樣,他們所談的像是兩個普魯士,但卻有其共同點。第一,都只侷限於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國家的利益範圍之內,並以這種利益作為評論的出發點;第二,都是從國家政治軍事的角度來衡量普魯士的一切,而一種內在化的決定性因素全然未予注意。他們所談所論、所列所舉,並非沒有道理,有的還是道理子足,可以服人,但是如果不把普魯士”作為“世界的現象”放在“國際大家庭中來考察,就無從平服世界人民的心。難道丘吉爾的話是錯了嗎?他講的普魯士是萬惡之源”不是成為歷史名言便被廣大世人所接受了嗎?現在可以申辯的問題是希特勒同普魯士是否就是一碼事?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傳統是否就是納粹罪惡的精神和文化?
普魯士和納粹國家總是存在著某種相通之處。但也決不會是百分之百,因為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在德國曆史上也曾起過很進步的作用,像反拿破崙統治的解放戰爭時期、俾斯麥統一德國時期,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都起了總動員的作用。只有把國家政治軍事同精神文化傳統共同進行考察,也許才有可能從實質上和總體上把握住普魯士。
1990年德國再度統一,“普魯士”這個話題,在德國人之間,甚至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又成為了爭論焦點。因此,對德國和世界人民來說,真實地認識和深入地瞭解普魯士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那麼真實意義下的普魯士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要想比較精確地把握普魯士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只有透過對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世人對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家從興起到衰亡的過程貶褒不一,這是完全正常的。封建的、專制的、官僚軍國主義的、衰朽的普魯士,當然會遭到大多數世界人民的反對和仇恨;而開明的、嚴謹理性主義的立憲主義的、生氣勃勃的普魯士,則會得到大多數世界人民的贊同和首肯。
對於我們而言,普魯士是和中國發生正式官方關係的第一個德意志邦。1861年普魯士遣使節團來華和清政府簽訂條約,那時中國人對普魯士還一無所知。中國知識分子最早親歷普魯士的是斌椿,他作為清政府派遣人員前往各國實地考察。他在《乘槎筆記》中詳細記述了對普魯士及其首府柏林的印象。
他曾寫道:
1866年7月,至布(即普魯士)國都名伯爾靈(柏林),樓宇高峻,街市整齊,週三十六里,人民二十餘萬。前日與奧士利亞(即奧地利)交戰,大勝。布國東南二千里,南北一千一百里。其地古為北狄所據。南宋時屬日耳曼,康熙三十九年,乃自立國。嘉慶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後六年,布(即普魯士)人不悅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師,遂復故土。地分東西兩土共八部。產鋼鐵絲布鐵器最精.工細若金銀造。瓷器優良,精緻不亞華產。西部主鋼鐵,造炮甲於泰西(西方國家)。
這是19世紀60年代中國人眼中的普魯士。雖然時值普奧戰爭,但斌椿卻未感到普魯士是在窮兵黷武,欺壓鄰邦,相反對普魯士的發憤圖強,莊敬自立的精神讚譽有加,對普魯土的工業文明和文化創造深表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