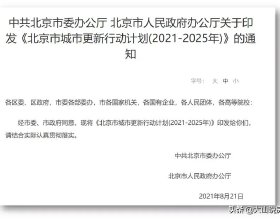從即刻起,鄒雅琦進入了一場行為實驗,目標是在北京不花錢生存21天。
那是5月1日零點,她身披黑貂外套,手提仿製名牌包,踩著一雙淺口黑皮鞋,全副武裝地走出中央美術學院大門。為了這個畢業作品,央美學生鄒雅琦精心準備,將自己打扮得像個“名媛”。
接下來的三週裡,她混進過頭等艙休息室,享用一日三次免費供應的自助餐;也藉口“等朋友”,獲得火鍋店的免費零食和水果;甚至預備好 “捉姦”的理由,混入酒店大堂過夜。當她裝扮成單身“富婆”逛拍賣會現場,保安殷勤地幫她遞水、拍照;在狂掃大半盤白巧克力後,服務生主動詢問她是否需要更多。
這些都被鄒雅琦拍攝下來,在她的畢業作品展上播放。這場遊走在灰色地帶,佔用“剩餘物資”的行為實驗也引起了爭議和更多的討論。
在作者看來,“一些人能利用他的物資,極少數人可以利用剩餘物資生活下去”,她就是“極少數人”。掌握免費資源的資訊,廉價且“美”的物品銷售渠道以及擁有體面的外表,也許是這場實驗達成目標的前提。這不免讓人思考,“極少數人”佔有更多的物資,一些更需要“物資”的人,卻是多方面的匱乏。
而在21天裡,鄒雅琦的身份從未被識破,則是實驗引發的另一個話題了。
【以下為鄒雅琦的口述】
2017年8月,當我收到中央美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感到憧憬,又有些畏懼。
很多人說,“美術學院畢業就是失業”,我怕自己像做了一場夢,之後沒能過上理想的生活。
我開始關注在北京的生存問題,我發現北京的房價、房租年輕人很難支付得起。如果畢業後,我從事和專業勉強相關的工作,月收入1萬元,租房可能花4500元,只能租到一個帶獨立衛生間的小房間,不算水電費和其他的生活成本。
所以我會往深層思考,能不能在北京不花錢生存?
2021年5月1日-5月21日,我在畢業創作中實踐了這個想法,在北京不花錢度過了21天,並且像“名媛”一樣優雅。我在社交媒體分享了創作過程,遇到爭議的聲音,我就給對方點贊,這說明對方有一些思考。也有人說我是“真名媛扮假名媛扮真名媛”,但其實不是的,我為什麼會看起來像名媛?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首先,在服飾妝容方面,我想打造一種有錢有閒的狀態。我的朋友贊助了我一件絲絨質地的運動服,是一個設計師品牌。另一個朋友贊助了一條假的名牌項鍊。我用媽媽贊助的啟動資金,購買了一個2700元的假名牌包,買的時候賣家就告訴我,櫃姐看不出來是假的。我還準備了一個10元錢的迷你夾板、髮油、洗髮水、一個蘭蔻的美妝盒及一些卸妝溼巾,蘭蔻的美妝盒是一個臨期產品,只花費了100元。
生活中,我沒有接觸過名媛。我關注了社交平臺上一些比較符合“名媛”刻板形象的博主,學習她們的穿衣打扮。比如我關注的一個“00”後小女孩,她經常妝容精緻,和其他姐妹在酒店喝下午茶或外出度假,影片裡分享自己的穿衣打扮,展示漂亮的鑽戒、名錶。我的妝容也是模仿博主,以黑白紅三色為主。我會把自己代入環境中,想象自己是個有錢有閒的名媛。
但在不同的場合我會扮成不同的人,如果我想混進頭等艙休息室、五星級酒店或者拍賣行,我就得扮成名媛,因為這些場所的剩餘物資較多,名媛這個身份更容易接觸到剩餘物資。而在海底撈、宜家家居和超市,我又會扮演其他身份。
我制定了21天的行程計劃,並踩點了近百個衣食住行場所,實際派上用場的可能只有20個地方。吃的方面,我踩點了一些購物商超,其中一些有很多試吃的東西。我也找了藝術展的開幕式,因為每次開幕式的點心非常好吃,通常開幕式當天也會有晚宴,我就會把這些剩餘物資收集起來。
住宿方面,我(踩點過)所有 24小時營業的地方。當時由於疫情,周邊24小時營業的書店和咖啡廳,基本關了,只剩下一家咖啡店還在營業。我晚上在那裡待過,趴在桌子上休息,那裡提供免費的水和糖。酒店、頭等艙休息室等地方也可以過夜,我傾向選擇距離近,“油水”多的酒店,比如在拍賣行、藝術展開幕期間,但畫廊周在4月中旬舉辦,5月份藝術展比較少。
21天生存實驗
5月1號的零點,我從中央美術學院出發,帶了兩個手機和一個迷你三腳架,其中一個手機別在腰帶上用於拍攝。假名牌包裡裝著美妝盒、七雙一次性襪子、20條一次性內褲,及部分洗漱產品。
我身上穿著絲絨運動服,披著黑貂外套,沒有帶換洗衣服——拿不了那麼多東西,而且有一些剩餘物資可以使用。我提前列好清單,不同服裝品牌的退貨期限及退貨條件,比如有的要求服飾不能被穿過;有的只要吊牌完整,服飾沒有被清洗過,就可以30天內退貨。
離開學校後的第一站,我去了學校附近的一家女僕酒吧,我從小就看動漫,喜歡這種日本文化。我向女僕酒吧的老闆解釋了我的整個計劃,他讓我在漫展上幫忙宣傳,允許我漫展期間晚上睡在酒吧裡,並幫我買了一張190元的機票,報銷了我往返機場的車費。
5月4日,我拿著提前列印好的假的兌換牌進去頭等艙休息室,最開始很緊張,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裡,在休息室裡待了三天,我很快適應了“名媛”的身份。休息室裡,自助餐每天開放三次,每一餐我都去拿了很多吃的東西。負責收拾餐具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說什麼,他們只是忙於自己的工作。
貴賓休息室樓下是GUCCI的店,我告訴櫃姐,“我的東西散落一地,能不能給我一個袋子。下次有時間的話,我會來消費。”櫃姐猶豫了一下,她可能覺得我突然找她要袋子很奇怪,但她還是給了我一個。這套話術是我臨場發揮的,可能是我太莽撞了,後來才知道,GUCCI的袋子在淘寶上賣20元/個,而我免費索要的過程不超過一分半鐘。
5月8日,離開機場後我回到望京。在海底撈,我沒有維繫名媛的身份感,而是假裝自己“在等朋友”。員工很同情我,他們抱著基本的善意,給我盛湯圓,端水果。看到我一個人坐在餐廳外面,還會讓我去沙發上休息一會兒。大家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但很有人情味。
朋友們對我的創作也很感興趣,他們也想來體驗一下。在宜家家居的時候,我選了一個床上有很多抱枕的樣板間躺下,朋友就睡在旁邊,我們儘量扁扁地睡在裡面,不被工作人員看出來。
在中央美院美術館的展覽上,我領取到了免費的烤饢,在學長制作的展品汽車裡過夜,在殘疾人無障礙衛生間洗頭髮。朋友們玩累了就去花錢吃飯,我坐在他們旁邊,他們吃他們的,我就繼續吃自己的零食。
5月11日,我決定從望京走到市中心(全程近20公里)。我實在太累了,就下載了一個交友軟體,希望搭車到酒店,再在酒店大堂甩掉對方。但配對上的五六個人可能覺得這麼漂亮的女孩不會這麼快答應去酒店,像是仙人跳,計劃就落空了,我就去貴州大廈的大堂睡了一晚。
到達市中心後,我去了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拍賣會現場。印象最深的是,遇到了一個很殷勤的保安小哥。他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給我送茶、送咖啡和水,主動幫我拍照。我沒有給他任何暗示,只是看起來像一個獨自前往的單身富婆。他當時很想加我微信,我不想讓他失望,也有點期待他接下來跟我說什麼。微信上,他對我噓寒問暖,“姐姐買了哪件藏品?姐姐今天在幹嘛?姐姐工作累不累?“我沒有回覆他,覺得有些內疚。
在另一個藝術品拍賣會夜場,我從朋友那裡拿到了邀請函。現場有白巧克力、鵝肝點心等。我吃掉了大半盤白巧克力,因為實在太餓了,工作人員問我,“好不好吃”,我說,“好吃好吃”,工作人員就讓我好吃多吃一些,不夠的話,他叫後廚再送一些。
這21天裡,我休息不好,是一個很疲憊的狀態。本來想蹭車去不同的地方,但大家都不太信任,只蹭到了一次車。20日晚上,我在酒店的拍賣夜場遇到一個比較好說話的藏家,我跟他說,“手機沒電了”,對方幫我送到了望京附近的一家酒店。在車上,我還蠻緊張的,寒暄了幾句當晚拍賣會的情況。
晚上,我在不同的五星級酒店過夜。我設想過,如果被盤問到為什麼一直待在大堂,我就用“捉姦”的理由和工作人員解釋。但沒有人來詢問,唯一一次被問到,是我坐在酒店大堂的消費區等拍賣會開始,我說自己剛退房,正在研究拍賣會的圖冊,等朋友來,就沒有再被打擾。
在酒店裡面洗澡,我之前籤的名都是《三國演義》裡的人物,直到第三次我簽了“811 遠坂凜”,一個我最喜歡的動漫名字,酒店服務員覺得異常,核實後發現沒有這個人。服務員有些慌張,我和她解釋,“我沒有續費,但我想在約會前補個妝”。可能我也沒有給她帶來麻煩,她就給我了一個手牌。
21天裡,最美好的體驗是我收留了一隻小貓。我路過的一家畫材店,門口有兩隻貓,我以為它們是野貓,就拿出一些從酒店拿來的食物給它們吃。畫材店的老闆娘告訴我,“如果你很喜歡貓,它們兩個下了一窩崽,你可以帶走一隻”。
我家裡原本有一隻貓,現在它們兩個關係很好,每天都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不是名媛”
現實生活中,我不是“名媛”。
我出生在湖南的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沒有買過愛馬仕、GUCCI等奢侈品牌。但是我非常會買東西,我可能花十塊錢買到華倫天奴襯衫——像在國際學校以及別墅區附近有開慈善商店,一些人把他們的東西捐到這個地方,義賣出去。
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買貨渠道。比如說我想買一件滿意的外套,別人可能只用淘寶,我可能會用阿里巴巴批發網、閒魚、拼多多、淘寶、京東,甚至去國外的拍賣網站、雅虎拍賣等渠道。我們學習藝術,會更喜歡美麗的東西,我和朋友們又相對貧窮,就會盡量低成本買到很好的東西。
我的父母和大多數父母一樣,幾個月前,還在催我考教師資格證,回家鄉做一名中學老師。他們每年都會跟我提這個事,我都說,“好的“,但應該不會去考,或者是考一個證應付他們。他們比較少肯定我的作品,直到前段時間,父母來北京參加了我的畢業展和畢業典禮。媽媽看了關於我作品細節的報道,才慢慢理解,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作品。
生活裡,我很少嘗試角色扮演,可能因為身邊的人都太熟悉我了。但高中的時候,我捉弄過我的同桌。同桌是一個比較自閉的女孩,不願意和我說話,我就和她說,我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告訴她我和雙胞胎妹妹有哪些不同。有一天,我化裝成雙胞胎妹妹,出現在教室門口,她很驚訝了,第一次開口和我說話,“哇!你是妹妹,對吧?”後來她知道被我耍了,就不和我玩了。
高二的時候,我在北京上美術考前班,那裡只許老師坐電梯,不讓學生坐電梯,打飯時給老師大雞腿,給學生小雞腿。我就假裝自己是代課老師,這樣就能坐電梯,能自由出入封閉式管理的校園,菜也給我打的多一點。因為很多大學生會來考前班教課,當時我和大學生只差一兩歲,打扮的也蠻漂亮的,沒有被識破過。
在大興機場拿著提前列印好的頭等艙休息室兌換牌子,我還是比較緊張,後來越來越放鬆。甚至覺得越來越不像自己,我緩了很久才緩過來。比如我去一家咖啡廳,我就會想這裡有免費的開水,免費的冰塊,免費的砂糖和黃糖,還有免費的紙巾,我看看營業時間到12點,那太好了,有點像職業病。
平常,我蠻恐懼社交的,對多數人都是一種比較封閉的狀態。第一次認識對方的話,我可能會假裝熱情,寒暄兩句之後,就擔驚受怕地躲開。但為了這次畢業創作,我需要豁得出去。
一天早上,我混進酒店的餐廳吃早餐,對面是一桌北京大爺,我特意明目張膽地連吃帶拿。當時有一點小小的壞,覺得北京大爺的反應會很有趣,一個光鮮亮麗的少女,居然“偷”東西。
如果被拘留的話,我會乖乖服法。我沒有和導師討論過可能被拘留的情況,但我覺得他們能理解有一個激烈的衝突,能給我的作品帶來更深的一個思考。我規避得很好,只有那麼一點點小衝突,都是很順利的,我覺得這也是真實的,只有在電影裡面才會出現激烈的衝突。
剩餘物資、瞬間與永恆
畢業展上,我準備了一個可以坐下12個人的沙發,這樣觀展的人累了,就可以在沙發上休息。我還想過偷偷準備一些酒,因為我在外面靠免費的酒,也生活了好幾天。我甚至想過有需要的人可以在我的展臺下面睡覺,但出於安全考慮,只保留了沙發的想法。
我想要把自己的沙發、酒、展位分享給大家,回饋這21天我使用的社會資源。當然,也有一點小私心,希望大家能坐下來多看看我的作品。
我還設計了一個“使命必達”環節,在展位上留了很多便利貼,希望大家留下心願,我去幫助大家實現。這個環節是來自導師的建議,老師覺得我拿了21天的社會資源,得還回去。這出於對一個作品完整度的考量,也昇華了作品的主題。
“使命必達”的環節,我把收集到的紙片分為三類。一類是我可以幫助對方做到的,比如說有人想領養狗狗,我就把一個收養流浪動物的組織推薦給他,有人想看我穿著睡衣去星巴克,這個也很好完成,我就去做了。另一類是需要我在紙條上面回答問題,比如有個小朋友畫了一個迷宮,希望我能走出這個迷宮,但我走了一半,沒有走出來,我就在底下寫,”不好意思,沒有走出你的迷宮”。還有一類是我沒辦法做到的,比如有人許願,“我也想考上中央美術學院“,”我希望我能考研成功“,”希望我和誰誰誰天長地久“,我就沒辦法幫他實現,所以我只是把它們收集起來。
畢業展剛開幕的時候,我遇到一位奶奶,她翻看我的畢業創作宣傳冊,上面醒目地寫著“白嫖名媛在北京21天的收穫“的標題,她建議我將“白嫖”的“嫖”改成“漂流”的“漂”,我覺得這個想法很棒。
也有觀展的觀眾提出,如果我是位男性或者是位不漂亮的女孩子,這21天是做不到的。但我覺得如果是中年男性,也一定有別的辦法去偽裝。
我給這個作品起名叫“瞬間所有制”,想討論的是瞬間和永恆的關係。比如20號晚上,我獨佔了近一畝地的一家五星級酒店大堂,酒店裡陳列著幾千元一束的鮮花,就像我瞬間擁有過一樣。
我在這21天裡利用的剩餘物資,不能說它是漏洞,或是浪費,它是一個灰色地帶,一箇中間餘地。一些人能利用他的物資,極少數人可以利用剩餘物資生活下去,在這21天裡,我就是那個極少數人。
但我沒有說過“假名媛實驗”,可能一些營銷號側重宣揚我是“假名媛”的身份,這是一個吸引眼球的爆點。 “名媛”只是我扮演的比較重要的一種身份,更容易和別人建立信任,獲得剩餘物資,但在不同的場合,我會扮演不同的身份。
如果說這個創作還有遺憾,可能是21天時間限制,我做的還不夠徹底,因為要考慮後期布展、剪輯影片。如果重來一次,我肯定希望扮得像一個真正的名媛,碰到更加意想不到的資源,我覺得會更加精彩。
現在,我被一家藝術機構簽約了,終於敢說出自己想做一個藝術家的理想。最近有很多媒體來採訪我,也給我帶來了一定的成就感,我已經進入下一階段的創作,目前,我在拍攝一個影像,表達有關東方主義的話題,新的作品會在10月28號在日本東京銀座展出。我在社交平臺開了一些賬號,想把這21天完整的經歷發在網路上,也會更新我接下來的作品,因為網路是大眾接觸藝術的一個途徑,我希望能做一個藝術傳播者。(記者:劉昱秀)
來源: 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