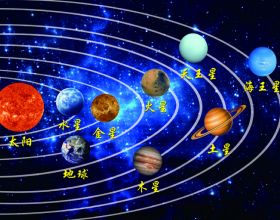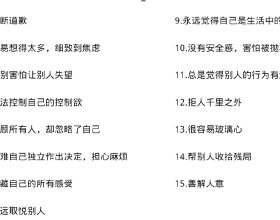本文章下篇七千多字經查漏補缺,悉心改版,再與讀者朋友們見面。初次創作類似於小說的這種萬言長文,文章的上篇已經發布多日,網頁上可能難覓蹤影。倘若讀者朋友有意有始有終地閱讀這一篇連貫完整的全文,請點選右上角關注本文作者。故事沉重淒涼,擔心會引起輕微的心理不適,但絕不會失了分寸在文中充斥著低階趣味甚至汙濁的內容,相信不負眾讀者,朋友們讀與否,請自便吧!
本文上篇截圖
那一年的深冬,南方斷斷續續下了三場雪,臨到春運前夕的那場雪,從下午無聲開幕,在天地之間紛紛揚揚,不屈不撓地飄灑到下半夜才悄然收場。
長江以南紛飛的雪花,經不住依然溫潤的大地燻蒸。從地上仰望,密密麻麻飛舞的白色花瓣,數不勝數,漫天飛雪竟然氣勢磅礴。一旦飛入高山曠野,頃刻之間蕩然無存。
雪後初霽,陽光明媚,卻比大雪天更加寒氣襲人。只要交通順暢,南來北往的遊子,好比那些翩躚在天空的候鳥,季節來臨,對家鄉朝思暮想,不怕歸途風雪嚴寒,不畏山高水長,千里迢迢歸心似箭。
外鄉人陳甲就是在一個化雪的奇寒天氣裡回家的。彷彿老天憐憫他,看上去打算連綿幾天的風雪,待到他啟程還鄉的那一天,黎明時分突然停了。
南方大雪
他在世上僅活了三十來年,初次登機回家鄉,也是人生最後一次乘飛機。
他蜷縮在一個不到一尺見方促狹的紫檀木匣內,飛機客艙裡沒有他的座位,他一聲不響地待在機腹行李託運貨艙一個角落裡,七尺高的血肉之軀,如今化作一抔灰白色齏粉……
他來時秋風乍起,將要回去時大雪紛飛,他的腳跡從初印南方這片異鄉土地上算起,直到離開那一刻,滿打滿算還未到四個月。
老鄉帶著他只有幾百克的骨灰回家,心裡卻如壓著一座磨盤,墜沉得他將要窒息。原本出自一片好心推薦他一分工作,現在腸子都悔青了。倘若時光可以倒流,他將不假思索一口回絕陳甲當初的請求。
他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陳甲那白髮人送黑髮人,肝腸寸斷的爹孃,也不知道該怎樣解釋陳甲在異鄉幾個月的遭遇。
究竟有多深的仇恨才會引來殺身之禍,才會讓三十來歲,終生未娶的陳甲付出這般沉重的代價。
年紀輕輕,淳樸善良的外鄉人陳甲究竟是如何客死他鄉的?說來話長……
初冬傍晚,車間工人陳甲等來接夜班的同事,步出機器轟鳴的工作間時,烏雲低垂的天幕上不見星辰,也沒有月亮,黑得如鍋底似的。冬天的白晝原本就很短,何況這眼看就要下雪的天氣。他在一陣緊一陣的寒風中縮著脖子小跑著回宿舍,要不是上下班的同事們迎面而來或擦身而過,他恍惚覺自己穿行在夜闌人靜的三更時分似的。
他在宿舍大樓門口的路燈下接到“嫂子”的電話,她的聲音依舊清亮甜美,特別是手機裡傳出來的音質,經過特殊處理過似的,足以讓陳甲靈魂出竅。
民工宿舍
周乙在寒冷的冬夜求助於剛下班的陳甲,從電話中傳出來的聲音不勝焦灼:出租房衛生間的水龍頭壞了,早晨就關不住水,滴滴答答漏過不停。下午回來,連地漏也堵了,水漫出來,把臥室地板都浸溼了。房東住在城裡,路又遠,天寒地凍的根本就不想過來解決問題,一句報銷材料和維修費用就打發了她,讓她自行想辦法,她一個弱女子有什麼辦法可想?又指望不上遠在兩百公里之外的丈夫,她一個人又冷又怕……話還沒說完,手機中傳來了小女人委屈的哭泣聲。
區區一樁小事將一個單身女人為難成度日維艱的一道天大的難題。
陳甲聽見“嫂子”周乙嚶嚶的哭聲,心都快碎了,連忙安慰她不要害怕不要著急自己馬上就趕過來。
掛了電話,陣甲連宿舍樓也不上了,一陣風似的卷出廠門,橘黃色的路燈下,他迎著冰冷刺骨的夜風飛奔在公路邊的人行道上。滿頭蓬亂起伏的黑髮在風聲中東倒西歪,瞧他賽跑般拼命的衝刺,既像倉皇逃命又像是十萬火急奔赴去救命……
地處低緯度和中緯度分野過渡的北溫帶南方臨海地區,一年之中最後兩個季節交替往往都不會遵守循序漸進的規律,一冷一熱,一驚一乍。待到一夜寒潮長驅直入,虛虛實實交鋒一二十天終見分曉,冬季冒進成功正式主宰這一片偏北寒冷的南方。
嚴冬降臨了,燦亮天光輝照大地的時間“縮水”不下於三成,下午還不到五點鐘,夜色漫上來,轉眼之間天昏地暗。天氣陰冷,濃夜漫長,夏天晚上人聲鼎沸的夜市銷聲匿跡,最遲不過冬夜九點鐘,超市打烊、店門落鎖,關門閉戶一個村落,寂靜無聲。只可聞村中偶爾傳來幾聲犬吠,佇立在沒有熱氣的路燈下東張西望,只看見幾扇視窗還透出黯淡的燈光……
單身漢大齡青工為解“嫂子”出困境,一口氣奔跑了近三公里,他氣喘吁吁停在村口的五金店門口時,店家的捲簾門早都拉下來了。他把耳朵貼在鋁合金面板上,店裡鴉雀無聲,難道里面連一個守店的人都沒有嗎?
這可怎麼辦?“嫂子”的難題怎麼解決?
七尺漢子在打烊緊閉的店門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寒氣襲人的冬夜,愁得連額頭上的汗水都滲出來了。
他在團團轉一籌莫展之際,突然瞧見對面理髮店還亮著的廣告燈箱上印著一串電話號碼。陣甲一下子茅塞頓開,猛拍一記腦袋暗罵自己太焦急,腦瓜子都急糊塗了。
開了竅的陳甲連忙退後幾步,退到了街心。在這個位置上,高懸於五金店大門上方招牌上的幾行金黃色大字在路燈下看得一清二楚。
五金商店
打通了五金店的電話,裡面有了動靜,門縫裡透出了燈光,緊接著捲簾門啟開了一道縫隙,縫隙不斷加寬,漸漸升高……
陳甲賠著諂媚討好的笑容,專門揀著好聽話說,滿臉不悅的店老闆披著大棉襖,打著哈欠,揉著睡眼,不耐煩的伸手擋開了顧客遞過來的香菸。粗聲粗氣埋怨顧客為什麼不早點兒來,口氣如審訊似的喝問陳甲這麼晚,這麼冷的天氣到底要買什麼。
當陳甲跨出五金店,鋁合金捲簾門在他身後又徐徐降下時,手裡多了一隻塑膠袋,裡面除了一個鋥亮嶄新的水龍頭、一卷密封生料帶、還有扳手、管鉗等工具。
工具是租借的,老闆只做銷售從來沒有開展出租工具的業務一說,但他拗不過執著的顧客。
陳甲為了討好和取信店老闆,壓了五百元現金不說,還擔心店老闆信不過他,連身份證都掏出來押上了。做了半輩子生意的店老闆從來沒見過這樣子的馬屁精,低三下四的“上帝”。心腸一軟,就破例答應了,壓金留下了,但他沒扣留陳甲的身份證。
陳甲的影子踽踽獨行穿過夜色中一條長長的弄堂,他遠遠看見周乙居住的小院落二樓視窗還透射出燈光,這光線在暗夜裡分外明亮耀眼,如大海上指路的燈塔一樣。不知道什麼觸動了心絃,他眼裡一下子又潮又熱,無人看見他在黑暗中那一刻,雙眼淚花閃閃,波光瀲灩。
三十掛零的少婦,集團公司白領麗人周乙居住在一座徽派風格的兩層小樓裡,這小樓四周築有圍牆,院牆後邊聳立著高高的大山,植被茂密的青山四季常綠;院牆前綠樹成蔭一片果樹,果園中間還掘了一口幾丈寬的池塘。
“徽派”建築風格的民房
並不清靜的小院子依山傍水,孤懸在村西口,夜裡山風一陣接一陣呼嘯而過,這陰森森的院子颯颯作響,活像一座鬼魅出沒的廟子。
這座兩層小樓的院子本來有三對外地夫妻租住的,只因另外兩口子嫌房租昂貴且離單位較遠,吵吵鬧鬧相繼搬走了。
周乙夫妻堅持不搬家,是因為他們是公司雙職工,且都是中上階層的管理者,房補較高,對於他們來說,只不過掏一個零頭,打著燈籠也找不出的划算。以前三戶人家住在一起,當然鬧熱。但隨著另外兩家搬離,丈夫顧丙又被調往外地履新任職,往日覺得並不寬敞的院子顯得格外空曠,她一個人住在樓上,樓下漆黑一團。深夜後山上傳來幾聲夜鳥的怪叫聲,把她驚嚇得抖過不停。
她心驚膽戰獨自住一棟小樓,緊張恐怖地熬著長夜還是沒有搬遷,是因為丈夫對她說很快就要把她調過去了,堅持也是暫時的,何必費力氣折騰搬家。
身邊沒男人陪伴的年輕女人連生活中許多小難題都無法化解:譬如牆上的插座沒電了、天花板上的電燈不亮了、洗衣機轉得不正常了、煤氣灶的卡扣鬆了……就如這天衛生間的水龍頭突然關不住水了,諸如此類都讓一個出門要梳妝打扮,長相漂亮,在工作上稱職的年輕女人束手無策。
南方山區
丈夫顧丙也深慮一個女人過日子的艱難,才在離家的前晚將這些對於一個男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託付給既是自己拜把子兄弟也是妻子救命恩人的陳甲。
顧丙不失於職場上的中堅骨幹,年富力強,頭腦清醒。冒死救妻子的同齡人陳甲從見面之初博得他的好感。因為信得過陳甲才放心將嬌妻託付給他幫忙照應,無可奈何事業和家庭不能兩全其美,這種內心忐忑的託付沒有從人性和理智去過細斟酌。
他也是對陳甲過於信任了,若不然又怎麼辦呢?他難道沒想過年齡相仿,樣貌般配的一對孤男寡女在一起時間待久了,神仙也不能夠保證不出意外。
陳甲在圍牆外的池塘邊撥打了周乙的電話,提前打招呼是好讓她下樓來開啟院門。沒料剛一接通就聽見了對方的手機來電鈴聲。原來那無助的女人,守在院牆大門黑漆漆的門洞裡,凍得瑟瑟發抖等候他多時了,聽見手機響起,再抬頭看見池塘邊一條熟悉的影子匆匆走來,彷彿來者是又一次救了自己的性命,成串的眼淚止不住滴下來。
南方夏夜
小鳥依人的女人亦步亦趨陪著與她有救命之恩的男人,打著手機電筒照路,撥開茅草叢,先到房後將小樓的總水閥關緊,再上樓去。
從在圍牆外迎接到眼前的這個男人,周乙一雙不盡感激的眼睛始終聚焦於忙碌的男人身上,見他敏捷又熟練地使用工具固定住水管,輕鬆取下滴漏損壞的龍頭,再將新龍頭一圈一圈纏上薄如蟬翼的密封帶,擰緊,再估量一下女人的身高,揣測她的習慣,細心地調整到女主人用水最方便的角度,再雙雙下樓,開啟總水閥……
給孤獨度日的女人造成深重困擾的難題在男子漢絲毫不顯費勁的操作下,不到十分鐘迎刃而解。
陣甲再耐心地將衛生間,臥室的水漬拖乾淨,事情做到這般徹底完美一步,完全稱得上服務周到地完成了任務。如果他就此告別女主人,退出房間,踏著夜色回去,興許就會避免後面發生的事了,興許他也會等來顧丙對他承諾的兌現……
周乙送陳甲下樓,到了院子裡,呼嘯的寒風一陣緊一陣,兩個人看見黑沉沉的夜空不知何時飄起了雪花。周乙呆望著雪夜中衣衫單薄,凍得微微發抖的陳甲,眼裡又湧起了淚水,她這才過意不去地意識到,眼前這個人在車間累了一天,剛下班就過來幫忙,可能連晚飯都沒來得及吃,是不是餓壞了。
在他鄉孤苦伶仃的忠厚男人其實也是臉皮薄,肚子裡早都唱起了“空城計”,受到女人邀請,飢寒交迫的他又隨她上了樓。
像一對夫唱婦隨過日子的親密小兩口一樣,女的洗菜,男的切肉,不消片刻,小餐廳的飯桌就熱氣騰騰擺上了葷素搭配的四五個菜。夜來天寒,周乙還拿出來一瓶高度燒酒,自己象徵性地倒了淺淺半杯,卻給眼前這個幫了自己一個大忙的男人斟滿一大杯,她這麼眼高手低一倒,一斤裝的酒瓶一下子空了一大半。
天寒地凍的雪夜,年過而立的單身漢身處溫暖的房間裡,面對一桌美酒佳餚,身邊還陪著一個讓自己朝思暮想而又從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女人。
老天真是造化弄人,這個溫柔美麗的有夫之婦和自己年紀相差不多,還比自己小點兒,怎麼沒有在她未嫁人時和她相遇?那一個大霧天的清晨,她命懸一線,是自己奮勇救下了她。她是自己結拜兄長的妻子,他稱呼她嫂嫂,流落異鄉悽苦無依,他將她視作自己的親人……
四角的餐桌不過一張課桌大小,桌子對面的她離自己不過兩尺遠,他又嗅到了她長髮散發出來的芬芳香味……陪自己飲了幾口烈酒的女人呵氣如蘭,一張俏生生的粉臉似一朵嬌豔盛開的桃花,在寒夜的燈光下越發楚楚動人,簡直讓自己不敢直視。
神情恍惚,醉眼朦朧的陳甲彷彿中了邪,他起身,繞到對面去,深深吸一口氣,稍一猶豫,猛地把周乙抱在懷裡,猝不及防的突然動作,與那一天在公路中間救人性命,何其相似……
周乙驀然一驚,臉紅到脖頸根,她劇烈扭動著身子想掙脫這魯莽的摟抱。但她在一瞬間看見了男人的一雙大眼裡噙滿淚水,這雙男人的淚眼裡盛滿了苦苦的相思,流露出對自己近乎殘酷地壓抑,這雙男人的眼睛,更像是被拋棄到驕陽似火的岸上,瀕臨曬乾的一條魚,對雨露渴望的魚眼……
周乙心裡一震,從未有過的心酸憐憫掠過腦海。就算是一種報答救命之恩獻出的犧牲,難道也要吝嗇和拒絕嗎?她百感交集,終於不再矛盾,她放鬆下來,停止了掙扎,扭身過來迎合地摟住了這個眼看就要焚燬了的男人……
這樣的事情見不得天日,連對燈光都感到畏懼。孤院兩層二樓上的燈光從上半夜熄滅那一刻到下半夜兩三點鐘陳甲冒著風雪離開時,都不敢再復明亮。
這樣的事情山重水複一旦開了頭,有了初一,十五也就順理成章。靜默了幾天的一條簡訊,三言兩語對暗號一樣匆匆結束通話的一次電話,一男一女心神領會。
世上再隱秘的事情也會露出破綻,天衣無縫本來就是一條悖論,終歸有東窗事發的一天。
村裡有一家棋牌室,白天正正經經做生意,到了晚上有些事先約好的人聚集在這裡。這些賭徒雙眼通紅,精力充沛,不怕冷也不怕餓,廢寢忘食管他外邊冰凍三尺熬幾個通宵不在話下。
其中有一個經常請假耍錢的小年輕,是周乙公司的一名員工,曾是顧丙的下屬。他不僅熟悉周乙,也見過救人的陳甲,但陳甲不認識這個人。他在村裡賭博,下半夜回來,好幾次撞見從村裡鬼祟出來,腳步匆忙的陳甲了。起初沒在意,碰見的次數多了,心裡就升起了疑雲。
不知道賭徒出自什麼動機,他把電話打給了在兩百公里外的前上司。顧丙這一驚吃得非同小可,但他懷疑是這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滿嘴跑火車死也不相信豁出命來救人的拜把子兄弟是如此不堪的人。
但這樣寬慰自己不能獲得解脫,為了一個水落石出的真相,為了自己不受耿耿於懷的痛苦困擾。顧丙和小賭徒加成微信好友,他轉過去一千元“經費”和“封口費”,託付曾經的下屬“偵破”此案。他要面子,自己的老婆若與結拜兄弟清白無暇,這個捕風捉影的謠言當然不攻自破,以後決不許再提。儘快將妻子調到身邊來,是防範於未然的最佳措施。如果真正有染,事情壞了這一步,那一定要讓這對行了苟且之事的男女付出相應的代價。
時令“二九”過了幾天的一個上半夜,顧丙又接到了一個告密電話。賭徒在電話裡壓低了聲音告訴他,今晚連夜回來,定然可以“拿雙”。
顧丙因心事重重而心神恍惚,工作上接連失誤,下午被老闆剋了一頓,全公司點名批評的通告都貼在了公告欄上。他的心情本來就敗壞到了極點,在床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眠。火上澆油接到這樣更糟心的電話,氣憤的臉都扭曲變形了。
他打電話給三個最貼心聽話的手下,讓他們穿好衣服,各人備一條鋼管,在地下車庫等他。
一輛黑色轎車,雪亮的光柱,穿破嚴冬濃黑如墨的夜幕,箭一般飛馳在高速公路上。
殺氣騰騰的顧丙鐵青著一張臉在駕駛座上,咬牙切齒講清楚了要三個手下連夜出行的的來龍去脈。後備箱裡,三條一米多長的鐵器隨著汽車顛簸,不時發出清脆的撞擊聲。而顧丙身上穿的一件大衣裡,暗藏著一把12吋的碳鋼縫紉剪刀。
碳鋼是生產炮彈殼的優質材料,用這種金屬製成的剪刀,雖然不能誇張成削鐵如泥,但用來剪2.5平方的普通銅芯電線,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可見有多麼鋒利。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作品,作家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對“拿雙”這種事情,小說開篇這樣一段描寫:
“…… 陶陶說,句句是真呀,只一歇的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這對露水鴛鴦下來,老公捉緊了賣魚女人,徒弟押了賣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樓梯,女人不肯跨出後門。老公講,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會去呀。賣魚女人朝後縮,賣蛋男人犟頭頸,等男女拖出門口,居民哇哇一叫,倒退三步,為啥,兩個人,一絲不掛,房子裡暗,女人拖出後門,渾身雪雪白,照得人眼張不開,女人一直縮,拖起來,蹲下去。老公講,快走,搞腐化,不要面孔的東西,去交代清爽,快。老公強力一拖,女人朝前走兩步,上下兩手捂緊,蹲了不動。賣蛋男人拖出後門口,跌了一跤,周圍老阿姨小舅媽,然後朝後一退,吃吃吃窮笑,小徒弟講,娘皮,走不動了是吧,起來。居委會老阿姨,馬上脫了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蓋,高聲講,大家不許動,回去冷靜解決問題,快回去,聽到了吧。此刻,老公迴轉頭來,忽然推開徒弟,朝賣蛋男人撲過去,兩手一把捏緊男人臍下這件……”
小說裡上海吳語方言的敘述,讀來句句驚心,但畢竟沒有鬧出人命。
顧丙在村邊停車場將汽車熄了火,帶著三個心腹悄悄潛進村裡,不聲不響翻牆入院,幽靈一樣上了二樓。四條黑影屏住呼吸停在門口,顧丙在雪花飛舞的黑暗中運足力氣,嘭的一聲就把紅油漆的木質房門撞塌了。伸手不見五指的臥室裡傳來一男一女的驚呼聲,緊接著三個房間燈光如晝。
四條人影撲過去,一把掀掉兩條覆蓋在一男一女身上的兩條羽絨被。窗外寒風刺骨,而這兩個在床上的男女,由於蓋得厚,絞得緊,不知道是熱還是恐怖,暴露在燈光下的兩具一明一暗的赤身人體,通身上下汗水淋漓,連雙人枕都浸溼了。
四條立著的影子一言不發,顧丙遞過去一個眼色,三條掀起風聲的鋼管同時朝床上的男人招呼過去,其中兩條在空中發生了碰撞,迸射出一串火花來。
結結實實捱了三棍重擊,身上當場就滲出血來。這男人嘶吼一聲,一躍而起想負隅頑抗。
那女人出奇的行為讓丈夫氣得要發瘋,她顧不得遮羞,也跟著站了起來,將線條柔美,雪花一樣白的身子緊貼在身邊捱打的男人身上,用自己的身體掩護著剛剛還肌膚之親過的男人免遭三條鋼管的又一輪襲擊。
妻子出格的舉動徹底引發了夜半更深顧丙心裡的火山爆發,玉石俱焚的惡念不可壓制就衝上來了。他像一頭負傷暴怒到極點的獅子,悽慘地暴喝一聲撲過去,左手撥開妻子,右手一把尺多長的烏黑剪刀噗嗤一聲就刺進了她身後男人的腹腔。大腦一片空白中,他聽見了如裂帛般的聲音,覺得還餘怒未消。又將合口的剪刀尖叉到最大角度,旋轉半圈再轉下去,直到受阻的刀鋒轉不動了,再使盡力氣剪下去,他清楚聽見男人肚子中傳來什麼柔軟的條狀東西輕脆斷開的聲音……
12吋碳鋼縫紉剪刀
歪在一邊的妻子見狀哭喊著披頭散髮撲過來,不顧一切要奪刀,怒不可遏的丈夫抽出剪刀,又朝女人當胸捅去……
顧丙的三個手下傻了眼,劇烈地抖動著身子話都說不出來。顧丙丟下長長的碳鋼縫紉剪子,彎腰扯過凌亂的床單擦乾雙手,面無表情掏出手機,開啟臥室後門,來到陽臺上,點上一支菸,三口就吸完,再接上另一支……他在煙霧繚繞的陽臺上,漫天風雪的深夜中打通了給警方的電話。
當警車和救護車閃著燈鳴著笛衝進這座夜色籠罩的院子。倒在血泊中的陳甲已經沒有了氣息,周乙尚有輕微的呼吸,在送醫院搶救的路上,也斷了最後一口氣……
老友在馬路對面的蒼蠅館子講完了這個長長故事,禁不住地唉聲嘆氣。站起身來,執意要離開,天色已晚,外面依舊酷熱難當,我勸不住他,又不敢讓他酒後駕車,招來了一輛計程車讓他去市裡下榻的酒店休息,第二天酒醒後再過來取車。
南方的夏天
這個借出差機會遠道來看我的老友,和顧丙是十多年的老同事了。當然我不認識顧丙,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和他見上一面了,包括另外的二位主人公,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這三個人了。
2021/10
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