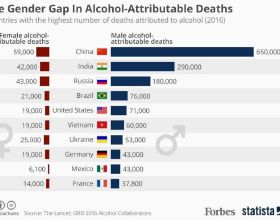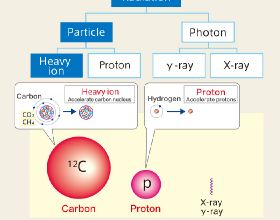“瞎子大爺”啥時住進我們家小正房,我也很朦朧,反正不是“斷腿”前。如果是那樣,敢肯定,我不會早早起來,更不會一個人,孤零零地立在大門外,去等什麼“送糞”的父親的牛車回來!像平常一樣,我會無論早晚,溜進“瞎子大爺”的小正房,不管他是躺在炕上,還是坐在炕上,吸著旱菸鍋,我都會立在鍋臺與炕楞的角角。那時,我比爐臺高一點,和炕楞一般齊。所以,那個鍋臺與炕楞角角,就像是為我量身打造的一樣,每次立在那裡,總覺著很舒服,又安全!尤其是冬天,緊緊貼在裡邊,還暖呼呼的。如果是晌午,聞著小鐵鍋裡的菜香,那簡直就是享受,比吃到還香。
“瞎子大爺”知道我立在那裡,好長時間,他不和我說話,只是有需要時,才叫我把笤帚拿給他,或是拿塊碳放進爐子。每到這時,我跑得最歡,生怕“瞎子大爺”會讓別的娃娃去幹。其實,除了我,沒有孩子願意來“瞎子大爺”家。
“瞎子大爺”很少點燈,除非他要抽旱菸鍋了。每次,他能精準地對準燈火,銅煙鍋頭裡的旱菸絲一閃一閃,有時都快將燈火吸滅了。但是,燈火就是不滅,油燈更是沒被戳倒過一回。每次,煙癮過足後,“瞎子大爺”就將油燈吹滅。屋子裡黑黢黢的,“瞎子大爺”自然是躺倒,勻稱地吸著氣,似乎睡著了。只有我和那隻貓不睡,而且,那隻貓的眼睛大不說,還閃著發黃的靈光。我對那隻閃黃光的黑貓特別恨!有一次,“瞎子大爺”好像又睡著了,我就揚著手,嚇唬那隻渾身亮黑的貓,實際是想和它玩一下。開始,它並不在意,只是把前爪的一隻,胡亂地一晃,象是應付差使。我也就膽子大到更進一步,把嚇唬的手下降地又快又低。貓好像不耐煩了,紅嘴一哈,白牙露得一齒不剩,我更得意,手直接就在它的頭頂亂舞。猛然,黑貓的爪子向前一抓,當我感到疼的時候,中指頭已是血流汩汨了。那次之後,我才知道,貓真正厲害的,是爪子,而不是嘴。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動貓了。事實是,以後,只要是我進門,貓就裝的睡著了!
“瞎子大爺”家的門,永遠不鎖。我有時實在無處可玩,無處可去的時候,“瞎子大爺”家就成為我唯一的歸宿。尤其是,那些個颳風下雨,黃昏落日的時節。我那時只有7、8歲,就知道“黃昏落日”是什麼時候。
“瞎子大爺”的雙眼,是那種像是“尺八老紙”糊住的一般,沒有睫毛,沒有眼廓,更沒有縫隙。但是,從來沒見過他有所不能,除了下地幹活。
每天一早,“瞎子大爺”的洗臉很認真,先是試試水溫,然後,撩水往臉上,脖子上。因為不用擔心眼睛進水,他用肥皂的手特有勁,使力地上下搓,直到臉面、耳角、光頭、脖子都泛泡為止。然後,才把頭伸進鐵盆裡,稀里嘩啦一頓猛衝猛潑,連測出的水聲都振振有節。然後,再用毛巾擦拭,尤其是兩眼處,擦得特別仔細。我覺著,他好像在擦眼淚。
“瞎子大爺”的做事,就像洗臉一樣,麻利不說,還精準。掃炕、疊被、生火,穿衣,從來沒見他麻胡過。不過,我最驚訝他殺雞時的利灑、精準和嫻熟。先開一鍋水在爐子上,殺羊刀(就是肚子突出像匕首那種)磨幾下洗乾淨放在一旁。接著,他抓住雞翅膀向外翻,合為一處,用一隻腳踩住,同時,另一隻腳踩在兩隻雞腿上。騰出的兩隻手,一隻手揣摸雞頭,順勢把頭和脖項折向一處一握,讓雞冠繃成扭扣向外凸顯。另一隻手在雞冠上揣摩,等找到一條隱藏的溝縫後,他捉刀順縫,橫著一拉,(有時是蹲在旁邊的我,遞刀過去)。瞬間,雞頭頂部,兩股血注直噴。過了一會,血不噴,開始放慢流了。“瞎子大爺”又從容地,從雞翅膀上拽一根粗翎,用翎根朝流血的管子,使勁地通一通。然後,把雞提起,頭朝下,雞又奮幾下翅膀,頭不停地亂擺。直到再沒有一滴血滴出,“瞎子大爺”才放手撂雞在地上。每到這時,“瞎子大爺”總要坐在小凳子上,抽一鍋旱菸,休息一會。我呢,就守在死雞的旁邊,看它還會動不。那個惱人的黑貓,靜靜地蹲在旁邊的牆頭上,靜靜地看著,從來沒打算跳下來,叼上一口。
爐子上的水滾了,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音。“瞎子大爺”把旱菸鍋朝鞋底上一磕,往鏽花菸袋一塞,再往炕楞邊一擱。他端起鐵鍋走到門前,在臺階上放穩坐實後,拾起地上的死雞,先是頭,再是雞身,一節一節往滾水鍋裡放,來回左右上下,讓雞毛全著水。之後便是褪毛,開膛豁肚。還嫌不淨,“瞎子大爺”再煒一把火,把雞肉支在上面,翻轉著燎毛。剩下的工序就是下鍋做成香烹烹的燉雞。當然,這些餘事就不在我關心的範疇了。而且,我見過“瞎子大爺”多次的殺雞,可是,從來沒見過他吃雞。我有時也想,他肯定吃過,就是不知道,是啥時候吃的。但是,我毫不懷疑“瞎子大爺”做菜的水平,就是現在,我也能聞到那股菜香的仙味!
“瞎子大爺”有身高,穿扮很整潔,要不是天生雙眼失明,絕對算得上氣宇軒昂的美男子。一回,不知因甚,外邊“二毛子”黃風,刮個不停,房子裡就我和他,還有那個黑貓。他還是躺在褥氈上,半身靠著鋪蓋卷,我仍然立在炕楞與爐臺的角角。他說,他是三歲時,父母把他寄在廟上,在廟裡長大。侍候師傅,學音韻,學樂器,學做法事。從當徒弟開始,一步一步作到住持,成為城隍廟的大當家,領有徒弟徒孫幾十號,個個能文能拉能吹,笙管絲絃,鐃缽鑼鼓,樣樣都精,方圓近百里的紅白喜事,全讓這班廟裡的樂僧給包了。最得意處,他還比劃著,說,一場白事下來,僅饅頭就有幾口袋。由於當時正處飢餓時期,我連個饅頭也沒見過,更不用說白麵饅頭!所以,“瞎子大爺”說著,我的口水一個勁地向上翻騰,我想,“瞎子大爺”更不好受吧!他是吃過白麵饅頭的。
“瞎子大爺”對寺院,特別有感情,說,要是沒有廟上,他絕對沒活頭。後來,他當住持後,凡來廟上窮人都有飯吃,有些乾脆就不走了,幫著廟田種地。有些受濟的窮人,後來發達了,也常回廟上佈施。所以,香火越來越旺盛。直到“文革”開始,廟裡的人員,全部還俗。而且,廟門關閉,神像被毀,禪堂拆除。他是因為年齡太大,父母早歿,無處可歸,才被安頓在我們家的小正房。
“瞎子大爺”從廟上被趕出後,落籍就在我們的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能力,算是“五保戶”對待。
“瞎子大爺”從我們家搬走,是在我上完小學後。由於學校的溫暖環境,我馬上成為了學習和革命的先進,在同學和老師中找回了自信。所以,也就很少去“瞎子大爺”家了。直到有一天,從高中放假回家,才聽說“瞎子大爺”過世了,是上吊死的,八十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