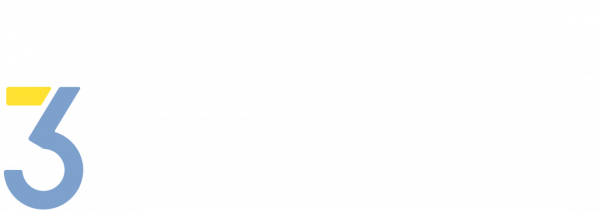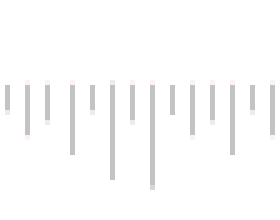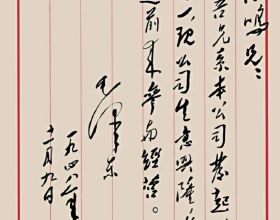真慘,婁燁導演的新片《蘭心大劇院》,儘管有堪稱頂配的陣容——
鞏俐、趙又廷、小田切讓、張頌文……還是市場遇冷了。
上映近一週,票房不過1800萬,甚至快被點映的《不速來客》趕超。
今天,飄不主談電影。
而是想借片中的演員王傳君,來聊聊一類群體。
國產大女主角電影裡,性壓抑的小男人們。
或許,這類角色將成為內娛小生轉型實力派的新賽道。
(注:該章節涉及部分劇透,介意請跳讀)
《蘭心大劇院》的故事,發生在1941年12月底,聚焦孤島時期的上海。
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週,著名演員於堇(鞏俐 飾)大張旗鼓回到危城。
目的成謎。
引來多方注目。
其中便有王傳君飾演的莫之因。
同片中大多數角色一樣,他身份也不簡單。
既是譚吶(趙又廷 飾)戲劇的製片人,又是汪偽政府情報員,同時暗地裡還和日本軍方密切往來。
簡而言之,留著漢奸頭、西裝革履的他,是標準意義上的反派,是“一個變態”。
這一非常容易標籤平面化的人物,卻在導演婁燁與演員王傳君的共同作用下,釋放出不一樣的滋味。
而進入他的關鍵詞,是慾望,是他與白雲裳(黃湘麗 飾)的糾纏。
最初,白雲裳打著粉絲旗號,去接近於堇,想要一探究竟。
知道她是國民政府情報員的莫之因,就此想要套近乎。
車內,面對年輕貌美的白雲裳,他先誘之以利,又妄圖動之以色。
一面,傾身靠在她耳邊,呢喃著:“跟我合作吧,我讓你舒服。”
一面,不等對方回覆,手底下就開始不老實。
然而,白雲裳卻毫不容情地,狠狠扇了他一巴掌,力度大到眼鏡都快被打落。
當此大辱,莫之因一言不發。
只是把眼鏡拿在手裡,埋頭看了看。
收住眼底洶湧的情緒,再扭頭望了白雲裳一眼。
她冷冷說了句:“開車。”
他便帶上眼鏡,扶好帽子。
只抽了幾下鼻子,“嗯”了一聲,依言發動汽車。
不管外表如何體面光鮮,其實莫之因的內裡,不過是色厲內荏的小赤佬。
哪怕頂著製片人名頭,因賣國求榮的行徑,劇團裡眾人皆看他不起。
他身上裹著厚重的毛皮大衣,卻撐不起想一展雄風的羸弱身板。
他對白雲裳的慾望,不是男人對女人的愛慾。
而是,欲圖透過征服這個高傲的女人,來證明自己可以。
是想透過佔有女人的陰道,來滿足自己對權欲的渴望。
所以他威脅、強暴白雲裳時,要反覆逼問:
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
色意伐(刺激吧)
他骨子裡,深深刻著自卑的基因。
才要在最像男人的時刻,還要反覆追索答案。
才只能借強權之手,以強迫手段達到心理與生理的雙重高潮。
就像回到了前不久的晚宴。
他被同劇團的演員推搡。
他點頭哈腰地對日本軍人報上自己的名字,卻換來一句:“誰他媽在乎啊。”
此刻,在進入白雲裳身體的那幾分鐘裡,他暫時地拋卻掉那些不堪的記憶。
白雲裳、於堇、譚吶……那些瞧不起他的戲子們,都被他壓在身下。
“一旦暴力進入劇場,演戲的和看戲的無一倖免。”
婁燁說。
在劇場後臺上演的這幕暴力,能把所有人吞沒與摧毀。
王傳君飾演的莫之因,既是一個鮮活的、具體的人。
又是廣義的、抽象的符號。
它的名字叫——慾望。
熟悉婁燁的影迷都知道,他標誌性的手持攝像,既出於對“記錄式攝影”的個人追求,也是為了保證表演的自由度。
《蘭心大劇院》的劇本是開放的,沒有規定演員具體的動作與臺詞。
導演指導演員時,“不是按照符號和身份來進入角色,而是從很具體的東西出發”。
比如,這個人物的前史如何,和其他人的關係如何。
它們不會出現在電影裡,卻是去掉好與壞的符號,建構起“人”的開始。
王傳君說婁燁的口頭禪是“隨便”,拍他的電影自由度非常大。
可以舒展全方位的自由,對好演員是酣暢淋漓的釋放,是能夠與對方棋逢對手的較量。
對不夠好的演員,則意味著無所適從,甚至是對職業信心的摧毀。
還好,儘管這次只是個八番的配角,王傳君不光在有限空間內接住了戲,還能讓人琢磨餘味。
從昔日的關穀神奇走到如今——
飄私以為,對他而言最重要的轉折點,來自另一個色慾滿滿的配角:《羅曼蒂克消亡史》裡的馬仔。
滿腦子都是“傢伙和女人”的馬仔,下流卻仗義。
會一臉窺視欲地打量他帶的小弟,用上海腔調問他“弄過嗎”,嘲笑他“還是個童子雞啊”。
但也會自掏腰包,給小弟尋找能幫他“弄一下”的女人。
可惜馬仔死得早,統共亮相三場,被亂槍掃射時電影才進行到四分之一。
但他的生與死間接開啟了另一個人的覺醒:杜江飾演的“童子雞”。
說間接,是因為飄認為,讓“童子雞”甦醒的直接因素,是女人。
“童子雞”是從江浙地區來上海的鄉下人,老家還有個等他回去結婚的“相好”。
他出來闖蕩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站穩腳跟,賺夠錢。
他對世事懵懵懂懂,時常露出天真的憨笑。
哪怕被朋友嘲笑是“小雞雞”,也只會收住笑,低下頭默默不語。
但第一次殺人,他又那麼兇狠不要命。
是由於當時支撐他的一切力量,就是求生,就是賺錢。
他要證明自己不是“童子雞”。
但當性不可得時,只能透過暴力手段來彰顯荷爾蒙。
當血飛濺到他面上時,完成了從男孩到男人的第一步。
第二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是性。
從大屠殺中僥倖逃生的“童子雞”,中槍後甦醒過來,恍恍惚惚中,去了王傳君為他找的、幫他開苞的妓女霍思燕那裡。
淌著血,在霍思燕床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一宿。
這是導演程耳對杜江講戲最多的一場。
他要杜江對著霍思燕,露出一個微妙且曖昧的表情來。
程耳告訴他,在那一刻,童子雞突然覺得很舒服,有點忘記了自己身上的傷,有點釋懷,心想今天也許會死在這裡吧。
臨死前看到一個曼妙的女性身體隱隱約約在珠簾背後,這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慰。
來源 | 橘子娛樂
這場戲從早上拍到深夜。
“童子雞”的臉上,首次有了裂縫。
你看他慢慢坐下來,一點點倚靠到身後的牆上。
從茫然,再到豁然,隱隱含了笑意。
彷彿世界洞開,窺見了人間的大秘密與大歡喜。
這才有了後來霍思燕照顧重傷的他,他醒來後賴在了霍思燕那兒。
霍思燕叫他回老家,尋相好的結婚。
他說他老早就忘了。
霍思燕眼裡汪著淚,抱怨他傷好了,還留在這兒做啥。
他說他“上癮了”“離不開你了”。
直到丟擲他對她能做出的終極承諾:“我養你。”
冷血殺手蛻變為養家男人,看似是被女人迷了魂。
實則他的眼神,有了前所未有的堅定。
原本模糊不清的未來,在遇到這個女人,在與她有了肌膚之親後,終於呈現清晰的輪廓。
他看到了人原來除了走別人安排好的路,還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他明白了成為男人的真正意義,不在於你殺了多少人,賺了多少錢。
而是肩負責任,並願為之矢志奮鬥。
發現沒,莫之因也好,“童子雞”也罷,這些男人的轉變,或多或少都與女人相關。
所以王傳君在《羅曼蒂克消亡史》裡戲言:“弄一弄,你的經絡就通了,就會發現以前的日子都白活了。”
笛卡爾曾說:“愛會影響你的脈搏和胃口。”
性亦如此。
它從來不止關乎“性”,而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脈搏和胃口。
表達人們對生命感知的最複雜的原始衝動。
唯有赤裸裸地直面、反觀自我的內在慾望,才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複雜的性也成為電影裡,折射社會世態的一扇窗。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許多港人心中的“黃金年代”。
隨著女性經濟與社會地位皎如日出升起,男人日漸被反襯得黯淡、無光。
男性普遍焦慮的背景下,港式中產喜劇片中,批次生產出一波“小男人電影”。
圖源 |《小男人週記》
片中那些“小男人”們,自卑,呷醋,處處失勢,乃至性無能。
甚至標準愛情喜劇如《孤男寡女》中,都安排了讓劉德華吃牛鞭的隱喻。
類似的情況到了這幾年的國產片裡,就是大女人戲裡,那些慾望被壓抑的男人們。
相比作為主菜、光鮮帥氣的男主角,這類角色往往只是一例配菜。
但人性深層慾望勾出的豐沛與複雜,賦予了他們相對自由的創作。
讓他們能跳出完美卻相似的角色,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尤其這兩年國產大片裡,中生代演員多在主旋律戰爭片或奇幻電影裡打轉。
不是說這類題材不好,而是置身其中的演員,往往負責的是功能性敘事,是靠樹立英雄來滿足觀眾的想象。
比如杜江,在《紅海行動》後,儼然成為“主旋律小生”的熱門人選。
但他最有記憶度的角色,對飄而言,仍停留在“童子雞”那裡。
還有接連在《八佰》《金剛川》《革命者》中亮相的李九霄。
刀子之類的角色,在群像電影有限的戲份裡,給予觀眾最多的印象,不外乎“熱血”“燃”“帥”等關鍵詞。
反觀《送我上青雲》裡他飾演的四毛。
一番雲雨後,他躺下休息,卻聽到身旁姚晨自我愉悅的呻吟。
曾吹噓自己“很厲害”的肥皂泡,就在聲聲叫嚷裡破碎——
女人的滿足,居然不是靠他,而是靠自己完成。
被傷了男人自尊的四毛,起身,望住姚晨三秒,躺回原處。
那三秒中眼裡湧動的情緒,勝過之後所有的言語。
性是私密的,是個人的,是難以言說的。
同時,它又是流動的,是多元的。
關乎自己與他者的關係,關乎自我在世界中的所處。
因此《性學觀致》中才說:“性是一個生物學功能,但它只有透過社會化才能獲得其形式和意義。所有的文化都影響著性行為,但方式各不相同。”
具體到表演方法上。
哪怕是和同一個物件,在不同感情階段,都會有各異的表達。
所以李安在拍《色,戒》每場激情戲前,都會私下和梁朝偉溝通,把要求的每個鏡頭都說清楚。
讓演員知道他做的每個動作,都有不同的動機、意義、心境與感情。
如此,激情戲才成為一雙眼,讓人看到易先生內心活動的外在化。
在滿是“炸裂式演技”吹噓的今天。
把握諸多複雜的層次,同時搭建好與對手戲演員的默契配合,才更是內娛小生演技的試金石。
夠膽來試,或許這類角色就是他們以演員身份被人記住,漸漸翻紅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