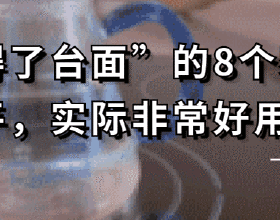老顧也是修腳踏車的。
他是我光顧最多的腳踏車攤。老顧的修車點在他的家前面,驥江路和漁婆路的交叉口。
老顧有一口燦爛的牙齒,還有一雙煤炭工人般的黑手,所以,他常常說自己是“黑手黨”——腳踏車的機油和灰塵染成的。
白天裡,老顧的身邊坐有許多老人,老人們彷彿是老顧的監工。他們看著老顧修車,補胎和打氣,到了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再坐在老顧的身邊做“監工”。
這些老人其實也在監視著路口發生的許多故事。
但這些故事都和老顧沒有關係,修車的老顧很是專注。
到了晚上,老人們全回家了,老顧不做生意了。他開始喝酒,剛抿了幾兩酒,神奇得很,如釣魚的姜太公,躺在那張老躺椅上,聽電臺裡播的講經。
偶爾也有生意的。見到有生意光顧了,老顧的小狗就會推他的腿。
狗名叫虎子,被他修理得很聽話。老顧回鄉下過年的時候,沒把它帶上,而是在虎子的窩裡放了五天的食,真不知道虎子是如何把五天的食平均成五份的?
我以為,老顧的虎子,是真正懂數學的。
電臺裡的講經總是會播完的。一旦播放完了,路上已空曠了許多。幾乎見不到腳踏車了。老顧會摸出工具箱裡的空竹,開始抖他的空竹。
空蕩蕩的深夜路口,那嗡嗡嗡的空竹聲,彷彿有無數只鳥的翅膀在振動——是什麼鳥翅呢,我猜了幾種,最像是是那種灰椋鳥。小小的,比麻雀還小,但比麻雀更為堅定的,如逗號一樣的灰椋鳥。
也不知道老顧是什麼時候停止修車的,只知道有很長時間見不到他了,那些老人坐過的老木椅翻放在路邊,很是落寞。
有時候會遇見虎子,虎子也變得很警惕,躥行出來,又很快消失了。
我很想去老顧家問問,但還是沒去問。
再後來,過了有半年時間吧,我終於在路上遇到老顧了。問起他的去向,他說他現在城北橋那裡看一個工地。
我問他辛苦不辛苦,老顧說談不上辛苦不辛苦,反正就這樣看著就行。
當時我正騎著一輛公共腳踏車,有點尷尬。老顧卻不尷尬,還說這腳踏車是實心車胎,不用打氣的,很好。
又過了半年,我見到老顧的機會多了,再問他,他說不去看工地了。
老顧說得很平靜,牙齒很白,手依舊很黑。
那些經年的機油和灰塵,就像我們面前不得不的生活,真是頑固得很。(龐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