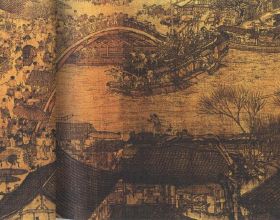現在是新冠病毒被發現並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第二十個月,這場傳染病大流行剛剛開始的時候正好是中美兩國矛盾擺上檯面的開始,而在將近兩年之後,疫情已經差不多要過去了。
或者說其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到此為止了,接下來就算病毒繼續傳播也已經不再能過多觸動人們的神經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冠病毒對國際社會的影響終將結束,但中美關係卻絕不可能回到過去所謂“正常的中美關係”。
實際上與新冠病毒一起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還有民族主義的思潮,或者說,當今世界正處於“整體性右轉”的階段,我們能看到許多國家出現了官方的亦或者是民間自發的右傾傾向的聲音。
比如說,日本右翼崛起主張更深度地發揮日美同盟的軍事價值,未能成功當選首相的前候選人高市早苗曾提出了“無條件支援美國部署中程彈道導彈對抗中國”的主張。
而澳大利亞當局也透過鼓吹種族主義言論為當局無底線的反華政策奠定合法性,他們是主動右轉的代表,其國家統治階級直接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作為綱領進行宣傳。
而被動右轉的國家,比如說法國,愛國的退伍軍官們向總統致信痛斥國家秩序被破壞的現狀。
由於伊斯蘭世界湧入的難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並與原住產生摩擦衝突導致民間整體性的種族主義思潮崛起。
另一個例子是德國,在默克爾即將卸任的2021年,德國國內的右翼勢力也蠢蠢欲動,並準備在社會主流思潮上徹底打破戰敗後對民族主義反思帶來的禁錮。
這些主動的或者被動的,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的種族主義崛起的現狀,一方面可以說是國際秩序出現了失衡。各國人民的期望與社會現狀出現了分歧,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國際秩序出現鬆動之後野心家們野心釋放的結果。
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秩序最主要的雙邊關係,這一點我相信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而中美關係出現的變化。
如果是朝著一種負面的方向發展,那麼必然會危及到當今的國際秩序,秩序的鬆動與重構,這個過程本質上也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任何人都會在這個過程中嘗試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
比如說土耳其,雖然總是有人嘲諷“國中土耳其”,但不得不承認,至少最近幾年土耳其這個國家的戰略目標得到了非常成功的推進,埃爾多安總統復興奧斯曼帝國榮光的大業確實是朝著更加現實的方向發展的。
一方面,土耳其對敘利亞內戰的干涉是頗為成功的,雖然最大的贏家是俄羅斯,但他們也確保了自己基本的利益訴求。
而在美國撤軍之後,伴隨著奉行獨立、強主權的阿富汗新政府的成立,土耳其夢想多年的,從巴基斯坦一路通往土耳其的,由伊斯蘭國家構成的陸上國家沿線終於打通,雖然距離自己能夠肆意妄為的程度還差了一些。
因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了對中亞擁有最大政治影響力的國家,但至少中國與土耳其在中東戰略沒有根本矛盾。
中國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訴求的中東戰略並不會阻礙土耳其以伊斯蘭教認同構建一個伊斯蘭國家合作框架乃至於鬆散的中亞國家間聯盟的最終目標。
最後在土耳其影響、支援下海量的中東難民湧入歐洲,正給歐洲各國的社會治理帶來巨大壓力,確保了現階段土耳其國家安全上不會受到任何威脅的局面。
至於說創造出這種局面的到底是誰?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土耳其至少作為標準的騎牆派、牆頭草,趁亂牟利這一點上還是做得很好的。
除了土耳其之外,還有一些國家的野心不容輕視,日本和德國,這兩個二戰戰敗國,如今作為國際上重要的經濟體之一。
其在地區國際事務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相比起五大常任理事國中較弱小的英國與法國而言,他們的影響力其實是要更大一些的。
但因為戰敗的歷史包袱,其國際地位、聯合國框架內的話語權大小與其國家實力、影響力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他們也必然會尋求打破這種現狀。
雖然這麼說可能政治不正確,但在不考慮歷史包袱的情況下,僅僅從國力與地區事務影響力的角度看,日本與德國顯然要比英國與法國更適合擔任常任理事國。
當然有一點是值得慶幸的,就是德國與日本在當今世界上距離前三強的差距已經非常大,也不再具備直接發動戰爭對外擴張的能力,他們謀求更高的國際地位的過程只能以一種比較溫和、文明的方式進行,所以尚且稱不上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但可以確定一點,就是未來一段時間,如果日本政府總體上是右翼把持朝政的話,那麼他們會全力挑撥中美關係,為日本國家正常化積累資本以及為日本擴軍乃至於廢除《和平憲法》尋求依據。
如果希望中美關係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局面,那麼日本幾乎必然成為中美關係最大的隱患。
這在現在也是有許多證據做支撐的,比如說臺灣問題上,除了美國以外,日本是干預臺灣問題最積極的國家,甚至還明確提出了一整套將軍事投送能力拓展到整個臺海的軍隊部署計劃。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雖然歷史包袱仍然在阻礙著兩國社會的融合,但兩國有著廣泛且深厚的民間交流,中國對日本也有著比較高的期待。
未來中日關係的處理,日本要如何在兩國巨人之間控制好平衡,這將是對雙方政治智慧的一次艱鉅的考驗,也將對兩個國家的命運造成深遠的影響。
而德國正在逐漸成為歐洲的中心,實際上非常諷刺的是,德、日這兩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策源地都發現,他們當初發動戰爭,給世界人民帶去深重苦難,卻並沒有實現戰爭的目標,乃至於將自己推向了深淵。
但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很多年,他們的反而實現了,日本在美國的保護與奴役下獲得了全世界的開放市場,日本企業的資產在國際上享受著與美國企業一樣的安全保障,沒有人敢直接制裁他們的企業。
而德國,也在冷戰結束後透過歐盟這個框架成為了歐洲的中心,擁有比法國更大的影響力,實質上已經掌控了歐盟的鑄幣權,他們當年整合歐洲的目標正在以一種和平的方式變成現實。
儘管前方還有很多阻礙,幾個主要國家都會阻止他們統合歐洲的過程,但德國已經享受到了整個歐盟經濟體系的紅利。
接下來,明確對外聲索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已經只是時間問題,現在他們還將這一問題的爭論侷限於歐盟內,隨著接下來兩年美歐關係進一步走遠,以歐盟的名義索要國際社會的承認將會是必經之路。
這些國家的野心家們的主張,不僅有來自精英階層的認同,同時也擁有廣泛且穩固的社會根基。
這種重振國威的意志正在塑造出一個右翼傾向的社會氛圍,當這種氛圍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對外以各種形式擴大影響力的行動程序將只取決於其能力大小而不取決於其主觀意願。
但對於中國而言,以上國家暫時都稱不上是威脅,對於中國威脅最大的是西南部的鄰居,也就是印度,這個我們陸地上直接接壤的鄰國,擁有十多億的人口,甚至比中國更加充沛的勞動力,特別是,印度現在已經有了很充足的理由與中國敵對。
在過去,中印兩國之間就一直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比如說印度想要在完全整合,亦或者至少是控制南亞國,他們甚至完全不掩飾控制周邊國家的野心。
印度在1949年逼迫中印邊境的小國不丹簽署了一份《永久和平友好條約》,根據這則條約,不丹在內政事務上必須接受印度的領導,並且外交權被印度掌控,赤裸裸地干涉內政到這種程度說不丹是印度的附庸國都完全沒有問題。
敢於這麼做,一方面印度也確實在南亞擁有霸主國家的地位,畢竟周邊都是一些小國,印度社會雖然也落後,但架不住個子大就是能欺負人的,另一方面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
印度也是英聯邦國家之一,與西方保持著接近同盟的關係,所以不用在乎受到西方的打壓。
而印度控制乃至於整合南亞世界的主要阻力,來源於域外的中國,否則的話巴基斯坦現在是怎樣的命運可沒有人說得準。
最後,印度與中國是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過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中期,兩國在國際生產體系上處於同一生態位,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關係,這些都是過去中印兩國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而現在,兩國的矛盾更加尖銳了,因為阿富汗問題上中印存在截然相反的主張,中國是支援中亞國家和平發展建設經濟的。
而印度作為一個仍然將宗教作為主要社會共識構建工具的國家,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大多數必然反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亞國家,從印度的角度講他們希望中亞國家越亂越好永遠不要發展起來。
而現在中國正在支援阿富汗,並準備為了一帶一路協助阿富汗的現代化重建乃至於將中亞國家拉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
未來這個具有更強經濟實力的中亞世介面對一個印度教並且積極尋求擴張與一定程度上尋求宗教擴張的印度必然形成敵對關係。這一點印度當局自然是非常清楚,所以他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敵對中國。
2017與2020年兩次中印邊境衝突,雖然印度方面沒討到什麼好處,但他們可是有備而來,有明確目的的,現在還與美國形成了四國聯盟,未來雙方會在對抗中國這個問題上達成多麼深入的共識,以怎樣的方式共同行動?無論如何對中國都不是一件好事。
而在對印關係上,中國應當充分利用印度與美國存在的一個根本矛盾,阻止美、印之間形成緊密的軍事聯盟關係。
美、印關係的隱患在於印度洋的控制權,這是1962年在邊境挑起戰爭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斷言,印度主張“印度洋是印度之洋”,而美國自然反對這種主張。
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不願意退步,這是迄今為止美印兩國都沒有進行極其深入合作的根本原因。
但未來,隨著中國實力的進一步崛起,面對中國這個共同對手,美、印兩國能否擯棄前嫌?只能說如果這成為現實對中國而言將是外部安全環境的巨大威脅。
哪怕印度社會動員能力極差,哪怕印度軍隊腐朽不堪戰力弱,但畢竟是一個十多億人的國家,美國可以援助海量的武器裝備與錢財來武裝他們,給軍事基地稀疏且空防並不算嚴密的中國西北地區構成威脅綽綽有餘。
但好在,中國與這些國家之前都並不存在很根本性的無法調和的矛盾,哪怕是印度,其本身也在享受著一帶一路的發展成果並在金磚國家框架中與中國存在一些合作。
這就決定了,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美國永遠不可能建立起一個類似於冷戰時期北約那樣的軍事聯盟來封鎖中國。
恰恰相反,如果說在某個時間點以一種合適的方式退場的話,其實很多國家會樂於看到美國霸權的衰落,畢竟只有美國衰落了,印度洋才可能成為印度之洋,德國也才能過成為歐洲真正的領導者,日本也才能夠獲得一個絕對安全不受壓迫的國際貿易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