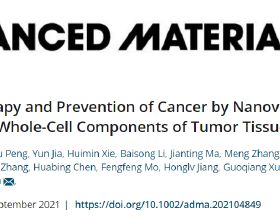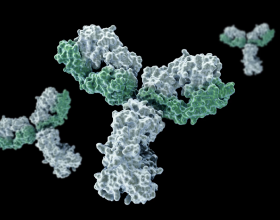飽受種族歧視的19歲一等兵,陳宇暉舉槍自盡,子彈從下顎穿過頭顱,左手手臂上留下黑色馬克筆寫下的兩句遺言:“植物人,拔管”,“告訴我的父母對不起”。這是發生在2011年10月3日,美軍駐阿富汗坎大哈地區軍事基地的一幕。
很快,陳宇暉的遺體被發現,隨即被曝光的,是這位新兵在不到半年時間內,所遭受的種種虐待。而虐待他的人,並不是他的國家派他去面對的那些敵人,卻是原本應該與他同仇敵愾互相扶持的戰友們。
2001年“9/11”事件後,美軍進入阿富汗,開始了反擊“基地”等恐怖組織的戰爭。2011年8月,當接受完新兵訓練的陳宇暉到達阿富汗時,本•拉登已經被美軍擊斃,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達成了目標,迎來了拐點。從7月開始,美軍主力已經開始撤出阿富汗戰場。
整日訓練和站崗的生活與陳宇暉最初參軍打仗的理想之間有不小的落差。而這還並不是最讓他失望的,早在喬治亞州便寧堡軍事基地接收新兵訓練時,陳宇暉就已經受到了歧視和排擠。
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說:“我是唯一的華人,他們每天都會問我幾遍是否從中國來,用怪怪的聲音叫‘阿陳’。人們時刻拿華人開玩笑,我已經沒有多少笑話可以回應他們了……
到了阿富汗之後,一切開始變本加厲,陳宇暉的隱忍並沒有讓他獲得多少同情。他的8名上級(包括一名中尉、兩名上士、三名士官、兩名專業下士)變著花樣地戲弄他。
他們把他從床上拖到地下,在碎石路上拖行十幾米,造成他滿背劃傷瘀傷;他們讓他嘴裡含著水做仰臥起坐,不準吐出來;讓他保持坐姿並踢他的膝蓋;作為所在排中唯一的華裔,他被要求戴上綠色的頭盔用中文喊口號,被他們稱呼為“龍女士”……
集體霸凌的行徑不僅刺痛了他的身體,也摧毀了他的精神。2011年10月3日那一天,他因為早上7點半去站崗的時候忘記戴頭盔,一位上級懲罰他穿著全副裝備冒著同僚們投擲來的石塊在碎石路上爬行100米。等他走上警戒塔,又有一位上級軍官扯著他的防彈衣將他拽下了臺階。一直到8點,他才被允許進入警戒塔執勤。
上午11點13分,一聲刺耳的槍響從警戒塔內傳來……
除了手臂上短短兩行字的遺言,陳宇暉在死前並沒有留下更多的話,也沒有嘗試做更多的抗爭。但同樣是華裔的藝術家們,則希望能幫他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把壓抑許久的不平喊出來。
2021年10月16日,“陳宇暉”站在了紐約巴德學院理查德費舍爾表演藝術中心的舞臺上,大聲唱出了一個華裔美國士兵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軍隊裡被當作“外來人”的困惑、憤懣和絕望。
作曲家黃若告訴紐約華人資訊網記者,陳宇暉的形象和故事在新聞裡很快就淡出了,沉沒了,但卻可以在一部歌劇裡一直存在,不斷地被講述,不斷地讓人們看見。而且這個故事存在的形式並不是紀錄片式的,它也不是一個個案,而是華裔真實的生活和困境。
這種困境從“天使島”的排華血淚史開始就一直存在,“現在不僅沒有結束,反而在疫情期間進一步地擴大了”。
以華人故事為創作題材,在黃若看來,是不僅有價值、而且有必要的一件事。他認為,華裔的辛酸歷史本身就是美國曆史的一部分,卻沒有寫進美國的教科書;華裔作為美國社會的一員,卻總是被當作“外來者”對待。所以我們的故事、我們的聲音有必要讓更多的人聽到,讓公眾瞭解,因理解而包容,從而推動華人等少數族裔從邊緣融入群體,推動這個社會往前走。
10月19日晚7點開始,第四屆紐約中國當代音樂節的最後一場線上交響音樂會,透過費舍爾表演藝術中心線上直播平臺,及古典音樂資訊網站The Violin Channel,對全球公眾免費播放,《一個美國士兵》選段,被串聯在一系列華裔移民故事主題的作品裡。
從黃若的《天使島》的故事和《一個美國士兵》,到龔天鵬的《一箇中國人在紐約》與李昕豔古箏協奏曲《覺醒之光》等等。
一批華裔藝術家的作品連線成了反映一個多世紀以來華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和心聲的專題。音樂會的選段隨後也上傳到了Youtube等影片平臺。
《一個美國士兵》除了由華裔作曲家黃若作曲,還有另一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任編劇。早在2013年,黃哲倫就在陳宇暉親友的委託下,構思如何能用藝術的形式將陳宇暉的故事記錄下來,他找到黃若商量,二人一拍即合。一開始做出來的是獨幕劇,後來又改成雙幕,而這一次的演出與“天使島”等事件呼應起來,更是直接照映進當下正在發生的歷史。
我第一次見到陳宇暉的母親,已經是那件事發生之後兩年左右了,在一個小型的紀念會上。黃若說:即便已經過去兩年了,他媽媽還一直在流淚,講每一句話都忍不住抽泣,沒有一句話能夠說完整,讓我迄今為止記憶深刻。他跟他媽媽之間的母子情,兩代人之間的對話也是這部劇要表達的重要內容。
作為關照人性的藝術作品,並不是在討論一個政治議題,而是在表達一個兒子在客死他鄉之際的思念,一個母親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傷。”陳宇暉的母親陳素珍也是流著淚看完《一個美國士兵》,她告訴黃若說:“感謝你們把我兒子的故事寫成了歌劇,讓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在其他母親身上。
陳宇暉從小生活在曼哈頓中國城的堅尼路和伊麗莎白街附近,就是現在“陳宇暉路”路牌所在的地方。他喜歡玩手球,喜歡吃麥當勞,成績優異,是“別人家的小孩”,也是父母的驕傲。
他的街坊鄰居,很多都是祖籍廣東的華裔移民,在他離世後積極為他奔走維權,也年年都在他的忌日裡紀念他。
為了瞭解陳宇暉的故事,體會他的境遇和心情,藝術家們跟他的親友聊天,蒐集他留下的資料和資訊,而越是深入瞭解,就越是感同身受,彷彿這就是自己的故事。
陳宇暉的母親是一代移民,80年代才從廣東臺山到美國,不會說英文,只會講客家話。陳宇暉是二代移民,在曼哈頓中國城土生土長,習慣了說英文、寫英文,自我認同完全是一個美國人。
與很多一代移民父母一樣,陳素珍夫婦希望自己的獨生兒子好好讀書,上好大學,今後能做醫生、律師這一類的精英工作,出人頭地。
但是二代移民陳宇暉,卻與父母的想法不同,他想要按照自己理解,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方式生活,參軍一直是他的理想。
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二代移民可能更為敏感,也更容易困惑。
黃若解釋說,比如編劇黃哲倫就能比自己更能體會陳宇暉的心情。黃哲倫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自我認同也是美國人,但是因為有一張東方面孔,別人會問他:“你的英文說得真好,是在哪裡學的啊?”那他就會覺得很奇怪,沒有辦法回答。而且在自己的家鄉卻被當作“外人”,是一言難盡的滋味。但是作為在海南出生,母語是漢語,19歲才到美國讀書的黃若來說,如果遇到別人問這樣的問題,可能就會自然的回答我一開始英語也不太好,後來是怎麼學好英語的。
但是無論一代移民,還是二代移民。無論是藝術家、知識分子還是工商業者。少數族裔在生活中遭遇的歧視和在職業生涯中遭遇的瓶頸,都是現實存在的。
黃若告訴記者,像其他很多領域一樣,華人藝術家並不缺乏才華和貢獻,但往往比較難獲得重要的獎項和藝術團體中重要的崗位。
在美國,從多元化的角度和社會的寬容度而言,紐約與其他保守州比較起來,已經算是相對好的地方了,但隔閡和瓶頸依然存在。比如一旦發生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亞裔包括華裔就會遭殃,包括這次新冠疫情引起的仇恨現象也一樣,仇恨事件和攻擊事件依然不斷地發生在我們身邊,讓我們立刻失去安全感。
所以,作為藝術家的黃若認為,藝術是可以做些什麼的,不僅是一種敘事手段,讓更多的人知道歷史上和現實中發生的這些故事。讓更多人瞭解不僅僅是“中國菜”和“長城”的中國文化,讓大家獲得知識,也是一種促進社會和文化融合的手段。
對藝術本身而言,也是儲存和更新的一種手段,他嘗試著將《山海經》寫進交響樂,將《牡丹亭》的崑曲唱腔融合進西洋歌劇的表演,都是想要推動這樣一種認識和融合,“因為人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