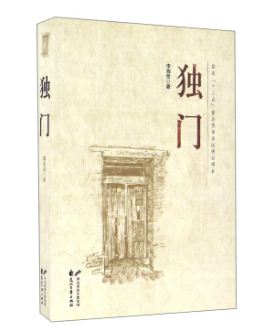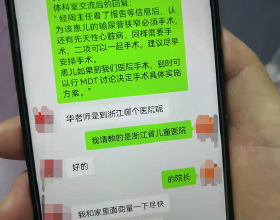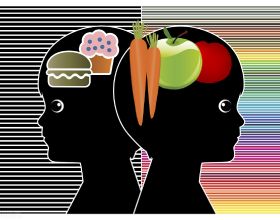我出生的時候只有四斤三兩,再加上孃的奶水不夠,使我顯得很賴巴。爹孃對我的成活率喪失了應有的信心,每天對著我唉聲嘆氣。
在我之前,屬於爹孃的產物只有姐,在姐之前和之後,曾有我的兩個哥哥出世,但都因為生下來不足5斤重,而沒活下來。我們李家急需人,特別急需男人。可我的倆哥,都在我的前頭無緣無故地死了。
據說,生我那天,爹有意躲在莊稼地裡不回家,生怕是個閨女,又生怕長得賴巴活不下來,是姐把他從地裡找回來。進了家,爹不敢看炕上的我,閉上眼,把手伸進我和孃的被窩兒,直到劃拉著了我那小命根子,才敢睜眼。但看我長得那個賴巴樣兒,扭頭又走了。
打那以後,爹每天干完活兒回到家,把鎬頭或者鋤頭往當院一放,衝進屋,仍是閉上眼,摸一下我那小命根子,才去幹別的。爹生怕哪一天我會變了品種,或者那小命根子會“噹啷”一聲掉下來。
按習俗,誰家生了孩子都在門吊兒上拴一個紅布條兒,以示極喜。但我出生以後爹沒讓拴,爹怕我一旦死了,自己空歡喜一場,也讓外人恥笑。
儘管我生下來只有四斤三兩,儘管家裡人都認為我活下來的希望很渺茫,儘管我一落生,爹就預備了一個破席筒,隨時準備把我像前邊的那倆哥一樣,捲起來挖個坑埋了。但我那親孃,還是正兒八經地享受了一次坐月子的待遇。
奶奶攢了100個雞蛋,是娘坐月子的絕對營養。我七天的時候,姥姥來了,妗子來了,倆姨來了,姑也來了。應該說,凡跟我家沾親帶故的,能走動開的人,都來了。她們帶來了雞蛋、紅糖、芝麻、掛麵等等,但她們見了小腦袋沒拳頭大,五官相當緊湊,跟個小賴玩意兒似的我,都認為,娘這月子又白坐了。
我過十二晌那天,因為給我起名兒,奶奶開了個家庭會。我前面的那倆哥,一個叫全勝,一個叫全保。據說,都是奶奶給起的,結果呢,一個也沒保住。奶奶對爹說:“你有文化。你起吧。”上過私塾的爹謙虛地說:“娘,孩子的名兒,都是你起。還是你起。”奶奶說:“我起了倆,都沒落住。這回不起了。”
爹見奶奶是真讓權,看著躺在炕上東看西看的我,就說:“小名兒就叫醜兒吧。名兒越皮實,越好養活。”奶奶“噗嗤”一聲笑了,對我說:“醜兒,長大了要尋不上媳婦兒,可都怪你爹。”就這麼著,我這“醜兒”就叫開了。等我長大會照鏡子之後,發現自己五官除了眼睛小一點兒之外,其他方面都相當湊合,起碼不至於醜得離譜兒。我想,爹當初根本顧不上我醜俊的問題,只想著讓我怎麼活下來。
我頑強地活到過滿月那天,好多親戚和鄰居,已經忽視了我的存在,沒人來看我(或許認為我已經讓席筒捲走埋了)。老人們說,三躺六坐八爬爬,十二個月會喳喳,可我賴巴,八個月了,根本不會爬,還沒被大人抱出去亮過相。也就是說,沒到我們家串過門兒的人,還不知道我是否存在。可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生命價值和奇蹟出現了。發現這種價值和奇蹟的是三叔。
我們家有一副象棋,平時沒人下,後來也就成了我的玩具。三叔把棋子撒在炕上,一邊指一邊教我:“這是馬,這是炮,這是卒,這是車。”
我不會發聲,但我已經記住了棋子上的字。之後,三叔把棋子弄亂,命令我:“醜兒,把‘馬’給三叔拿過來!”我那小手就伸入棋子中間,不慌不忙地把“馬”遞給三叔,三叔就把大拇指伸向我。
我家串門的人逐漸多起來,親戚們也來得勤了。他們來了,很重要的內容是考考我,是不是認字兒,是不是神童。
就這樣,在大王莊,都知道李家出了一個長得賴賴巴巴,但不會說話卻會認字的孩子,出了一個叫醜兒的神童。
■文/改編自《獨門》(李西嶽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編輯/賈立芳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