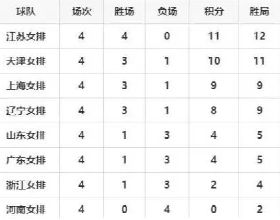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鍾建新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軍的軍人,也曾是駐守西藏高原的軍人。爸爸從1939年參加新四軍到1981年離職休養,在部隊42年,就有21年在西藏高原,我們家和西藏軍人的家一樣,聚少離多,我們姐妹三個和十八軍軍人,老西藏軍人的大多數孩子同樣,從小遠離父母,在保育院、八一校長大。父母兩年多才能回內地休假,我們因歲數小,也曾不認識父母,姐妹也曾不認識。小時候家的印象很少,父母回成都休假幾個月,住在西藏軍區招待所,招待所就是我們臨時的家,父母休假如果剛好遇寒暑假,我們就可以不留校,平時週末我們也可以回到臨時的家,臨時的家有歡笑,有趣事,有好吃的零食,可和父母幾年才相見,在臨時的家裡,記憶還是模糊的。
1966年,媽媽因身體不好,無法適應高原的氣候,也無法在西藏陪伴爸爸,回到了成都,在西藏軍區第三家屬區,我們終於有了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家,但還是缺少爸爸在家,爸爸一個人仍在西藏部隊。因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我們姐妹三人回到家裡,第一次真正在家生活。可是媽媽生病,我們姐妹開始學著做家務,這對從小在保育院、八一校長大,吃飯去食堂,衣服有洗衣班大叔洗,過慣集體生活的我們,有點難度。還記得媽媽讓我去市場買只母雞,一個女孩,第一次單獨去市場,我紅著臉很不好意思,鼓起勇氣買了雞,也沒弄懂是什麼雞,最記得手放在雞翅膀下提著,雞一掙扎,翅膀一夾緊,我就嚇得小聲尖叫,可又不敢把雞扔了,好不容易把雞提回家,媽媽和樓下的阿姨很高興,都過來看我第一次買的雞,公雞?母雞?都不像,正說著時,那雞突然腿一蹬死了,還沒搞清是公雞還是母雞,結果買的是一個瘟雞。大妹去蒸飯,只放米忘了要加水,小妹學著洗衣服,拿個小牙刷在衣服上一點點地刷,不知用手搓。那時家家燒的是蜂窩煤,我家沒有男孩,每個月姐妹三人都要把蜂窩煤搬上三樓,拿不動,一次就搬幾個,每個月不知要上下多少次才能把蜂窩煤搬完,不會用蜂窩煤,幾乎爐子天天熄,每天我們要學著用柴把蜂窩煤點燃,被煙燻火撩的鼻涕眼淚齊流。後來爸爸的大嫂從安徽蕭縣老家來住了一段時間,我們稱呼大娘。大娘為我們擀麵條、烙餅、蒸包子、包餃子、原來的北方的麵食那麼好吃,大娘還教我們做飯,後來我們笨手笨腳很多事還是做不好,可總算能把一日三餐混下去。
爸爸休假回到家,才是快樂的日子,家裡總是歡聲笑語。我們可以跟著爸爸外出玩,去菜市買菜,爸爸也和我們一起去,我們姐妹三個就像爸爸的小尾巴,爸爸去哪我們都跟著。爸爸有一輛那時少見到的藍色鳳凰牌腳踏車,輕巧漂亮,平時媽媽不讓騎,但爸爸回來休假,我們就可以在院子裡騎腳踏車玩。有一次我騎腳踏車摔了,腳蹬摔得貼在車鏈盒上,我怕父母批評我,就撿了塊石頭砸腳蹬,傻乎乎地想把腳蹬敲直,結果腳蹬沒敲直,還把鏈盒上的漆敲下來了,沒辦法,只有紅著臉把腳踏車推回去,爸爸看了一下腳踏車,又看了一眼漲紅著臉的我,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頭頂,說沒關係,等會到車鋪去修。爸爸溫暖的大手一摸我時,我差點哭出來了,心想爸爸真好。在我們第一個家裡,姐妹三人學會了一些基本生活常識,學會了做一點家務事,慢慢我們長大了,1969年,我和大妹同時報名參軍,離開了我們真正意義的第一個家。
1971年,爸爸從西藏調回內地,在溫江軍分割槽任職,住在軍分割槽大院裡,我從部隊回到家,家是平房,房間不多,但很寬敞。一個小院,用圍牆隔出一個小天地,院裡有棵桂花樹,中秋節前,小院總會飄出淡淡的桂香。家裡養了一隻毛色黃白相間的小花貓,虎頭虎腦煞是可愛,小花貓每天順著桂花樹上竄下跳,給家添了很多樂趣。夏日的夜晚,我和父母常坐在院子裡,輕搖著扇子,抬頭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常常就這樣乘涼聊天,在這些夏夜聊天中,我才慢慢知道了一點爸爸媽媽參軍後和在部隊的經歷。
小院的屋後,圍牆下也留有一小塊空地,牆外是文化館,每天會傳出老師拉手風琴的優美旋律,我也每天都會坐在後院,如痴如醉聽那位沒見過面的老師拉出音色變化豐富,歡快和抒情的,或節奏感強的不同風格曲目。這時的我也常回想在西藏軍區第四野戰醫院,每個科室都有一部手風琴,女兵們在醫院後門的馬尾松林裡,學拉手風琴的專注和刻苦,可以拉出一些簡單曲目後的快樂。
我因在西藏部隊時,患上較嚴重的高原性心室擴大,從西藏返回成都的路途中,在雀兒山頂上突發嚴重高反,差點失去生命,身體很弱,回家後,靜養了好長一段時間,爸爸後來帶著我去華西醫院,成都軍區總醫院反覆複查心臟幾次,直到確認我已完全恢復,才准許我去上班。在這個靜靜的小院裡,我們第二個真正的家裡,我的高原性病症痊癒了,我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記不清哪年,父母搬出了小院,搬到軍分割槽另一套房子,家寬敞了很多,除了客廳還有四間大住房。最讓我喜歡的是有一個大露臺,大露臺上面有屋頂,不怕日曬雨淋,無論春夏秋冬,都可以在露臺坐著觀星賞月。記憶深刻的是一個夏夜,我和父母坐露臺上聊天,不知從哪裡飛來幾隻蝙蝠,突然一隻蝙蝠啪一下掉在我頭頂上,正說笑的我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一下呆住了,坐一邊的爸爸一個箭步跨過來,一把抓住蝙蝠一轉身如投手榴彈一樣投出去,就這個幾秒鐘的動作,在我還沒有回過神時完成了。爸爸媽媽看我還傻傻地硬著脖子呆坐著,都笑起來,我卻一下哭起來了,邊哭邊說,好嚇人的蝙蝠掉頭上,笑什麼嘛。一個20多歲已當過兵的我,可以這樣在父母面前嬌嗔,這個事永難忘。
在這個大房子裡,大妹妹生了女兒後在這住了一個多月,爸爸下班後,常抱著小外孫女。有時我這個大姨看到孩子解便,一閃身溜了,顯臭,爸爸卻笑呵呵地幫著洗,那雙大手此時很輕很柔,爸爸臉上的笑容,我忘不了。
這個大房子的家,我在單位生病時就回來住,父母一定會為我做喜歡吃的汽鍋雞,燒排骨,炒燴麵。我生病住院,爸爸中午休息時,會把媽媽做的可口飯菜送到醫院,我在輸液,爸爸覺得我一隻手吃飯不方便,會一勺一勺餵我吃飯,這讓從小在保育院,八一校長大,又遠離父母在西藏當兵的我,感受到濃濃的父愛。不懂事的我,從沒想過爸爸上班的辛苦,只是心安理得的享受從小沒有多少印象的父愛母愛。
這個大房子,一直住到1981年父親離職休養搬到幹休所,我們姐妹平時上班,只逢年過節,或生病時才回到這個大房子,才回到這個家,這是我們真正意義住的第三個家,家的溫暖,對爸爸媽媽的依賴,爸爸媽媽給我們深深的關愛,永遠留在記憶裡。
1981年,爸爸離職休養,我們家搬到了幹休所,這是父母最後一次搬家,爸爸戎馬一生,終於放鬆休息了。剛離休時的爸爸,精力充沛,小院裡種植了葡萄,櫻桃樹,香椿樹,門前的小菜園,爸爸收拾得整整齊齊,隨季節種了很多菜,春天的韭菜,夏季的西紅柿,茄子、小辣椒、四季豆、絲瓜、冬瓜,秋冬的小白菜、蘿蔔,都是那麼的水靈,讓我們喜歡。週末或過年過節回幹休所的家,爸爸媽媽都會摘下地裡的菜讓我們帶走。春天的櫻桃、夏天的葡萄熟了,爸爸一定會親自爬上木梯為我們摘下水果,那時我和兩個妹妹的孩子都小,一看到爸爸摘水果,孩子們就會歡呼雀躍。我們給爸爸添了漁具,爸爸可以騎腳踏車快樂的去河邊釣魚,即便有時什麼也沒釣到,爸爸也樂此不疲。我們給媽媽買了風琴,那是媽媽參軍前在河南開封女子高階師範學校讀書時就會彈奏的樂器。媽媽讀書時,一個窮學生能學到的樂器,風琴、二胡、簫,口琴媽媽都會,媽媽參軍在十八軍文工團,她的吹拉彈唱,十分受歡迎。在幹休所的家裡,我們後來又給媽媽買了電子琴,媽媽會在樓上彈奏風琴,在樓下彈奏電子琴,有時還會吹口琴給我們聽,媽媽吹奏口琴是複音,非常好聽,我也跟著媽媽學吹口琴,可惜一直只能吹單音,很單調的聲音。那個小院,一直充滿歡歌笑語,孩子們的嬉笑打鬧,媽媽的琴聲,爸爸忙碌的身影,都留在幹休所的這個家裡。
隨著父母的歲數增大,爸爸又不慎摔了兩次,把腰和股骨摔了,爸爸的身體差了很多,走路需依靠柺杖,他再也無法騎腳踏車去河邊釣魚。小院裡的葡萄架拆了,櫻桃樹、香椿樹也砍了,小菜地也由照顧父母的家政人員隨意種,爸爸媽媽身體越來越不好,這時我因一些困擾,身體很差,爸爸媽媽又不顧年邁體弱,再次把我接回幹休所家裡,在家住了幾個月,慢慢調理身體和心情,我逐漸恢復了健康。和父母一起的日子,無論遇到什麼事,父母總會給我們很多的關愛。
幹所休的家,是全家在一起最長時間的家。我和兩個妹妹的孩子常回來,孩子們在這留下了成長的足跡,也讓他們留下了很多童年的快樂記憶。爸爸媽媽也由剛搬來時的年富力壯,逐漸衰老病痛,現在爸爸媽媽離開了我們,幹休所的家已沒有了歡聲笑語。逢年過節,我還是回到幹休所的家,對著爸爸媽媽的照片說話,我會潸然淚下,父母的音容笑貌會浮現在眼前,父母年邁時,蹣跚行走的背影,躺在床上病痛時的呻吟,我們姐妹輪流回來照顧年邁父母的情景,過年時家大門高掛的大紅燈籠……,一切一切、太多太多的記憶,都凝固在幹休所和父母在一起時間最長,也是我們最後的家裡。
時鐘記錄下我們和父母在一起的時光,細數那些點點滴滴的小事,那些平靜,普通的生活,女兒有許多想對父母說的話,有太多的思念深藏在心底,也有很多遺憾和內疚,撿拾起如碎片般的記憶,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永駐心間。
(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鍾建新:1969年12月拉薩入伍,曾在西藏扎木大站,西藏軍區第四野戰醫院服役。退役後,考入四川行政財貿管理幹部學院財會專業學習,從事財會工作,居住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