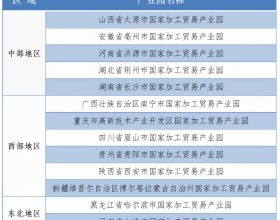俗語云:“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可秋天的螞蚱養得健碩碩、肥嘟嘟,一包子兒。早起郊外散步,我在菜園裡、草叢中捉了幾隻草蜢子,翠綠的身子、尖尖的頭兒,肥肥的肚子,一放手,蹦躂蹦躂逃脫了,模樣倒也有幾分可愛。
螞蚱是蝗蟲的俗稱,還稱為蚱蜢、草蜢,屬直翅目蝗科動物,種類繁多,全世界有超過10000種,我國有1000餘種,主要包括飛蝗和土蝗。飛蝗生得威猛,兩腿健壯有力,飛行能力強,代表性的即是鄉人稱作“蹬倒山”的紅螞蚱;土蝗以土黃色的小螞蚱和草綠色的稻蝗為主,專吃農作物的葉莖。還有一種尖頭長身的綠色螞蚱,稱作“草蜢”,我老家還叫做“草婆子”,長得貌似文靜秀氣,可吃起作物來一點也不客氣,尤以禍害菜園為甚,剛長出的菜苗經了它們一頓吞嚼,變得光禿禿的,一片狼藉。
這些在田野山間蹦蹦跳跳的小生靈,與野草野花、蜜蜂蝴蝶為伍,也能顯出些許小清新小可愛,古人的詩歌裡多有描述。春日裡,小螞蚱在淺草花甸輕躍,給人帶來溫暖的氣息。元末明初詩人錢宰曰:
霽日簷牙落,光風瓦上生。
草晴跳蚱蜢,花暖困狸狌。
——《春日閒居》
一幅春天的小畫兒裡跳躍出兩隻蚱蜢,多美啊!夏天,青翠翠的螞蚱和紅閃閃的蜻蜓還會擾人清夢。南宋詩人楊萬里說:“蚱蜢翅輕塗翡翠,蜻蜓腰細滴猩紅。”“黃蜂作歌紫蝶舞,蜻蜓蚱蜢如風雨。”到了秋天,蹦躂蹦躂的螞蚱沒有幾天好日子了,雖然如元代詩人方回所言“暗想田塍上,禾秋蚱蜢飛”,可終究耐不住霜凍嚴寒的打壓,“霜中蚱蜢凍欲死,緊抱寒梢不放渠。”一個個死翹翹了。
不過,螞蚱終究是農作物的一大害蟲,它分佈廣,食性雜,蔓延成災時見什麼吃什麼,不論作物、雜草還是樹葉,所到之處,一掃而光。可以說,古代一部農業史就是一部蟲口奪糧的滅蝗史。蝗災有多厲害?小時候,我聽太姥姥講起早年“起蝗”的情景,簡直是觸目驚心!“過蝗”之時,“旱蝗蔽土翳雲空,遙想驅馳逐轉蓬”,黑壓壓、亂紛紛,遮天蔽日,翻湧而來。若在屋簷下斜插幾支高粱穗,底下放一隻大號的泥瓦缸,頃刻之間飛蝗狂卷而至,吱吱嚓嚓一陣,成團成團滾落下來,不消多大功夫,泥缸裡落得滿滿當當。
古詩裡是怎麼描述的呢?宋末元初文學家戴表元寫有一首《蝗來》:
不曉蒼蒼者,生渠意若何。
移蹤青穗盡,眩眼黑花多。
害慘陰機蜮,殃逾蟲毒蛾。
秋霖幸痛快,一卷向滄波。
烏黑一片的蝗蟲數也數不清,罩得人眼花繚亂,頭昏目眩,青青的穀穗眨眼間成了光禿禿的秸稈,蝗蟲如魔鬼一般,吞卷千頃原野。明代軍旅詩人郭登也作《飛蝗》一詩,歷數蝗災的慘重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詩云:
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
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
官曹醉臥聞不聞,嘆息回頭望京闕。
該詩詩意淺顯直白,既描述了飛蝗的猙獰恐怖,又寫出了官吏的昏庸無能,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仰天悲號。
古人對蝗蟲驚恐至極,恨之入骨,連帝王都要生生吃了它。《貞觀政要》裡記述了一則“唐太宗吞蝗”的故事:“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duō)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蝗災爆發後,唐太宗到京郊視察農事,見到蝗蟲後咒罵蝗蟲與百姓奪食。當左右勸止他吃蝗蟲時,他表示願為人民承載災難,痛下消滅蝗蟲的決心,其為民情懷令我們歎服。
古人與蝗蟲的鬥爭可謂手法多樣,主要有焚燒、挖坑填埋、人工捕捉等。早在先秦時代的《詩經》裡,先民對蝗蟲危害莊稼就有了清醒的認識,主張運用火燒之法剿滅。《小雅.大田》中有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míng téng),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bì)炎火。”這是說:田裡的莊稼長勢良好,顆粒飽滿,沒有秕穀和雜草,豐收在望。可是像蝗蟲之類的害蟲要來禍害,啃吃還沒有熟透的作物,怎麼辦呢?田祖農神發號令了,那就用烈火把害蟲們統統燒死吧!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作有《捕蝗》長詩,描述貞觀之初蝗災的嚴重程度,“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諷刺各級官吏借捕蝗之名勞民傷財。在波瀾壯闊的滅蝗運動中,一些詩人也親臨一線,身先士卒。北宋大文人蘇軾在《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一詩中,生動記敘了捕蝗的經歷,他“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親自部署,親臨督導:
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
飛騰漸雲少,筋力亦已竭。
哪怕手掌磨出老繭,馬匹累得氣喘吁吁,大家都筋疲力盡,也在所不惜,“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只要解民憂、排民難,我們就盡職盡責,心中無悔。北宋詩人鄭獬的《捕蝗》詩中,記述了古人捕殺蝗蟲的方法,“鑿坑篝火齊聲驅,腹飽翅短飛不起。”這是挖坑填埋和燃火焚燒之法;“囊提籯負輸入官,換官倉粟能得幾。”這是官府以捕蝗獎糧的激勵之法,可謂多措並舉。更有意思的,是北宋“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在《花林示楊彭年秀才莎雞食蝗》詩中提及一種獨特的捕蝗之法,他說:
常嫌莎雞聒麥壟,紡車細掉喧晨昏。
莎雞可憐爾吻利,驅蝗逐蝻群披分。
大意是說:別看這些公雞母雞在麥田裡聒噪,可它們眼尖喙利,啄食蟲兒更強一籌,實為捕蝗能手呢。
不過,那種青綠色的螞蚱我們叫做“草婆子”的,古人倒是偏愛有加,把一種兩頭尖尖、船身窄長的小船,美其名曰“蚱蜢舟”“舴艋”。唐代詩人陸龜蒙詩曰:“岸聲搖舴艋,窗影辨蠨蛸。”善寫“漁歌子”的唐代另一詩人張志和詩云:“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晚唐的杜牧也說:“織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皆指像蚱蜢的小舟。更有宋代女詩人李清照的《武陵春·春晚》,低迴詠來,使我們記住了這舴艋小船還有美妙的詩意: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
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麼說來,小小的綠螞蚱還有幾分好處。
民國時期的汪精衛人品極差,小詩卻寫得不差,他有《山中即事》數首,其中一首寫道:
怡然相坐語,間亦恣遊戲。
小妹捉蚱蜢,荊棘創其指。
一笑釋自由,驚飛側雙翅。
聯想起小時候,我和小夥伴們常到田野裡捉螞蚱,我們可不憐惜它,絕不會“一笑釋自由,驚飛側雙翅”,扯了有韌性的稻棵或莠草,捉了穿起來,不一會就穿成一大串兒。拎回家讓大人放在油鍋裡,或煎或炸,黃燦燦、油亮亮一盤美味,吃起來酥脆脆、香噴噴,美著呢!
-作者-
劉琪瑞,男,山東郯城人,一位資深文學愛好者,出版散文集《那年的歌聲》《鄉愁是彎藍月亮》和小小說集《河東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