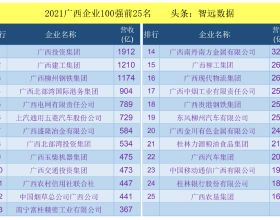鄒韜奮,原名恩潤,1895年出生於福建長樂縣一個破落的舊式官僚家庭。5歲時便在家讀私塾。1910年,入福州工業學校。兩年後進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附小,在此上中學並讀至大學電機工程科二年級。1919年,他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1921年,畢業後在工商企業和職業教育社任職。1926年,任《生活》週刊主編。
1936年,任全國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同年被國民黨政府抓捕成為“七君子”之一。1937年出獄後,他大力宣傳抗戰。翌年,應聘國民參政員。1941年,因受國民黨迫害出走香港。翌年初,從日軍鐵蹄下秘密潛渡到東江根據地,再輾轉進入華中新四軍軍部。1943年因病情惡化赴上海治療。1944年7月病逝,中共中央追認他為共產黨員。
在中國近現代文化界,享有盛譽的三聯書店(生活、新知、讀書出版社)是與其主辦者鄒韜奮的名字緊緊聯絡在一起的。毛澤東所寫的輓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對鄒韜奮一生奮鬥經歷的最好概括。
接手《生活》雜誌後六年,將發行量由兩千份擴大為十五萬份,創造了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的最高紀錄。受特務暗殺威脅出洋考察兩年,訪蘇後深受教育,對西方白人與黑人的對立等社會矛盾有了清醒的認識。
鄒韜奮從小在家讀經書十年,打下厚實的語文基礎。後來,父親想讓兒子當工程師,就送他上了南洋公學。進入大學的鄒韜奮讀的是電機工程科。由於對數學、物理全無興趣,鄒韜奮大學二年級時便轉到聖約翰大學文科。
這期間他的家庭破落,雖然每學期他都獲“優行生”而免繳學費,但鄒韜奮的生活費仍要自己籌措。為此,他寒暑假都當家庭教師,平時就到圖書館做夜班助理員,還經常向報紙投稿。因過於勞累幾次累得吐血。
大學畢業後,鄒韜奮到工商企業任職,幾年時間獲得了寶貴的經營知識。1926年,他在上海接手一個叫《生活》的小刊物,這個刊物連他自己在內只有兩個半職員(三人中有一個還在外面兼職),其銷量不過2000份。因付稿費太低難以對外約稿,主要由鄒韜奮輪換用六七個筆名撰文。鄒韜奮上任後創新編輯方法,避免使用貴族文字,“採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生活》將報紙和雜誌的優長兼顧起來,裡面都是一兩千字的有趣文章,以小市民、小職員等
“小人物”為物件答疑解惑,不到三年其銷量便升到4萬份。“九一八”事變後,《生活》雜誌又以疾呼救國的政論為主,訂戶擴大到15萬份,遠銷海內外,創造了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的最高紀錄。這一雜誌的稿費,又成為在國民黨文化“圍剿”的環境下許多革命文人維持生活的主要來源。
“九一八”以後,已成名人的鄒韜奮對國民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極為憤慨,改良政府的希望完全破滅。1932年,他加入了宋慶齡等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在雜誌上大量發表魯迅的文章。隱蔽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也對雜誌提出許多修改意見。
不久,蔣介石的嫡系軍官胡宗南“來訪”,與鄒韜奮爭吵了四個小時,隨後當局又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為由禁止郵遞《生活》雜誌。1933年夏,人權保障同盟的具體主持人楊杏佛遭暗殺,大家得知特務也把鄒韜奮列入黑名單,便力勸他出國避難。
此後,鄒韜奮環球旅行兩年,著重考察了西歐諸國和美、蘇。他看到了經濟危機下的西方有巨大貧富懸殊,也看到蘇聯的建設成就和青年的自由解放風氣(那時還未進行“大清洗”)。他後來說,以前對美國是有好感的,但是看到白人與黑人對立等社會矛盾及剝削者的貪婪,深感其腐朽沒落。他參加過美國共產黨地下支部的會議,並向旅美中共黨員提出了入黨申請。
因主張抗日救國,遭關押八個月才獲釋,此後在國民參政會的發言仍讓當局“討厭”拒絕成為中統特務頭子的“同窗”讓他參加國民黨的威逼,將周恩來當作最敬佩的朋友。
1935年鄒韜奮回國後,不顧威脅利誘繼續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翌年,他參加了組織救國會,將所辦的《大眾生活》作為救國會的機關報,結果被逮捕關押了八個月,成為轟動全國的“救國會七君子案”。
抗戰爆發後他得以出獄,為體現團結對外的精神接受政府之聘就任國民參政員。在參政會上,鄒韜奮的言論總是讓當局“討厭”,尤其是他調解國共摩擦,被要人罵為“國民黨請你當參政員,你卻為共產黨說話”。他主辦的書報又被“審查老爺”大量禁發,勉強透過的也經胡刪亂改,往往頁間充滿“被略”字樣,還造成文理不通和謬誤百出。
面對國民黨的高壓,鄒韜奮把希望寄於共產黨。到武漢後他向周恩來提出入黨申請,得到的回答是“現在以黨外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樣”。在重慶,他是“周公館”常客,周恩來也經常出席《生活》書店的茶話會。鄒韜奮臨終前曾說,周恩來是他畢生最敬佩的朋友。
從1939年起,國民黨在大力反共時加緊打壓社會輿論,一年多內生活書店在全國原有的56處分店只剩下6個。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係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
徐恩曾厚顏無恥地回答,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餘只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接著拂袖而去。
國民黨當局隨之將所剩的6個分店又查封了5個,留下的重慶一家店也岌岌可危。鄒韜奮為示抗議,憤然辭去參政員一職,擺脫監視化裝出走香港,在中共南方工委的支援下復刊了《大眾生活》。
日寇侵佔香港後由東江縱隊搶救脫險,此後化裝橫貫中國南部,到達新四軍軍部所在的蘇中解放區,準備去延安前被診斷患耳癌,秘密赴滬治療無效,留下遺囑請求中共中央追認自己入黨。
鄒韜奮到香港八個月後,1941年12月日軍便攻佔當地,他帶著全家躲進銅鑼灣的貧民窟裡。此時,中共南委接到延安關於搶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華的指示,派東江縱隊交通員接他內渡到根據地。
鄒韜奮原打算回重慶,卻得知國民黨特務機關已下密令,只要發現他便“就地懲辦,格殺勿論”,便暫留粵東遊擊區與戰士們一起住草棚,在山間密林中行軍轉戰。後來,周恩來考慮到鄒韜奮的安全,電示當地黨組織將他轉移到華中新四軍處。1942年9月,他化裝成商人,步行千里,透過國民黨和日軍的重重哨卡,經武漢到上海,再由交通員接到蘇中解放區。
進入了根據地,鄒韜奮感覺到了新天地。他同新四軍一起行動,考察抗日政權的活動,並在千人大會上講演,在盛讚建設的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一些缺點。他還打算北上遍訪各解放區,一直行至延安,再寫一本《民主在中國》。
然而,鄒韜奮的耳病日益嚴重,有時痛得打滾,經診斷是耳癌。當時,根據地沒有治療條件,只好派人秘密將他送往上海。毛澤東對此事也非常重視,黨中央專門致電華中局指示要贈送足夠的醫療費。
在日偽統治的上海,鄒韜奮就醫一年間用過四個假名,調換過五家醫院,仍在病床上強撐著寫下《患難餘生記》(可惜後一部分未及完成)。
1944年6月2日,自知快不行了的鄒韜奮留下遺囑,回顧了顛沛流離的一生,說明此次到敵後根據地視察,“看到新中國光明的未來”。他希望死後能將骨灰送往一直嚮往卻未能成行的延安,並請求中共中央追認自己入黨,囑咐夫人和鄒家華等子女要為偉大的革命事業做貢獻。7月24日他與世長辭,中共中央在弔唁電中滿足了追認為黨員的臨終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
周恩來曾說:“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生長於中國近代經濟最發達的江浙地區的鄒韜奮,其動盪的人生正是近代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在社會風浪中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也是由愛國主義逐步走向追求共產主義的典範。
與中國革命早期的前驅者不同,五四運動的風潮中鄒韜奮並沒有激進的表現,按他後來所說的,當時政治上“還很混沌”,“無所謂思想”,這與所處的貴族化大學環境以及江浙地區西式影響濃重的工商氛圍有關。鄒韜奮大學畢業後主張“振興實業”,雖對南京政府的腐敗不滿卻仍寄希望於當局“覺醒”。
1931年“九一八”的炮聲改變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和政治態度,包括江浙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階層民眾都紛紛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政策,站到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鄒韜奮又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他不僅改變了主辦《生活》週刊的宗旨,還進行環球旅行,對西方和蘇聯進行實地考察,從而實現了思想轉變,認識到共產黨人代表著光明的前途,並在近十年間一再提出入黨申請。
鄒韜奮雖然沒有能看到革命勝利便抱憾離開人間,但是他留下的書店卻成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重要奠基石。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做出的關於三聯書店的指示時,便高度評價了鄒韜奮的工作,並肯定說:“三聯書店與新華書店一樣是黨領導之下的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