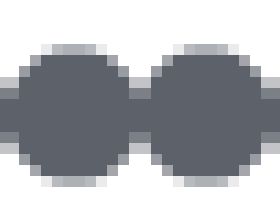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惟覺祭文多。2021年,年近七十的文化學者馬未都為了紀念故去親友,寫下了這部《背影》。短短十餘萬字,他不說文物,說人事;不說收藏,說人情。
1996年,馬未都創辦中國第一傢俬立博物館“觀復博物館”。時至今日,人們認識馬未都,往往以“收藏家”或“文化學者”的身份,鮮少知道他也曾有過一段在出版社做編輯的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二十歲出頭的馬未都調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成了全出版社“年齡最小、身份最低“的一名編輯。然而,這樣一位不受重視的小編輯,卻因一篇文章收到了大作家劉紹棠的親筆信。三十多年過去了,劉紹棠先生業已作古;在馬未都先生這篇真摯的回憶小文中,我們仍能讀到劉紹棠先生當年的那份赤子之心。
作家劉紹棠
文 / 馬未都
本文選自馬未都新書《背影》
今天的年輕人知道劉紹棠先生的恐怕不多了,這才過去幾年啊!當年紅極一時的紹棠先生中年而歿,走得太急且太早了,沒能看見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變遷。
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調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社會百廢待興,尤其文學界經歷“文革”的重創,一片凋敝。當時迅速復出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蒙、劉賓雁、從維熙、鄧友梅、劉紹棠、張賢亮等等,每個人都有轟動社會的力作。劉紹棠先生在所有右派作家中年齡最小,劃為右派之時年僅二十歲,一九七八年平反摘帽子時人剛到中年,四十一歲。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右派都是比爺爺年紀還大的人物,怎麼二十歲的人也能當上右派呢?
紹棠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一九五零年十三歲時就發表了作品,被譽為神童。當時的教育遠不及今天普及,罕見神童,他十四歲上高中時又連續發表了小說,其中《青枝綠葉》還被編入高中課本。一九五四年,他十七歲被保送北大中文系,他發現大學課程對於寫小說幫助不大,一年後就退學了,此舉給他留下了禍根,有作家認為他蔑視北大。雖然他後來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仍不能給他帶來福音。那時的作家協會會員算是一份殊榮,入會很難。
劉紹棠 1980年代 北京
一九五七年,二十歲的劉紹棠不知深淺地寫了些批評文章,加之又寫了兩篇有人不樂意的小說,一九五八年乍暖還寒時刻,他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一去二十年。對於右派,能否摘帽成為他們的心中之痛,一九六三年劉紹棠先生被摘去右派帽子,輕鬆上陣沒幾年,又爆發了“文革”,他識時務地自我流放至老家儒林村。
《蒲柳人家》發表於一九八零年,影響之大如同今日最紅的電視劇。街談巷議,人人在說《蒲柳人家》。我在文學編輯室,閱讀是必須的;《蒲柳人家》寫的是紹棠先生家鄉——大運河,今天已改區併成為北京城區了,想想都有趣。我小時候要去一趟通縣也算得動靜不小的出門呢!通縣人進城都說上北京。沒承想今天居然變成了城區,來去自由方便,一座城市也能給人暴發戶的感覺。
我喜歡文學的時候沒想過有機會能見到作家本人,到了出版社,看見那些原本印在書上的名字現在是活蹦亂跳的真人,很是讓我興奮了一陣。那時大作家都由大編輯接待,普遍都是成雙成對的感覺,別人插不進手。我耳聞目睹編輯們為搶作者爭風吃醋的事端,總是感到知識分子的可憐。當時我在全出版社年齡最小,身份最低,每天開啟水拖地是必修課,如同僧人修行。大作家來編輯部都會忽視我們的存在,跟我談得來混得熟的都是同齡作家,當時也都沒地位,因為經歷相同,溝通就容易。
編輯工作是我的主業,副業寫點文章補貼家用。那個年月的人是沒有外快的,拿死工資,按年齡大小發放,有本事的最多比別人多個十塊八塊,所以寫作勤快的人手頭總是富裕一些。可是稿費低,千字十元甚至八元執行了很長時間,寫個短篇小說弄個百八十元,長篇小說特難發表,周折也多,所以那時作家特願意寫中篇小說,發表後能得一筆算是像樣的錢。
我業餘時間寫了一箇中篇小說《記憶的河》,寫的是我在北京郊區農村插隊的事情,原來五萬餘字,發表時讓編輯砍去兩萬字,讓我對稿費心疼了許久。小說發表後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開啟一看,字寫得舒張大氣,落款居然是劉紹棠!大意是看了我寫的《記憶的河》,小說中描寫的那群知青與他在儒林村見到的知青一樣,希望我去找他聊聊天。信上留有他家的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光明衚衕45號。那天下班後,我懷揣著那封信,騎著車去見劉紹棠先生。
那是個夏天,晝長夜短,下班時太陽還老高呢!我上下班的方向東去西來,都迎著陽光,夏天的朝陽和夕陽唯一的不同是晚上熱點兒。我騎得一身汗,那時街上也沒有賣水的,直到找到劉紹棠先生的家,已渴成沙漠中的駱駝。
紹棠一身短打扮,和尚衫大褲頭,我進門後他先是大聲招呼,接著一陣震耳的大笑,一大壺釅茶馬上倒滿一杯,說:“先喝,正好喝,解暑。”我驢飲一杯,他馬上又倒滿一杯:“再來一杯。”直到我把壺中涼茶喝光,才話入正題。
劉家小院房子不多,院子還算寬敞,沒北房,在北京的四合院裡,北房算正房,沒北房的院子不能算好院子。院子裡有幾棵很粗很高的棗樹,樹上掛滿了青棗。過去住老北京的四合院,初夏的棗花香、入秋的打棗都是生活中極大的樂趣,所以魯迅先生寫自己的宅子時開篇就寫棗樹。棗子這東西不到日子沒法吃,無味還艮,但掛在樹上很耐看,尤其棗多掛在樹梢上,風吹時如小鈴鐺亂晃,煞是喜人。
紹棠先生身寬體胖,聲若洪鐘,一看就是那種口無遮攔的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這種人讚賞有加,但實際生活中這種人極易引起負面效果。我估計紹棠先生劃為右派就是因為這張嘴,不得罪事也得罪人,在中國得罪人也就算得罪事了,所以“最年輕的右派”帽子就扣在了他頭上。福禍相倚,因為禍,劉紹棠先生又返回了生他養他的農村。一去就是二十年,而這二十年又讓他得一福,能讓他寫出《蒲柳人家》等多篇鄉土文學。紹棠先生掛在嘴邊的話就是“為我那粗手大腳的爹孃畫像”。
我就是個直來直去的脾氣,紹棠先生更直來直去,我們爺倆相談甚歡。他問了我插隊時的情景,並說他們村的知青和我筆下的知青簡直一模一樣,我記得他說了一句:離開爹孃的孩子都成熟得快。我告訴他我一個軍隊大院長大的孩子離開父母去農村當農民的內心感受。那天,紹棠先生留我在家吃了飯,光顧說話了,把吃的什麼忘得一乾二淨,也不記得喝了酒沒有,反正直到午夜,我才從他家的小院走出,騎上車哼著小曲回了家。
今天的人不知什麼時候都變得勢利起來,凡事無利不起早。過去的苦,日子雖苦心裡卻甘,是因為每個人內心乾淨。內心乾淨是個多麼難得的人生狀態啊,只有丟了才覺得寶貴。我的前半生心裡從沒有不乾淨的時候,朋友之間即便吵架,都不過夜就煙消雲散了;可今天,社會的場面上,每當有人和你勾肩搭背之時,你都可以感到在他心裡藏著其他目的,明明在算計人,可嘴裡仍抹了蜜,說著連自己都不信的甜言蜜語。可那年月沒有,我也不會恭維紹棠先生,紹棠先生也不會居高臨下與我交往,所以一見如故,沒有開場白,沒有客套話,也沒有請客送禮的概念,一切順其自然。
那年我三十左右,劉紹棠先生五十歲上下,雖然年齡差不大,但人生經歷相差太多。“反右”的腥風血雨,“文革”的風捲殘雲,在他們那一代人心中都留有清晰的烙印,永遠伴隨著他們的人生。而我,“反右”“四清”是聽說的,“文革”在我眼中只是半個,童年時代經歷“文革”所理解的最多是一半,儘管我在農村待過兩年,但與農民對農村的感受還差著十萬八千里。紹棠先生成長在北方農村——儒林村,一條流淌的大運河不僅僅從村中穿過,更重要的是從他心中穿過,所以他的鄉土小說特別引人入勝。
可惜紹棠先生走得太早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劉紹堂先生已經臥床多日,由於積勞成疾,年僅六十一歲溘然長逝,按他的好友作家從維熙先生的話說,“劉紹棠六十一歲去世,成為我們這代人心裡難以彌補的傷痛。”我何嘗不是呢?我雖和紹棠先生僅幾面之緣,但他父兄一樣率直的性格、豁達的人生態度給予了我強烈的感染,讓我們晚輩有機會可以重新審視人生。所以我從不抱怨年輕時插隊的苦難,吃不飽穿不暖睡不熱都是人生的磨礪,都可以轉化成人生的財富。
寫此文時我翻遍了書房,也沒有找到紹棠先生當年給我的親筆信。在這個不知哪天進入的電子媒體時代,一封手寫的信多麼重要啊,況且是一個大作家無緣由無訴求地給一個無名的小編輯寫的充滿了情感的信,在那信中,有他的熱情與期盼,有他的情感表達與流淌,還有他那看不見的赤子之心;而對於我,三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劉紹棠先生龍飛鳳舞的字跡,記得那份讓我沒來得及親口道謝的恩德。
2016年2月15日 觀復博物館
×
馬未都丨《背影》丨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