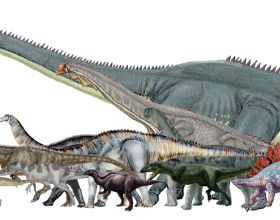“這腮上薄薄的酒暈,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豔;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
丈夫酒後對妻子略顯造作的讚美,並未激起妻子心中的漣漪,反倒令同樣微醺的她,藉著酒意,提出了想要當著丈夫的面“出軌”的請求。
盛宴結束,妻子採苕醉眼朦朧地望著那個想要親吻地沉睡中的“俊俏臉龐”,她告訴丈夫,只需要一秒鐘,如果不能夠親吻他,她總是不會舒服。
這是一個完全沉浸在醉意中的荒唐故事,儘管妻子在臨近越線,親吻另一個男子的最後時刻“幡然醒悟”,但戛然而止的結局卻令所有人都感到如鯁在喉。
這段充滿了醉意的故事,出自民國才女凌淑華的短篇小說《酒後》。
在思潮激盪的民國初期,《酒後》的發表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更是讓凌淑華在那個文人輩出的年代一夜成名。
有人說,要想了解一個作家,就要從她最荒唐的作品開始,因為那裡往往隱藏著她鮮為人知的心緒,《酒後》於凌淑華來說,便是如此。
1900年,凌淑華出生於北京的一個名門望族,父親凌福彭從清末到民初,一直都是政府高官,因此凌淑華自小便過著富足自在的生活。
對於凌家的大宅院,凌淑華曾在小說中這樣描述:“說不清到底有多少個套院,多少間住房,我只記得獨自溜出院子的小孩經常迷路。”
凌家的富足從中可窺見一斑,凌淑華雖是女孩,又是庶出,但在凌家眾多的孩子中,她是最聰明伶俐的一個。
由於父親喜愛繪畫,家中常與書畫大家有所往來,凌淑華自小耳濡目染,對繪畫亦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父親特意聘請名師教她學畫。
不僅如此,凌淑華還得到過民國“怪才”辜鴻銘的指點,在中外古典文學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新文化和新思想如暴風雨般席捲中華大地,在求新求變的思潮下,凌淑華也加入了追求自由和女權的大潮中。
22歲那年,凌淑華考入燕京大學,專修英法日等語言文學,自此專注於寫作,併為各大報刊投稿,開始展露出驚人的文學天賦。
可以說,凌淑華是民國時期真正少有的才女,她的文字善於表現對女性細膩心理的刻畫,被沈從文、徐志摩等大家譽為中國的曼殊斐爾。
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凌淑華作為陪同人員,與胡適、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人組成接待團。
從接待團的名單中可以看出,能夠進入接待團的人絕非等閒之輩,尤其是當中屈指可數的女性,在當時,凌淑華的才情絕不在林徽因之下。
也恰是在這個接待團中,凌淑華遇到了那個令自己糾葛一生的男人。
彼時,徐志摩對林徽因的追求雖被佳人所拒,但他並不死心,為此還請求泰戈爾幫忙在林徽因面前美言,儘管如此,林徽因依舊不為所動。
徐志摩黯然神傷,泰戈爾卻不以為然,林徽因固然才貌雙全,卻並非獨一無二,在泰戈爾看來,有個人的魅力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
於是,在泰戈爾的牽線下,性格開朗幽默的徐志摩很快便和凌淑華打得火熱,徐志摩更是驚奇地發現,凌淑華似乎比泰戈爾說的還要優秀。
在他的眼中,凌淑華不僅有著驚人的繪畫天賦,文章更是溫婉清幽、獨樹一幟,這樣的女子無疑對徐志摩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
此後,徐志摩與凌淑華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徐志摩曾對她做出這樣的評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
徐志摩平生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便是凌淑華的小說集《花之寺》,可見凌淑華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
儘管如此,凌淑華卻始終與徐志摩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這令徐志摩備感苦惱。
雖然對徐志摩的才華欣賞不已,但聰慧伶俐的她又怎會不知,徐志摩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凌淑華始終對現實有著超乎常人的清醒的認知。
果然,不久後陸小曼的出現,又令徐志摩春心蕩漾,對其展開了瘋狂的追求,讓人不得不佩服凌淑華看人的獨具慧眼。
其實,凌淑華之所以沒有與徐志摩走到一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她的心裡還裝著另一個男人——陳西瀅。
當時,關於泰戈爾訪華期間的接待宴會,接待團覺得在北大食堂太簡單,在大飯店又顯得俗氣,思來想去最終將接待宴會定在了凌淑華家。
凌家不僅寬敞氣派,又有中國傳統宅院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凌家是書香門第,接待這樣一位大文豪最合適不過。
而接待泰戈爾的負責人,正是時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的陳西瀅,在接待宴會中,凌淑華不凡的談吐與氣質給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後來,二人便有了書信往來,他們時常討論對文學、繪畫和時事的看法,陳西瀅的踏實讓凌淑華覺得心安,兩顆蠢蠢欲動的心越走越近。
隨著小說《酒後》的發表,凌淑華的名字轟動了整個文壇,陳西瀅更是被她不同凡響的才情所驚豔。
於陳西瀅來說,他從未接觸過如此奔放灑脫的女子,凌淑華對愛情和自由的嚮往,深深感染著他。
儘管彼時的凌淑華與徐志摩亦是書信頻繁,但凌淑華清楚地知道,對徐志摩是才華的欣賞,而對陳西瀅是情感的寄託。
1926年,陳西瀅與凌淑華走進了婚姻的殿堂,才子佳人無疑是令人欽羨的結合,婚後二人一起赴日蜜月。
不能否認,再危機四伏的愛情,婚後最初的時光也是幸福美好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婚姻會將彼此不曾瞭解的缺陷全部暴露出來。
陳西瀅希望妻子在婚後能夠將重心放在家庭,而對於畢生追求自由解放的凌淑華來說,她又豈是一個甘願為了家庭而放棄自我的人?
很多時候,男人希望女人可以為家庭放棄一切,但卻從沒有想過,當初之所以愛上她,恰是因為她對自由的嚮往。
夫妻因公來到武漢大學後,生活習慣和性格的矛盾越來越大,一點一點吞噬著看似光鮮亮麗的婚姻,代替“彼此欣賞”的是“互相埋怨”。
據女兒陳小瀅回憶:“母親顯然不甘心扮演那種傳統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個女人絕對不要結婚’,這句話我不知聽了多少遍。”
在陳小瀅看來,陳西瀅與凌淑華的結合,都是奔著彼此想象中的美好而去,他們許配給了彼此幻想中的愛情,而並非彼此。
誠然,如果愛情不能落實到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這些實實在在的生活瑣碎中去,是不容易天長地久的。
這時候,一個英國詩人的出現,打亂了凌淑華隱忍的生活,朱利安是武漢大學的外籍教師,在被陳西瀅邀請到家中做客時,與凌淑華相識。
令陳西瀅始料不及的是,將朱利安帶到家中無異於引狼入室,這一次見面居然促成了日後妻子的“紅杏出牆”。
一個空虛寂寞的女人,一個浪漫詩意的男人,愛情的到來從來就不需要過多的贅述,像是飛蛾撲火,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團抖動的光亮。
凌淑華對朱利安說,她的婚姻沒有愛情,是為了結婚而結婚的,她不會再相信愛情,但是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熱烈和真切,她卻放棄了抵抗。
就像《酒後》中的妻子,儘管丈夫讚美的詞藻紛華靡麗,採苕卻不能對發自內心深處的情慾置若罔聞。
不得不說,作家與其他門類的藝術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藝術家需要自我催眠,需要忘記殘破的現實,只專注於美。
而作家則會時刻保持清醒,即便偶爾醉眼朦朧,身陷內心掙扎的囹圄,仍要住在用自身殘缺搭建的監獄裡。
《酒後》就是她深埋在內心的監獄,每一根鐵欄杆上都寫著忠貞教養,被囚禁的卻是一顆追求個性解放的活生生的心。
然而,越是內心清醒,那如死水般的婚姻就越是令人恐慌,她不得不為自己找到一個出口,哪怕等待她的是一團火,她也要撲過去。
對於愛情,凌淑華從來不需要掩飾,她開始穿上美麗的旗袍,燙了時尚的捲髮,塗上鮮豔的口紅,去迎接那個活在當下的愛情。
她以探望恩師為由,帶朱利安回到北平遊山玩水,大方地向朋友介紹自己的情人,她在享受這一刻的無比自在,似乎浪費一秒都是罪過。
小說中溫婉賢良的妻子,似乎不再有醉意,此刻的採苕無需一遍遍央求著丈夫滿足自己離經叛道的要求,她已真切地吻了那張俊俏的臉。
然而,在一番放肆的歡快過後,凌淑華卻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悲哀。
北平的夜空繁星點點,每一顆閃爍的光都像是蚊子叮在傷口上,說不清是疼還是癢。
曾經的篤定,如今的背叛,疊加在燈火昏暗的街頭,此刻,她像採苕一樣微醺著,這世界彷彿顛倒了過來,人在蒙著星辰的黑色天空上走。
街頭拐角猛然出現的霓虹燈,朦朧刺眼,像酒後的涼風一樣醉人,她想在這一刻死去,永遠不要醒來。
對於凌淑華在北平的“招搖過市”,陳西瀅耳聞後憤然不已,回到武漢後,等待凌淑華的無疑是一場暴風驟雨,此事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後來,冷靜下來的陳西瀅找到妻子,讓她在自己和朱利安之間做出選擇,凌淑華並未多做考慮,她決定與朱利安分手,迴歸家庭。
而彼時的朱利安迫於輿論壓力,已從學校辭職,在給凌淑華留下一封告別信後,徑自返回了英國,回國後的朱利安很快便開始了新的戀情。
其實,凌淑華何嘗不是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局,如今的朱利安不正是當初的徐志摩麼?這世界沒有變,變了的是自己。
如今回想起多年前《酒後》剛剛發表時,魯迅先生對凌淑華的點評,莫不是一語成讖,真真地預言了她的婚姻生活:
“她大抵是謹慎的,適可而止地描寫了舊家庭中婉順的女性,即使有出軌的舉止,那也因為偶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回覆了她的故道。”
誠然,小說中展現出的酒後人物的醉意和醉態,本身就是一場和現實世界的角力,有時皆大歡喜,大部分的情況卻是兩敗俱傷。
在男權社會所規劃的社會秩序中,女性始終被賦予了理想化的“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而長時間對於這種理想化的認可和讚美,也令她們主動甘願接受這樣的命運安排。
儘管我們在《酒後》中看到了一個女子本我與自我的激烈鬥爭,儘管採苕一再祈盼一次偶然的叛逆,儘管凌淑華的紅杏真的開出了牆頭。
但那杏花的根脈終是邁不出人倫道德的高高的院牆,當激起漣漪的那粒石子沉入湖底,湖面究竟是要恢復原有的平靜。
然而,沒有人知道,在看不見的暗流之下,那粒石子終會被腐蝕被衝擊,然後變成針變成刺,深深地紮在柔軟的糜爛的心底。
重新迴歸家庭的凌淑華,並未如願與陳西瀅和好如初,結疤的傷口雖然不再疼,卻會永遠烙在心裡,何況他們之間的裂痕不止如此。
除了生活瑣事上的格格不入,凌淑華與婆婆之間的關係更是劍拔弩張,巨大的觀念差異,讓她在面對整個家庭時都身心俱疲。
女兒陳小瀅在回憶起幼年的家庭時說:“母親與她們合不來,也會和父親吵,從家庭出身、生活習慣到語言都有矛盾。”
不久後,凌淑華的母親去世,凌淑華藉機帶著女兒回到北平,開始和陳西瀅過著“非正式”的分居生活。
於凌淑華而言,她對家庭有著世俗的心理上的依賴,然而切實的生活又讓她望而卻步,這種“非正式”的分居,對她來說算是暫時的解脫。
後來,陳西瀅因公赴英國上任,凌淑華再無理由留在北平,只得帶著女兒一同前往歐洲,儘管如此,來到英國的他們依舊分房而睡。
為了填補自己空虛寂寞的內心,凌淑華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繪畫和文學創作中去,忙碌的生活令她暫時忘卻了婚姻的傷痛。
夫妻二人似乎都滿足於這樣的婚姻生活,沒有一別兩寬,卻也各自安好,任憑時光飛逝,彷彿都在祈盼自己的生命可以短一些,再短一些。
轉眼暮年,在旁人眼中,他們是相敬如賓的夫妻,恩怨情仇彷彿也淹沒在歲月的塵埃裡,每每想起,一切似乎變得沒有那麼重要。
1970年,陳西瀅在倫敦病逝,“非正式”的分居變成了“正式”的孤獨,曾經那個追求個性、風華絕代的才女早已不知所蹤。
此刻,空曠的房間裡,只是一個沉默的老人,日復一日,用不羈的青春過往,果腹著自己日漸頹靡的靈魂。
在晚年寫給好友冰心的書信中,凌淑華這樣寫道:
“我真想立刻飛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頭悲慼,我在此一肚子苦惱,誰也不要聽,只好憋著氣,過著慘淡的時日。”
1989年底,凌淑華終於回到北京,回到了承載著童年與愛情的宅院,那些喧鬧的身影似乎還在,他們的聲音、表情、呼吸彷彿觸手可及。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時光遲暮,人生不返,她孱弱的軀殼和靈魂,也將隨著北京的一年一度的春風,就此消散。
1990年5月,凌淑華在北京病逝,家人幾經輾轉,將陳西瀅的骨灰從英國運到國內,同凌淑華一起葬在了無錫陳家的祖墳。
無論陳西瀅與凌淑華是否情願,他們終是永遠地在一起了,曾經的青春、不羈、情慾,於愛情來說,卻都不及這死亡來的篤定。
就像丈夫對採苕說:“如此人兒,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讓我享至”,卻終究是一個醉意朦朧的不真實的世界。
不得不說,有時候,情慾只是一種“當下的情緒”,如果有人錯將這份情緒當做愛情,那是本身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