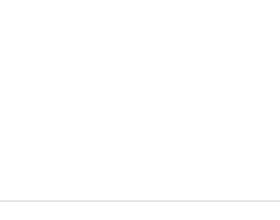《昭明文選》 資料圖片
《昭明文選論考》 力之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近捧讀當代“選學”研究的重要學者、廣西師範大學教授力之的《昭明文選論考》(獨秀學術文庫之一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版。後徑稱《論考》),筆者謂此書堪稱《文選》研究的扛鼎之作,有著重大的學術貢獻,是該研究領域最新進展的優秀成果,且為並世研究該門學科樹立了邏輯方法論的標杆。是書與其著者,誠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先唐文學研究與經典解讀”專案首席研究員範子燁在《序》中所說:“在我們的時代有如此優秀的學術著作出現,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而擁有力之這樣的學者,更是我們時代的奢侈”;“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書亦非一世之書”。
如何更好地推進當代《文選》研究,使之躍上一個更高的平臺,而不是在一個低層次上打轉?力之教授是書對此給出了精彩的回答與詮釋。筆者讀之如飲醍醐,啟發與感觸良多,特別是其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所取得的成就。這不禁使我想起湯炳正(景麟)先生的一句話,即“真正的科學結論,往往是看準穴道,一針見血,經絡通暢,手到病除”。
《論考》所收25篇論文(36萬字),皆系著者近20年來發表在《文學評論》《中山大學學報》《古典文獻研究》等刊物上的。全書析為三編:上編《關於成書及分類研究之方法問題》;中編《編者及編撰的其他相關問題論考》;下編《作品諸問題論考及其他》。
我向來以為邏輯思維(思想方式與洞察力)是學術研究的靈魂與命脈,亦可以說是利器。問題是,現在不少論著恰恰是不講邏輯的,甚至是自說自話,從而致使其結論往往是人云亦云,甚至漏洞百出,完全經不起推敲。說嚴重點兒,這樣的文字可謂禍棗災梨。在筆者看來,力之先生是當今《文選》研究領域為數不多的非常重視方法論而以邏輯思辨能力見長的標誌性學者——王立群先生在其出版於2003年的《現代〈文選〉學史》中曾說:“力之是一位介入《文選》研究較晚卻極有特色的研究者……其文甚重思辨,對諸史的用語極為講究。”如其在本書中提出並具體運用的“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等研究方法,將會給文史與文獻研治者以思維上的啟迪,從而推動與促進相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是書佳例甚夥,這裡不一一列舉,僅以其《關於〈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一文為例而略說之。著者認為,學界對《文選》成書“相關方面的研究存在著不少問題,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對學術研究而言,文獻的支撐與研究方法均是至為重要的,然後者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今僅就‘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等四個方面展開探討。一者,以期對《文選》成書研究的推進有所助益,進而能對相關學科的相關研究有所啟迪;二者,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者們對研究方法有更多的關注與進一步之重視”。
在第一個問題“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中,又分為“跳出《文選》以究其編纂工作量之大小”“用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選》的成書狀況如何”“用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選》編者及其相關問題”;在第二個問題“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中,又分為“以古還古以究《文選》的成書狀況”“關於《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的是非問題”“關於李善因某題名與‘集’異而謂其‘誤’的問題”;在第三個問題“將相關問題置於文獻可信度的層面上考察”中,又分為“從文獻可信度的層面上考察《文選》編纂過程之‘兩階段’說”“對前賢時彥之說,先驗其所據文獻有無問題”;在第四個問題“從情理:邏輯的層面上考察”中,又分為“關於選文標準的問題”“關於《文選》的性質:從是私人編纂還是官書性質的角度看”。統而言之,從上面所舉之例看,著者治學甚有獨到之處,觀此或不難體會到其何以能在《文選》研究上取得那麼多歷史性的突破與貢獻。但是著者這些方法還遠沒有得到學者們應有的重視。我以為忽略這些方法的研究,其結果往往確“似是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自當明之”。
我們知道,關於《文選》的編者,姚思廉的《梁書》與李延壽的《南史》均說是昭明太子,而略晚於姚氏、與李氏大致同時的唐人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及其後的宋人《中興書目》則分別有“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說與“(蕭統)與何遜、劉孝綽等撰集”《文選》之注。據此,著者從七個方面進行了精審的考證,其結論雲:“唐代的‘選家’如李善、‘五臣’(包括呂延祚)等無一家同《古今詩人秀句序》與《中興書目》說者,此其一;其二,唐‘景龍’(707—710)時人吳從政‘刪宗懍《荊楚歲時記》’等書而來之《襄沔記》有‘襄陽有文選樓,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說等,然‘此齋’與蕭統‘造《文選》’毫無瓜葛,其雖生於襄陽,卻數月後便‘隨母還京都(建康)’,故‘於此齋造《文選》’云云可謂是‘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的……其四,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一類出於眾門客之手的書,史家或注家均有說明;其五,《梁書·劉孝綽傳》說‘太子文章繁富,群才鹹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而此‘集’易被誤作《文選》;其六,《梁書·昭明太子傳》之‘(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說,其與太子集‘才學之士’編纂《文選》非為一事;其七,略加比觀《文心雕龍》與《文選》,便可推知無論是工作量還是難度,前者均大於後者,即就《文選》編纂工作量言,昭明太子憑一己之力可完成,等等。總之,用就整體考察部分的方法對《文選》編者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考察,其結論才會經得起推敲,堅實可信。”而這正如著者在《關於〈文選〉篇題和卷目的差異與其文獻價值問題》一文的“結語”中所說:“將‘問題’置於‘網路’中考察”,而非“看到‘線上’的某一現象便匆匆下斷語”。
“關於《文選》編纂工作量的大小如何,於史無證”,而“由於是書收錄了自周至梁近千年的130餘位作家之700餘首詩文,且史載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故在不少研究者那裡,首先想到的便是其非有個‘編纂班子’不可。於是,自然而然地出現了諸如‘昭明十學士’說、‘選樓諸子’說,等等。”對此,著者採用跳出《文選》來考察《文選》之法,並藉助部分小於整體之“公理”,將本無可比性的詩文選本《文選》與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作了切實的比較。他說,完成《文選》的“‘工程’還遠不如完成《文心雕龍》中的論文體部分及《辨騷》與《才略》這22篇的大”,而“劉勰之完成《文心雕龍》只花四五年的‘業餘’時間,非傾其數十年的心血”,故“就《文選》編纂的工作量及其實質性言,昭明太子憑一己之力完成是書並非什麼難事”。又說:“僅就《文選》本身來考察其工作量大小,從研究方法的層面上說,無論如何均恐為思之未周所致。明乎此,便可知未考察《文選》的編撰工作量如何,就將一定的時間範圍內之某年東宮進多位學士一事與太子編纂《文選》掛起鉤來,恐未免失當了。”著者的結論是,“《文選》乃正常完成之書,非倉促所就,而其編纂,則出於昭明太子一己之手”;“合‘顯內證’與‘潛內證’觀,《文選》之分類原本只能是‘三十九類’”,等等。這些結論,或言前賢之所未言,或屆時彥之所未至。按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說法就是,“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
著者的“從出發處辨路向,就《文選》本身考察”“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說,我從日常生活到讀書治學方面皆有深刻的體會。兒時第一次隨家父上街,見公交車來了便激動地往上衝,家父忙拉住我說,你先看清楚這車是不是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再上好不?如坐錯車,結果如何可想而知。這件事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自那以後我特別注意“辨路向”,所以在我的潛意識中和《論考》的觀點與方法產生了強烈共鳴。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影響最深廣的一部詩文總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論考》著力解決的是“選學”中之難題,而由於著者研究之得法與對相關文獻理解之準確,因此能在一系列問題上得出精當的創造性結論。
(作者:湯序波,系貴州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