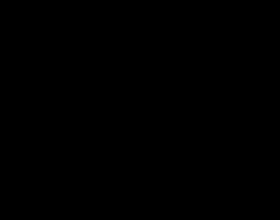清華簡八《虞夏商周之治》僅3支簡,共104字(含重文1處)。原無篇題,由整理者據文意擬定。該篇多涉上古三代禮樂制度,相關內容可與《墨子·三辯》《韓非子·十過》《淮南子·齊俗訓》《儀禮·士冠禮》及《禮記·明堂位》等文獻合觀。自簡文刊佈以來,學界對其主旨及性質探討歧說紛然,未有定論。
為便於討論,現將整理者釋文迻錄於下,個別字詞釋讀參考諸說,擇善而從。其文曰:“曰昔有虞氏用素。夏後受之,作政用俉,首服收,祭器四璉,作樂《羽籥》九成,海外有不至者。殷人代之以三,教民以有鬼畏之,首服作冔,祭器六簠,作樂《韶》《濩》,海內有不至者。周人代之用兩,教民以儀,首服作冕,祭器八簋,作樂《武》《象》,車大輅,型鍾未棄文章,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
批判禮樂與節用裕民
整理者認為,本篇以虞夏商周禮樂由樸素走向奢華,以致從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內有不至者”,再到周代的“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闡發崇簡戒奢的治國思想(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中西書局2018年版)。王寧進一步指出,其目的在於表述一種財用觀念(《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治〉財用觀念淺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8年9月26日)。馬文增提出不同觀點,認為簡文意在以虞夏殷周為例項而言治天下之道有“變”與“不變”之理(《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六題》,《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相較而言,前兩說更為妥帖,因為節用裕民是清華簡治道理念的重要內容,在其他篇章中亦多有體現。如清華簡六《管仲》桓公問管仲施政之道,管仲答曰:“斂之三,敷之以五,其陰則三,其陽則五。是則事首,惟邦之寶”;清華簡八《治邦之道》主張慎用民力,“度其力以使之”“資裕以易足,用是以有餘,是以敷均於百姓之兼利而愛者”;清華簡九《治政之道》批判在位者“聚厚為徵貸,以多造不用之器,以飾宮室,以為目觀之無既”。
在節用裕民舉措中,儉省禮樂祭祀又是重要內容。如清華簡八《邦家之政》所述“邦家將毀”諸多緣由,其中就包括“其宮室坦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縟,其禮採,其樂繁而變,其味雜而齊,其鬼神庶多,其祭拂以不時以數”。清華簡八《治邦之道》亦提到“不厚葬,祭以禮,則民厚”。不過僅就禮樂器服而言,《虞夏殷周之治》節用主張的針對性更強,其他簡文除批判禮樂繁縟外,還涉及宮室、飲食、服飾等日常奢靡之費。
以史為鑑 虛實結合
《虞夏殷周之治》並非直接批評時政,而是以史論政,這繼承了西周的史鑑傳統。就目前刊佈的清華簡來看,很多篇目都蘊含較為濃厚的史鑑意識。如清華簡一《祭公》“嗚呼!天子,鑑於夏商之既敗”;清華簡二《系年》“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清華簡五《殷高宗問於三壽》“診夏之歸商”;清華簡九《治政之道》亦云“昔夏後作賞,民以貪貨;殷人作罰,民以好暴。故教必從上始”,“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儘自失秉”,“遠監夏後、殷、周,邇監於齊、晉、宋、鄭、魯之君”。但《虞夏殷周之治》呈現的是虞夏殷周“四代”史觀,這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傳世典籍中較為常見。
不過,《虞夏殷周之治》有關“四代”表述並不一定符合歷史真實。簡文提到殷人“作樂《韶》《濩》”。“作”有始作之意。但實際上,“韶”並非殷商時作,而是虞舜之樂。《竹書紀年》即提到帝舜有虞氏“作大韶之樂”,《說文解字》亦云“韶,虞舜樂也”。至於《韶》與殷商的關係,傳世文獻多記述為商湯因循韶樂。如《墨子·三辯》商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呂氏春秋·古樂》“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簡文作者言殷人作《韶》,或為了與夏“作樂《羽籥》九成”、周“作樂《韶》《濩》”相對,追求句式齊整而混言之。
道乎?墨乎?
至於《虞夏殷周之治》學派屬性,目前主要集中在道家與墨家兩端。石小力指出,簡文反映了道家崇儉戒奢的治國思想(《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尉侯凱認為,簡文與墨家節用尚儉的思想更為切近(《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補釋一則》,《簡帛》第2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前說似將簡文“素”字與道家見素抱樸思想相聯絡;後說則認為簡文與墨家節用、非樂等主張相契合。兩種觀點的論據都不夠充分。尚儉節用是夏殷週三代以來的政治傳統,為當時諸子普遍接受的共識。因而由尚儉節用很難判斷文獻的學派屬性。
但這是否意味著簡文性質難以確定?並不盡然。若從《虞夏殷周之治》對禮樂的認識與態度著眼,或有新的認識。簡文所述夏殷週三代禮樂制度多見於儒家禮類文獻。如簡文提到的夏“首服收”、殷商“首服作冔”、周“首服作冕”,與《儀禮·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相參看。其中,“首服”指稱冠戴服飾,可與《周禮·春官宗伯》“其首服皆弁絰”相聯絡。再如,簡文提到的夏“祭器四璉”、殷商“祭器六簠”、周“祭器八簋”,可與《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合觀。
由此不難推斷,簡文作者對儒家禮儀及其經典較為熟悉,不排除為儒士的可能。但簡文將禮樂作為批判物件,又不能體現出儒家注重禮樂的特質。這兩者是否相互矛盾?其實,簡文作者可能是荀子所謂“俗儒”,他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以至於“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荀子·儒效》)。因此,簡文很可能由儒家“繆學雜舉”一派所作。他們不固守禮樂圭臬,能夠圍繞現實政治需求,對禮樂有所損減。如此,上述所謂矛盾之處即可得以解釋。
該篇雖簡短,但末簡有絕止符,內容較完整。賈連翔稱,在清華簡未公佈的篇目中還有一部分竹簡與《虞夏殷周之治》篇的編痕、契口及竹節位置相同,劃痕也可貫聯,推測可能屬於這卷竹書(《戰國竹書整理的一點反思——從〈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三篇的編聯談起》,《出土文獻》第13輯,中西書局2018年版),《虞夏商周之治》很可能是一卷竹書中的一部分。此外,簡文篇幅太短,又以“曰”起句,並未提及論述具體物件。因此,該篇單獨成篇可能性較小,似可將其視為某篇的一部分。如此,“曰”前無言說物件之由即能得以解釋,或因承前省略,又或前有相關指稱,但尚未發現。唯有待簡文篇卷明確後,方可對其文字性質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