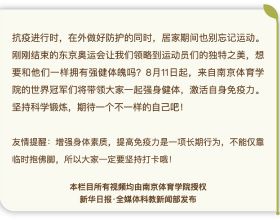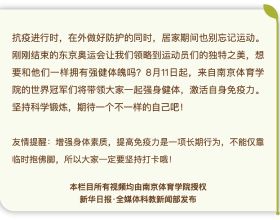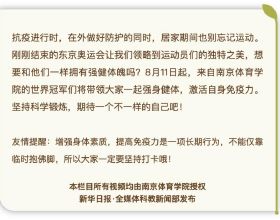Original 江 丹 新三屆2
作者簡歷
江丹,北京33中老初一,1969年4月15日內蒙兵團開建後抵達巴彥綽爾盟的第一批知青。先在一師直屬連,後調師醫院。一直努力自學補充中學教育,75年上了北京中醫藥大學,又繼續讀了兩個碩士研究生,在校任教。1991年赴英國,中醫學者。
大學,在我去生產建設兵團時,是完全沒有想到過的。
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我剛剛進入初中一年級。在初一都還沒有結束的某一天,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我們不得不中斷學習,按照偉大領袖指引的方向投入到“革命”的運動之中。對剛剛14歲的我,對這場革命的方式,前景,意義都根本無法理智地思考,參加宣傳隊,跳舞唱歌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69年初春,我們被分配了。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我的歸宿。可在那時,我沒有選擇:作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代表李維漢的“黑干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父親被批判,被審查;父母工作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因為當時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旨,而沒有了統戰團結的任務,他們即將下放“五七幹校”。我們家將在一個星期內“散夥”。
父母離京之前,必須安排好弟弟妹妹,我只能服從學校的分配奔赴內蒙生產建設兵團。
4月15日,北京火車站紅旗飄飄,人群熙熙攘攘。
由於有過宣傳隊的經歷,我和另一位手風琴手陳嘉磊被調到師直。我們離開同校的同學,被單獨安排與北京60,66中的同學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車。
沒有朋友親人的送行,沒有歡聲笑語,沒有興奮,沒有激動,只有迷茫與淡淡的淒涼。
火車在荒原上顛簸了一天一夜,我們抵達內蒙古西部河套附近的巴彥淖爾盟,在小鎮巴彥高勒下了車。
因為是初建兵團所迎接到的的第一撥知識青年,當地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敲鑼打鼓,呼聲高昂。
我和66中同學李鳴託舉著一個巨大的毛主席像走在前列。我們趟著車軌下滿地的玉米粒(這是國家為突然注入的大量人口緊急調撥的糧食),迎著裹著黃沙的颶風,踉踉蹌蹌地登上了一輛輛大卡車,向沙漠中進發。
一路上,巨風呼嘯,黃沙滾滾,兩個小時,我們抵達包爾托拉蓋,當時的師部直屬機關所在地時,每個人都已黃沙蒙面,看不出人樣了。
一,初到直屬連
說是師部直屬機關,也就是一箇舊的勞改農場的基地。幾排黃色的土房,院子正中有一個稍微莊重一些的建築,就是師部了。我們被分配到直屬連。
直屬連是位於師部院子西側的一個玉字型建築,門前有個紅十字,應該是過去的農場醫務部門的舊址。
師直的第一批北京知青,二排右一是我
直屬連是直屬於師部的一個連隊。連裡下設鋪路,測繪,架線三個排,車輛,炊事,女生三個班。排裡大多數是部隊復員的退伍軍人,擔負測量規劃,以及修築從師部通往各個師,團,連的公路,架接電話線等基礎建設專案。
我們女生,每天被分派到不同的排,協助工作。
我們說是知識青年,可跟著測繪排出勤,我卻不會看座標圖;跟著架線排出勤,我卻不懂分辨線路的陰極陽極;跟著修路排出勤,我當然也不能介入路面鋪墊材料的配置等技術工作。我們只有參加體力勞動,平路基,拉沙土,扛電線…….
一天,我和女生段援朝跟架線排出勤。我們被分派向從師直到五團團部已經建成電話線的電杆進行標識與統計。
吃了早飯,我倆就上路了。
一路上,黃土沙包一個接著一個,時而有一些荊棘灌木,偶而,也會見到1-2棵沙棗樹,渺無人跡。這天風沙不大,天氣晴朗,乾燥炎熱,我倆順著建成的電線杆一路走下去,標識著,談說著,不知不覺,夕陽西下,天漸漸暗了下來。
當時只有16歲的我們沒有手錶,也不會看太陽,在荒無人煙的沙漠中走著走著。一天下來,沒吃也沒喝。突然,在遙遠的公路上傳來一輛卡車緊急剎車的刺耳鳴聲驚動了我們。只見身材略胖,被我們女生背後戲稱“胡傳魁”的副連長,焦急緊張地向我們走來。
在他的責備呵斥下,我倆登上了卡車被載回了連隊。原來,兩個女知青外出一天未歸,讓連領導們急眼了。
二,調入師醫院
過了週末,連裡突然宣佈我們八個女知青被調離直屬連,重新分配。在完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和另外兩個女生陳繼青,小趙被要求馬上去師醫院報到。
提上簡單的行李,登上卡車,我們又回到了兩個月前初下火車的小鎮巴彥高勒。在距巴鎮市中心5、6裡地郊外的一處舊中學校址內,就是我們初建起的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師醫院。
我被分配到一科,另外兩位戰友分別被分到二科和四科。這裡是解放軍野戰醫院的體制,不像地方醫院按病種分科那麼細,醫護人員的工作界定也不特別的清楚。我應該是衛生員,或是護理員,除了在病房搞衛生,配餐,擔水,護理病人之外,我們也參與一些治療工作。
上班第一天,穿上白大衣,心理緊張而又激動。我被分派給老衛生員於忠田做助手。瘦瘦高高的現役軍人小於靦腆寡言走在前面,我端著注射盤小心翼翼地跟在後面。在他的指導下,我進行了第一次肌肉注射。
從那以後,在知青食堂裡,大家見面就都興奮地交流著自己的收穫:我會打針了,我會抽血了,我會輸液了,我參加特護小組了……這一點一滴護理治療技術的嘗試,讓我們充實,讓我們快樂。有了這些,即使每天12小時值班,每天為病房做清潔搞衛生,每天幾十擔病人吃用冷熱用水的擔進挑出,每天打飯配餐,為病房生火捅爐子,我都不覺得辛苦,不覺得疲勞。
我們這些衛生員,大都是從連隊調入,直接充實到醫院護理部。因兵團初籌建醫院,急於開展工作,收治病人,沒來得急給我們進行初步的醫學培訓。在我們的工作漸漸走上正軌,醫院為我們開設了業餘醫學理論培訓班,由我們科王吉雲醫生開始教授解剖學。
在動盪的1970年,政治學習的任務一個接一個,戰備的動員令說來就來,作為小小的衛生員,我們完全沒有屬於自己可以支配的所謂業餘時間。醫學的第一課是解剖學,解剖學的第一課是運動系統,運動系統的第一課是骨骼肌肉,可是從人體具有206塊骨頭的運動系統概論被介紹了之後,學習班就再也沒能堅持辦下去。
學習瞭解了這點滴的醫學知識之後,我就越發不安了:每當為病人抽血時,我會想:血的PH值為什麼是7.35-7.45?低了或是高了會怎麼樣?肝功能所抽的血是查轉氨酶,可轉氨酶為什麼會從血裡邊出來呢?明明手術已經成功了的患者,出了手術室卻一直在搶救,為什麼呢?一個游泳時跳水而跌折了頸椎的戰友,他為什麼會癱瘓,他為什麼會昏迷?生理鹽水為什麼是0.9%,葡萄糖為什麼5%,10%?術後病人需要營養,為什麼不能多給?給濃度更高的營養液?隨著工作時日的增加,我頭腦中的問題每天層出不窮。
三,找到了方向
我們一科包括外科,婦產科與五官科。在護士長分配衛生員專職婦科時,衛生員的知青班裡都是十幾歲的青年小姑娘,誰也不願意去。我自告奮勇獲得了這個位置。這是因為婦科有一個專門的房間,一般情況下,婦產科病患不多,我可以靜靜地在這裡學習。
剛到婦科值班的第一週,就遇到了一起讓我刻骨銘心,印象深刻的事件。
一天晚上,三科康護士長急腹痛,因懷疑是宮外孕,她被送入婦科病室。地方調來的婦產科醫生周友芬心急火燎地趕了過來。在她檢查的同時,她口述醫囑:“婦科三級護理,備皮,術前常規準備”。她按地方醫院的常規程式指示著。
作為剛上任的婦科護士,又未經過護校學習的我當時就傻了:我不知道什麼是婦科三級護理,不知道針對這個醫囑我應該做些什麼。
外科值班軍醫張希智在一旁提醒我:量血壓。看著患者痛苦的面容,醫生緊張的神態,我抓起聽診器就衝上去量血壓。沒想到,周醫生一把奪過聽診器,將我搡到一邊,親自測試起來;同時對我大加訓斥。原來,我情急之下,把聽診器拿反了。
委屈,自責,無奈,痛苦,我當時站在一旁,只有不停地流淚。是的,沒有知識,沒有技能,就不能勝任應該擔任的工作。光知道苦幹,傻幹,拼命幹又有什麼用?可知識不完整,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厄運,就是我們因文化大革命而獲得的個人的損失。
沒有抱怨,沒有責備,沒有怨恨,沒有苦惱,從現在開始學習,學習。就從那時起,在那個一科婦產科的小房間裡開始了我如飢似渴,頑強的自學歷程。從手術室護士長齊獻玉那裡借來的《護理學》是我的第一本教材。當進入醫學知識學習,我就發現中學教授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化學,物理,數學,彼此在內容上是絲絲相扣,密切相連的。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識,根本就讀不懂醫學書籍。
從那時起,我為自己制訂了嚴格的自學計劃,充分利用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業餘時間,向朋友,向患者借討教科書,參考書。要工作,要生活,學習必須要有周密的計劃,從時間,從學習內容上予以嚴格的保障。
從那以後,我下了白班堅持夜讀;下了夜班,從不睡覺,放棄所有的休閒,娛樂,交友,享受,堅定地實施著學習的計劃;後來離開兵團,到了地方醫院,這個自學的計劃得以更為順暢的實施。科裡的醫生,進修生,有文化的病人,當教師的病人家屬,都可能是我隨時討教的老師。
終於,我聽說大學開始招生了。雖然是工農兵推薦上學的入學制度,可不學習補足中學課程,我只有初一的文化基礎是難以勝任在大學的學習內容的。我開始有了目標,更加執著地,努力地學習著。
經過不懈的努力,1975年,我終於獲得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學習機會。屆時,我已經透過自學完成了全部初中,高中課程,護校課程,和部分西醫大學課程。當我進入北中醫學習的時候,我成為了同學之中,文化基礎與醫學臨床知識都具有比較好基礎的學生。所以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並考取了研究生,得以繼續深造,以致走上了一生學術發展的道路。
在兵團讓我嚐到了缺乏知識的苦痛,讓我感受到了沒有完整教育的無奈;但是在這裡,我奠定了吃苦耐勞,不怕挫折,不怕磨難,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渴望學習,渴望充實自己的信念。就是這種意志與信念鼓勵,激動著我一路走來。
要說在兵團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那就是:那裡是讓我看到大學的地方。
在那裡的經歷讓我認識到:要讓自己成為有用的人,就是要學習,要充實,要用知識武裝自己。在日後的社會實踐中,我發現兵團的這一段經歷與獲得的志向,對我的一生都是彌足珍貴的。
醫院宣傳隊的女生們,後排右一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