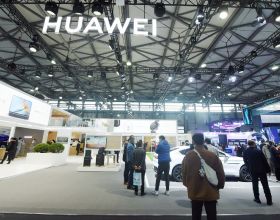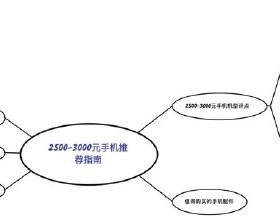《降E大調三重奏》是莫扎特的一首作品,在音樂大師如雲的名曲中算不上如雷貫耳;它也是法國電影新浪潮主將埃裡克·侯麥的一部戲劇作品,比起在華語世界都名聲顯赫、褒貶不一的“道德故事系列”“喜劇與箴言系列”和“四季系列”,它太低調。
但《降E大調三重奏》低調的最主要原因,是國內沒什麼人看過。它是電影大師侯麥唯一傳世的舞臺劇,多年來,既沒有國外院團攜其來華,也未曾聽說國內院團將其本土化公演。直到今年夏天,它的中文版被搬上國內舞臺。結果,作為近日疫情防控背景下鼓樓西劇場正常演出的最後一部戲,引發了北京觀眾的集體舒適。
一般對大師偶爾的跨界,欣賞者多是抱著嚐鮮的心態。但侯麥唯一的戲劇,不僅可以代表他的藝術追求,也完全可以代表他的藝術水準。若稍加研究,居然可以發現驚喜:這非但不是大師玩票,反而濃縮了他電影藝術的精華,甚至是承上啟下、構成其大半生涯的索引。
首先,要看這部戲的時間背景。《降E大調三重奏》創作於1987年,次年在法國首演。在侯麥的電影年表上,這段時間貌似空窗期:之前,他剛結束讓他贏得世界級大師聲譽的“喜劇與箴言系列”,之後,便是後期最重要的“四季故事”。
很多觀眾都覺得,“喜劇與箴言系列”更像是戲劇,完全摒棄了蒙太奇,徹底採用線性敘事。《降E大調三重奏》則將這一系列中受制於銀幕形式的歡快、自由、幽默,在舞臺上推到更淋漓的境地。比起“道德故事”時期令人時而反感的精英視角,“喜劇與箴言系列”中那些尚未功成名就、對愛情抱有理想的年輕男女主人公,因不那麼功利而討人喜歡。而其中每一個,似乎都能從《降E大調三重奏》裡的保羅和阿黛爾兩位主人公身上找到影子。
至於此後的“四季故事”,從《春天的故事》裡“一個包裝盒引發的誤會”,到《夏天的故事》裡始亂、終發現親友團才是避風港,再到《秋天的故事》裡“明明我知道我說出來你會生氣,但因為忠於你和我自己的道德,我必須說出來”的死理性派,再到《冬天的故事》裡“只選對的,不選貴的”等各種心理潔癖……恐怕每一部都在關鍵情節上有這出小戲的影子。
其實,就算侯麥更早期的作品,也能在這部戲劇中找到著陸點。“六個道德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她們生活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都不同程度地在遭遇“第二性”的社會困擾;電影中的她們,按時間順序,一個比一個更覺醒更有力,《降E大調三重奏》中的阿黛爾,則是發出“他們憑什麼管我啊”反問的八十年代新一輩。而保羅那“我寧肯要百萬分之一的成功機率,因為帶來的滿足也是百萬倍”的蜜汁自信,分明有著侯麥處女作《獅子星座》男主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保羅也是《獅子星座》編劇的名字。這位保羅·傑高夫是侯麥的摯友,兩人有著共同的音樂、文學和哲學愛好,而他最出名的身份,是新浪潮陣營中頭號花花公子,侯麥許多電影裡的花花公子角色,都是以他為原型。侯麥創作《降E大調三重奏》之前,保羅不幸身亡。於是,侯麥把摯友的名字和他骨灰級音樂發燒友的人設,都給了自己唯一的戲劇男主角,卻讓其情愛觀徹底反轉。這樣的紀念方式,還真的挺侯麥的。
筆者特別留意了下《降E大調三重奏》中文版的主創陣容,翻譯王婧近年來從事中法戲劇交流,導演何雨繁是作者型導演,再加上有法國文化藝術學習背景的鋼琴師……場燈亮起,演員們既不像從前的譯製片那樣,演著中國人想象的外國人的生活,也不是近年越來越多的拿衚衕串子的語言詮釋半個地球外的家長裡短,而是去捕捉侯麥賦予角色和對話的獨特價值,並且儘量符合2020年代中國都市人的理解接受習慣。
服膺康德理性批判哲學的侯麥(可參見《春天的故事》開頭),每每也將“自律給我自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給了自己的角色。此處的所謂“律”,絕非外人或社會強加的秩序,而是和頭頂星空一樣高的心中的道德律。在這個意義上,《降E大調三重奏》劇組也是在自己演自己,一群獨立狀態的戲劇人,如導演何雨繁所說,“除了戲本身,沒聊過別的,演完了也就散了,大家完全不熟;但共同的價值觀把這幾天的我們,迅速地捏合到一起。”而這樣自律並自由著的,還有臺下不願從眾、也不願躺平的觀眾。
這齣戲給觀眾以愉悅和滿足,線上的不只是演員的演技、導演的排程,服化道也功不可沒。服裝去裝飾、重質感,即便是紅黃這種傳統意義上的亮色,也把明度降到觀眾舒適區的下限……直到今天,典型的巴黎知識分子(嬉皮範兒除外)幾乎還是走著這樣不動腦子也不怕出錯的路線。上述細節,在侯麥本人也非常推崇的哲學家羅蘭·巴特所著、被時尚人士奉為聖經的《流行體系》中,都可以找到依據。
特別是男主角,無論是收口短袖白襯衫,還是西裝和毛衣,都採用啞光面料來營造緩慢、悠長的感覺,正如以紐約和北上廣為題材的作品,常以blingbling的造型來製造都市快節奏。如此一來,女主角無論何時推門造訪,“原來你還在這裡”的忠犬人設就天然真實可信起來。
至於女主角的海魂開衫、樂福鞋、幾乎可以視為男款的大西裝、隨意任它鬆垮的吊帶衫,則是對那個全球範圍內理想主義發出最強音的八十年代之忠實復刻。
喜歡拍“路人電影”的大師,大銀幕風格就是極簡,而他唯一編劇導演的話劇作品,還要加個“更”字。原版中除了“窗外”那和演員換裝同樣用來表示四季更迭的樹葉,幾乎道具上就沒有任何亮點。
鼓樓西的觀眾身在二環內的衚衕,卻彷彿穿越到了三十多年前巴黎左岸的頂層公寓,沒有最新電子裝置、物質和精神生活所需產品少而精地存在,陽臺花圃一應俱全。中國劇組的詮釋在尊重大師節制的審美趣味的同時,就像夏季的下午茶點那樣,色彩和造型透著清爽和甜蜜。
男主家的綠椅子和巴黎的每座公園裡擺著的幾乎同款,舞臺上的“巴黎綠”,和“巴黎8分鐘”裡大放異彩的鍍鋅屋頂、米黃的建築外牆主色調一起,為這座天氣陰溼而善於哲思的城市,營造出多變、熱情和包容的感性。
也許,放在2019年及以前這不算什麼。但在“世界這麼大,我卻不能去看看”的當下,對於文青,這場戲的“巴黎80分鐘”就像奧運閉幕式上的“巴黎8分鐘”那樣,是三伏天的一大杯冰鎮酸梅湯,哪怕之後不免再失落,但起碼當場是解過了渴。
攝影/塔蘇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