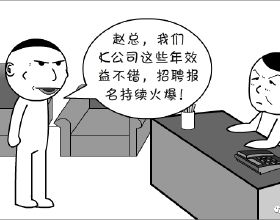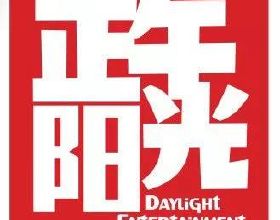先秦時期法家是戰國的終結者,以商鞅、韓非和李斯為代表的法家輔佐秦國一統天下,終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秦帝國卻二世而亡。
此後的傳統帝制中,雖然不再言法家,但很多人都認為是“儒表法裡”。
在春秋戰國的紛爭中,秦國並不屬於中原文化圈,一直被視為虎狼之國,尤其是秦孝公在採納了商鞅關於變法的措施後,國家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迅速增強。這是法傢俱備的先秦其他學派不具備的優勢,而這一優勢也最終促成了最終的大一統。
但是為戰爭為存在的法家學說,有著致命的漏洞與缺陷,它過於緊張,對普通的束縛過重,對人們的管控過於嚴厲,所以我們就會看到秦朝土崩瓦解之快,令人咂舌。
先秦法家的一整套學說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大一統,為了君主而服務。
商鞅,韓非都是洞悉人性的政治家、理論家。
商鞅說: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求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
在他的眼裡,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靠著這個本能去做的,餓了想吃飯,勞動就像休息,困苦就像安樂,卑微就像榮華富貴。
在對人的本性的分析中,韓非舉出了大量的例子論證,無論人與人之間處於何種關係,背後都是赤裸裸的利害計算。在親情關係中,孩子會抱怨父母沒有好好地撫養自己,父母又會抱怨孩子沒有盡到贍養的責任,身為至親,卻“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意思是都會抱怨對自己不好。
當時社會中有著濃厚的重男輕女的風氣,生男孩則慶祝,生女孩就殺掉,其原因不過是出於利益的計算考量罷了。因為生的女孩遲早要嫁到他家,而男孩則能更好地贍養父母,“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
當君主妃子的會盼望著君主快點死去,因為只有這樣自己才可以母憑子貴,開棺材店的會希望死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只有死人自己才會有生意可做。在韓非的眼中,社會的規則也好,人們之間的關係也罷,都被還原成了利害的計算,“利之所在,民之歸也。”
如此我們就會看到,法家學說對黑暗現實的赤裸裸的洞察力,實際上直到現在為止仍然有這種現象存在。人與人之間,往往是單純的利益關係,人被換算成金錢,變成了可被利用的工具。
但是如果把人類所有的關係都用簡單的公式概括,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法家也承擔了這一惡果,當人們僅有的一點選擇權都喪失的時候,爆發起來也是劇烈無比的。
秉持著此種人性論的法家,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學說。
在秦國統治下的人,沒有別的出路可選,要麼耕地,要麼打仗。
“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你有很多欲望要實現,可以。但是你只能按照我說的去做,去做農民耕地,去當士兵打仗。
只要立下戰功,無論你是什麼出身都可以獲得爵位。這在看重出身的先秦時期是具有開創性的,對人們的誘惑也很大。秦國的強盛很大程度都來自於此。
作為君主應該制定法律去禁止人們從事其它的職業,“多禁以止能”,讓人們畏懼而不敢有更多的想法,達到所謂“民樸”的愚民目的,讓老百姓一心一意的耕戰。
在這樣的社會里,出於自願也好,被迫也罷,沒有了其他謀生的出路,只能聽從統治者的安排,在戰爭上奮力殺敵以獲得想要的地位和財富,從而達到商鞅筆下的“壹賞”,即“利祿官爵摶出於兵”。
在社會中偏偏有一部分人不受君主賞罰的約束,既不從事農業,也不去戰場廝殺,韓非把他們斥之為“五蠹”,他們是分別為儒者、縱橫家、遊俠、逃兵役者和商人。這些人在韓非的眼裡簡直是禍國殃民般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對待他們的辦法就是消滅之。秦國後來的“焚書坑儒”就是實踐。而後世則透過不同的方式繼續實踐。
如此,我們就會看到,在法家的思想體系中,看不到除了耕戰之外的其它選擇。
每個人都像一根螺絲釘,處在國家這個大機器的一環之中,為了整體的利益所服務,卻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普通人對於法家來說只是工具,法家根本不關注個體是否真正的願意從事耕戰。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法家的耕戰思想也不是真正為了使民眾能夠富裕,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而服務,一旦民眾力量過於強大,則會想方設法的去削弱民眾的力量,掠奪民眾的錢財,剝奪民眾的地位。因為一旦普通人有了一定的金錢和地位,必然不願意再從事辛苦的勞作與戰爭,這是法家所不想看到的。
隨著秦國靠著對人們嚴酷的控制而促成的大一統局面,原先僅僅是秦國農民的遭遇擴大到了其他的國家之中,人們苦不堪言,又無處可逃,只好在沉默中爆發,最終迎來了秦末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