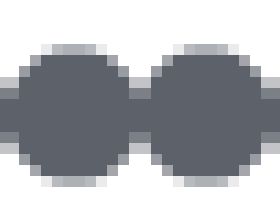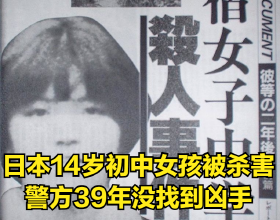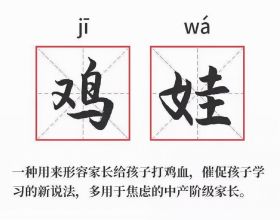家鄉人喜歡秦腔。
衡量一齣戲的好壞與否,則看角兒硬不硬。村外的土臺子上若有郭明霞或任哲中的表演,肯定能鬨動十里八鄉,那怕兩天兩夜不吃不喝也行。
記得小時候,不知為啥事村裡請來了西安劇團演出,而且有李愛琴壓臺。呀!不得了,早早就有莊稼漢們擠滿臺下,或蹲或坐,任憑臘月的西北風呼呼吼叫也毫不在意。等到八點戲一開鑼,土場竟黑壓壓堆了上千人。李愛琴做、唱、念、打一亮相,臺下立即炸了鍋,大家都想擁到近前看個仔細,你擠我,我擠你,攪成人浪。村裡基幹民兵二十幾個人,抽散幾把掃帚,從臺上齊刷刷跳下去,一陣猛抽,人群才像壓癟的豬尿泡一樣,向左右展平,稍傾人潮又起,民兵再打,一場戲,抽完了十來把掃帚。散場後,滿地丟著鞋、襪、帽子、圍脖、花頭巾和斷成一截截的竹枝。村裡人摸著被抽腫的腦門說:“看李愛琴這樣的角兒,值!”
在家鄉,還有一種角兒受人崇拜,但不是演員,也不是行當,而是頂神的角色。如狐仙、貓神及各種叫不上名字的鬼仙,這些角兒大部分是一些沒出過門,沒見過世面的家庭婦女。神來時,角兒閉目唱歌,搖頭晃腦,爾後說出某一隱秘之事,或預言某一怪事發生,信男善女伏側恭聽,皆感激涕零。回家則敬香、燒表、唸經、埋石、栽桃、封神、祛邪,以求平安。神走後,角兒恢復原狀,竟對發生之事懵然不知,聽旁人說才知道自己成了角兒。鄰村有一狐仙角,述事如神,有好事者告諸公安部門,以盅惑人心之名抓之坐監,角兒入內便大吐鮮血不已,公安怕其喪命,遂放,角兒立時健康如初,人皆驚異。在一次古會上,我有幸目睹角兒神采,眾人圍一小屋,角兒上香唸咒,俄傾忽覺有冷氣襲人,角兒隨即進入混沌狀態,但聞闢啪作響,一大堆供奉的核桃及兩瓶白酒被角兒鯨吞,眾人於驚竦中問命問病,角兒對答如流,我當時感覺那怪怪的聲音非常遙遠,卻又異常清晰。
漸漸家鄉人見到的角兒少了,先是名角進了大劇院,錄成像上了電視,於炕上、沙發上就可賞其風采,但絕沒有了在土臺下感受到的那種蒼涼的韻味,即秦腔變得富貴起來,聽或看有一股膩味,全然提不起神來;再則住房換成了小樓,財神土地找不著地方,邪門頂神角兒也就沒有了市場,平常有頭痛腦熱的,早去醫院治療,哪來閒功夫讓角兒胡掐?再說老百姓從電視裡瞭解了外面的世界,又經過風風雨雨,所謂傳話類的預言也失卻了往日的魅力。因之,角兒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漸漸被遺忘了。
但角兒所代表的那種文化氛圍卻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法國世界盃期間,我於晚上在咸陽的街頭閒蕩,希望有一家鋪面播放球賽,遺憾的是除過霓虹燈和如梭的車流外,沒有街面電視,人們紛紛在廣場或休閒的地方乘涼。我失望地在市中心廣場躑躅。忽然,兩聲梆子響傳入耳鼓,循聲而去,在59路車站牌下聚攏一圈人,兩名土眉土眼的男人拉著二胡,敲梆子定弦的則是一女角,她蓬著頭髮,眼睛穿過虛假的燈光射向深邃的夜空。一聲如泣如訴的苦音陡然間從喉間溢位,漸長漸遠。隨之巜五典坡》中的王寶釧走到了眼前。
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停了下來,身上的汗液也被那純樸如土的顫音揩搽得乾乾淨淨。我想起十三年前冬天聽完《長安》雜誌社的詩歌講座,子夜時分從教場門走回南郊,在夾裹雪花的西北風裡行走,到南門時,門洞裡幾名藝人正在鼓弦唱巜下河東》,三十六哭竟成了城市的絕響。那時,我佇立街頭,於風雪中潸然淚下,淚水從臉頰流下時散發著熾熱的情感。雖然未能看清角兒的面目,但我相信,他們是在用整個生命在吶喊。一樣的血肉之軀,一樣的唱腔和絃律,因了他們,秦腔在都市裡也唱出了味兒。
我聽著,心頭不時掠過頂神角兒表演帶給人的肅殺與靜穆。我的目光越過桔紅色的燈光,在各種卡拉OK廳、錄影廳、遊戲廳及計程車的喧囂聲裡,我只感到本質的純淨的秦腔在胸中流淌、澎湃,並激蕩成我的血液,成為我生命的本源。我祈禱,讓這角兒永恆!
(網圖,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