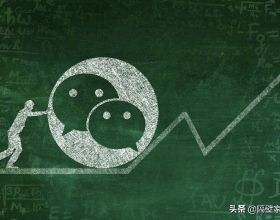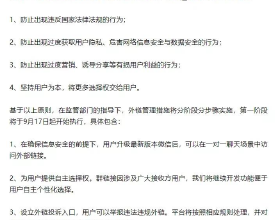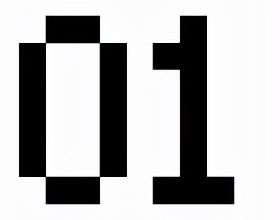1830至1860年代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一大批影響深遠的文學家和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1825年,隨著以“十二月黨人起義”為代表的貴族革命宣告失敗,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動統治的殘酷時代成為新的現實。如今被譽為“現代俄國文學的奠基人”的普希金率先登上了時代的舞臺,他的作品是反映當時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但也因此成為沙皇政府嚴密監視的物件。正如思想家赫爾岑所說:“只有普希金的響亮遼闊的歌聲在奴役和苦難的山谷裡鳴響著,這個歌聲繼承了過去的時代,用勇敢的聲音充實了今天的日子,並且把它的聲音送向那遙遠的未來。”
對於新一代文學青年來說,普希金是他們共同的嚮導。詩人萊蒙托夫深受其影響,他的早期作品借鑑了普希金的風格,並且常常在詩中塑造一種拜倫式的英雄——以一個被放逐者和復仇者的姿態出現,堅定而冷漠地對抗世界。1837年,普希金在與沙皇禁衛軍軍官、紈絝子弟丹特斯的決鬥中負傷而死。那時,萊蒙托夫還沒有進入到與普希金關係最親密的圈子,兩人並不相識。然而,他在獲悉普希金去世訊息後立刻寫就的《詩人之死》卻引發了轟動。在詩中,萊蒙托夫直言貴族是普希金之死的真正罪魁禍首,他將上流社會描繪成一群自私自利的惡棍,是“殺害自由、天才和榮耀的劊子手”。事後,萊蒙托夫被捕,並被流放到高加索。但與此同時,他也聲名鵲起,被譽為“普希金的繼承人”。
某種程度上,萊蒙托夫與普希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都出身貴族,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不滿貴族階級醉生夢死的生活和對沙皇專制統治的盲目服從;他們都透過詩歌探尋社會的方向,卻也因此被流放,作品難以出版;更巧合的是,兩人都死於和他人的決鬥。俄國作家伊·伊·巴納耶夫在其文學回憶錄《群星燦爛的年代》中指出,儘管萊蒙托夫意識到普希金之死源於他的上流社會習氣,但前者卻也未能擺脫上流社會的吸引力,“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樣,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個文學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
這種上流社會習氣在1830年代的文學圈十分普遍,而當時作為文壇新秀的巴納耶夫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對作家及其作品的巨大傷害。他的文壇好友別林斯基也注意到,文學界有一種“可憐的、幼稚的對權威的崇敬”,人們不敢公開批評顯貴。巴納耶夫同樣出生於貴族家庭,但從青年時便醉心文學創作,對官場升遷毫無興趣。1834年,他透過發表作品接觸到以普希金為核心的文學圈,見證了這一時期萊蒙托夫、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學大師的傳奇往事,也看到了他們不為人知的性格品質和生活日常。
《群星燦爛的年代》(節選)
文 | 伊·伊·巴納耶夫 譯 | 劉敦健
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有些文學活動家很容易染上所謂的上流社會習氣,這種傾向對他們本身和他們的作品都十分不利。就連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樣有巨大影響的天才人物也常常陷入這種傾向。
萊蒙托夫不惜一切代價,首先要獲得的就是作為上流社會人物的名聲。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樣,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個文學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順便說一句,儘管他意識到,普希金之死歸因於他的上流社會習氣,儘管萊蒙托夫有時也想對上流社會的人們投以鐵的詩句,但他怎麼也無法擺脫上流社會的種種偏見,上流社會對他仍然很有吸引力。
萊蒙托夫是以《詩人之死》一詩而出的名,然而在此之前,當他還在士官學校讀書的時候,他傑出的詩才便有所傳聞—他的《惡魔》一詩也以手抄本形式流傳開來。他那篇關於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故事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主編的《俄國榮軍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以後,文學評論才開始注意他。
01 一個總要拿別人當犧牲品的頑童
我初次見到萊蒙托夫是在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晚會上。
萊蒙托夫的外表非常出眾。
他個子不高,身體健壯,頭和臉龐都很大,前額寬大,有一雙深邃、聰明而又銳利的黑眼睛。當他久久凝視別人時,會使人不由得感到發窘。萊蒙托夫瞭解自己眼神的力量,喜歡用他那持久而銳利的目光使那些膽怯而又神經質的人感到窘迫難受。有一次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裡碰見我的朋友米·亞·雅澤科夫,雅澤科夫坐在萊蒙托夫對面,當時他們互不認識,萊蒙托夫目不轉睛地盯了他幾分鐘,雅澤科夫一時間覺得神經受到強烈刺激,他受不了這種眼神,便起身到另一個房間去了。他至今沒有忘記這件事。
我曾多次聽萊蒙托夫的同學和團隊的夥伴談到他。據他們說,喜歡他的人不多,只有同他關係親密的人除外,但他同這些人也很少傾心交談。他很喜歡在自己的每一個熟人身上尋找可笑之處、尋找某種弱點,一旦被他找到,他便一再糾纏那個人,經常拿他取笑,直至別人無法忍受。當別人終於發起火來時,他卻感到十分愜意。
“說來也怪,”他的一個夥伴曾對我說,“他這人其實倒也不壞:飲酒作樂呀,玩樂一番呀——他在哪個方面都不落在大夥兒後面,可他對人一點兒也不溫厚,總要拿別人當犧牲品,否則他就不得安寧;選中了誰當犧牲品,他就死死纏住人家不放。他免不了要遭到這種悲慘的結局:就算馬丁諾夫不殺他,他也會被別的人殺死。”
就結識和交往的範圍而言,萊蒙托夫屬於上流社會,他只結識屬於這一階層的文學家,只結識文學權威和知名人物。我初次見到他是在奧陀耶夫斯基家裡,後來又經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兒見到他。他是在什麼地方和怎樣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結交的,我不瞭解,但他和他關係相當親密,甚至以你相稱。
萊蒙托夫通常是上午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這兒來(那是在《祖國紀事》創辦初期,即1840和1841年),並把自己新的詩作帶給他。克拉耶夫斯基的工作室裡擺設著樣式古怪的桌子和大大小小的書架,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書籍和報刊;主編則坐在一張桌邊埋頭看校樣,神情莊重,身穿一套煉丹術士的服裝。萊蒙托夫總是大聲喧嚷著走進他的工作室,來到他的桌前,把他的校樣和文稿撒得滿地都是,把桌子上和房間裡攪得亂七八糟。有一次他甚至把那位學識淵博的主編從椅子上撞到地板上,致使他手忙腳亂地在一堆校樣裡掙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一向舉止穩重,習慣井然有序、認真細緻的作風,對這類玩笑和頑童式的舉動該是不喜歡的,但他對他以你相稱的這位偉大天才的種種舉動卻不得不忍受,總是半皺眉半微笑地說:
“唉,夠了,夠了……別鬧了,老弟,別鬧了。瞧你這個頑童……”
這種時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很像歌德筆下的瓦格納(注:詩劇《浮士德》中的博士),萊蒙托夫則像是梅菲斯特(注:詩劇《浮士德》中的惡魔)暗中派到瓦格納身邊、故意擾亂他深沉思緒的小鬼。
當學者理一理頭髮、拍一拍衣裳,恢復正常以後,詩人便開始講述自己在上流社會的種種趣事,再讀讀自己新的詩作,然後起身離去。他的來訪總是十分短暫。
02 作為普通人的萊蒙托夫和作為作家的萊蒙托夫
萊蒙托夫同法國駐彼得堡公使巴朗特先生的兒子決鬥的那一天,我也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裡見過萊蒙托夫……萊蒙托夫在決鬥以後徑直乘車來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給我們看了他手臂上的一處傷痕。他們決鬥時用的是長劍。那天上午萊蒙托夫異常快活,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別林斯基當時也在場。
別林斯基經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碰見萊蒙托夫。別林斯基不止一次試圖同他認真談一談,但從來都是毫無結果。萊蒙托夫每次都用一兩句笑話敷衍過去,再不就乾脆打斷他的話頭,使別林斯基感到難堪。
“萊蒙托夫很聰明。誰要是懷疑這一點,那是很奇怪的。”別林斯基說道,“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萊蒙托夫說過一句有道理的、聰明的話。他似乎是有意炫耀上流社會的那種空虛。”
確實,萊蒙托夫彷彿總是炫耀這種空虛,有時還想加上一點撒旦式或拜倫式的成分:敏銳的觀點,刻毒的玩笑和哂笑,竭力顯示他對生活的鄙視,有時甚至是一個好鬥者尋釁滋事的情緒。毫無疑問,即使他不是透過畢巧林(注:萊蒙托夫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的形象描繪他自己,那麼至少這也是在當時攪得他心神不安、他很想效法的一個理想人物。
當他同巴朗特決鬥以後被關在禁閉室時,別林斯基前去探望過他;他同萊蒙托夫面對面地談了將近四個小時,隨後徑直來到我這裡。
我朝別林斯基看了一眼,一下子就看出他心情異常愉快。我已經說過,別林斯基不會隱瞞自己的感覺和印象,也從來不偽裝。他在這一點上同萊蒙托夫完全相反。
“您知道我從哪兒來嗎?”別林斯基問道。
“從哪兒呢?”
“我去禁閉室見了萊蒙托夫,談得非常成功。他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哎,老兄,我頭一次看出這個人的真實面貌!!您是瞭解我的:既不機靈,又不會上流社會那一套。我一到他那兒馬上就窘住了,就像我平時一樣……說實在的,我感到十分懊喪,決心在他那兒最多待十五分鐘。開頭幾分鐘我覺得很不自在,但後來我們不知怎麼談起了英國文學和沃爾特·司各特……‘我不喜歡沃爾特·司各特,’萊蒙托夫對我說,‘他的作品很少有詩意,乾巴巴的。’於是他開始發揮這種見解,越談越來勁兒。我望著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十分自然,他在這一刻現出了自己本來面目……他的話裡有那麼多的真知灼見,那樣深刻而又淳樸!我頭一次見到真正的萊蒙托夫,而這一直是我的願望。他的話題從沃爾特·司各特轉到庫珀身上,談到庫珀時他熱情洋溢,他論證庫珀作品中的詩意比沃爾特·司各特多得多,論證得非常透徹,很有見地。我的天呀!這個人的美感該有多麼豐富!他有一顆多麼細膩、多麼敏感的詩的心靈!……可他這人也真怪!我想他現在正在後悔,覺得不該暴露自己的真相,哪怕只有一會兒——我確信這一點……”
怎樣才能把作為普通人的萊蒙托夫和作為作家的萊蒙托夫這兩個概念連在一起呢?
作為一個作家,萊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膽機敏、孜孜進取的才智令人驚訝:他的世界觀較之普希金已博大和深刻得多——這一點幾乎是公認的。他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顯示出他具有遠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們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會欺騙這種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過早擱筆,說不定他會在俄國文學史上佔居首位……那麼,為什麼大多數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是個空虛的人,幾乎是個凡夫俗子,而且心術不良呢?初看起來,這一點似乎不可理喻。
然而大部分認識他的人中有些是上流社會的人,他們用輕率、狹隘和膚淺的觀點看待一切,有些是眼光淺薄的道德君子,他們只抓住一些表面現象,便根據這些表面現象和行為對人作出武斷的、蓋棺定論式的結論。
萊蒙托夫比他周圍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認真的態度對待這樣一些人。看來令他特別不快的是後一部分人,即那些頭腦遲鈍的正人君子,他們擺出一副頭頭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勢,實際上卻是鼠目寸光。在這些先生面前裝扮成一個最空虛的人,甚至裝扮成一個頑皮的小學生,這樣做可以帶來某種精神享受——這是十分清楚的事。
當然,一部分是由於萊蒙托夫在其中長大和受教育的那個圈子的各種偏見,一部分是由於他處在青年時期,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願望,想披上一件拜倫式的外衣賣弄一番——這些因素使許多思想真正嚴肅的人感到很不愉快,也使萊蒙托夫顯得矯揉造作、令人厭惡。但是,能因此而苛責萊蒙托夫嗎?……他死的時候還那樣年輕。死亡迫使他擱筆的時候,他在內心深處正在同自己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其結果他有可能取得勝利,轉而用樸實的態度同人們交往,並樹立堅定牢固的信仰……
03 文學應當脫離孤立的藝術高壇
萊蒙托夫的作品發表在最初幾期《祖國紀事》上,這對刊物取得成功無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一個刊物,不論它的文學作品專欄辦得怎樣出色,沒有評論欄還是不能發展……
彼得堡的文學界和期刊出版界在我置身局外時曾一度對我很有魅力,但隨著我同他們日益接近,這種魅力便日漸消失。當我躋身於文學舞臺的幕後時,我看出我一度奉若神明的那些人所懷的動機是些多麼卑劣的人類的貪慾——愛慕虛榮、貪圖錢財、嫉妒別人……別林斯基發表在《望遠鏡》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爾戈羅德》一書中的小說和萊蒙托夫的詩篇開始稍稍擴大了我的視野,讓我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氣息,使我的心裡預感到會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出現。別林斯基的文章使我對一些文學權威的盲目信仰和對他們的卑怯之情開始徹底動搖。我已不時地認真思索起以往不會引起我任何思想的那些現象,我開始更加留心地觀察人們、觀察我周圍的現實生活,我開始產生疑慮,心裡也感到不安;由於家庭和學校的陳規舊習,我從小就對各種生活事實習以為常,不持異議,然而現在我似乎已經不願意相信這些生活事實並對它們無條件加以接受。但是,所有這些日益覺醒的意識的徵兆在我的思想上還表現得非常模糊、非常微弱……
藝術應當為它自身服務,藝術乃是一片單獨的、獨立的天地,藝術家在其作品中愈是態度冷淡,或者如當時所說的愈是客觀,他就愈是高尚——這種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學界最為突出、最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鏗鏘和諧的詩篇發展了這種思想,而在《詩人和群氓》一詩中則把它發揮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利己主義程度,然而我們當初朗誦這首詩時無不異常欣喜,認為它幾乎可以算是普希金最優秀的抒情詩。繼普希金之後,當時所有傑出的文學活動家和活躍在他們周圍的青年都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竭誠而熱烈的捍衛者。
庫科爾尼克也是這一理論的讚賞者。我們已經看到,他在普希金去世前幾年,尤其是在他死後,還一再宣揚真正的藝術不應當留意於日常的、當代的、庸俗的生活,藝術應當翱翔於雲天,它描繪的只能是英雄人物、歷史人物和藝術家。由此也就產生了那些冗長而又極其乏味,內部冷如寒冰、表面卻熱情沸騰的描寫藝術家的戲劇和幅面巨大、明暗對比強烈的畫幅——而且一齣戲愈是冗長乏味,一幅畫的底布愈是巨大,人們對詩人或畫家就愈是感到驚訝。……他透過這些作品助長了一種十分荒唐的自信心,彷彿俄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制服全世界,這種自信心後來使我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社會上已經朦朧地感到需要有一種新的見解,並且已經表現出一種願望:文學應當脫離孤立的藝術高壇,並接近現實生活,應當或多或少關注社會利益。誇誇其談的藝術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極為厭煩。
我們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羅斯人。就在這樣一個時刻突然出現了果戈理,普希金以其藝術鑑別力最先看出了他的巨大才能,但波列沃伊對他卻根本不理解,而在當時大家仍然把波列沃伊看成一個先進人物。
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獲得極大的成功,然而在開始時,就連果戈理最熱烈的崇拜者中也沒有什麼人充分理解這部作品的意義,也沒有預感到這部喜劇的作者將會實現多麼重大的變革。庫科爾尼克看了《欽差大臣》的演出後僅報以譏諷的一笑,他沒有否認果戈理的才華,但同時卻又說:“這終究只是一場鬧劇,稱不上什麼藝術。”
繼果戈理之後出現了萊蒙托夫。別林斯基則以他那犀利大膽的評論文章使那些文學貴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學家十分惱怒,但卻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
一股清新的氣息已經吹進了文學界……
本文書摘部分選自《群星燦爛的年代》一書第八章,較原文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