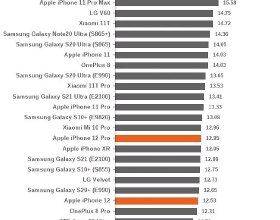人到了一定歲數,總愛回憶許多過去的人和事、生活過的地方,尤其是當時伴度了歡樂的。在我風雨五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有幾處留存念想地方,其一就是我童少時代的樂土烏鳳嶺了。
烏鳳嶺,位於我們京山錢場劉嶺村七組,是我么叔家居住的地方。么叔,實則是我的姨媽,我的外祖母生過十來個孩子,活下來的只有媽媽和么叔兩姊妹,因為欠男孩,所以就女作男稱,要我們喊么叔了。媽媽是留家裡招的上門女婿,外祖父又去世得早,外祖母我們也女作男稱,稱作爹爹。我到底不知道烏鳳嶺這名稱的來由了,總之,是那麼一處山嶺相夾的小山窪,中間是沖田,由北向南傾斜,東西兩側橫亙山樑山丘,沖田西側高處,鬆鬆散散住著七八戶人家,么叔房子居中,往外伸出一些。
童年時代我經常到烏鳳嶺去了。在故鄉村小學讀書的那些年,因為那裡較我家離學校近,又加上么叔的兩個兒子社平和會平和我同班,所以有時天下雨,我乾脆就隨表兄弟去過夜了。
記得小學四年級時,一個秋雨天,我到烏鳳嶺去,那時么叔家房子是棟土磚屋,幾經整修,每間房頂布瓦間都安設一塊明瓦,房間裡很亮堂。那一夜,我和會平同睡一張床,會平給我講山裡的故事,我望著房頂明瓦透進的亮光,好奇聽著,覺得多麼新奇有趣啊,在想象裡漸入甜甜的夢鄉。次日早晨,雨過天晴,么叔燒早飯,我們吃後上學,當我們走過綠伏灣,爬上山坡,昂然站在坡頂,終於看到土磚房的小學,和小學邊那口水面鏡面般光亮的堰塘時,我是怎樣地欣喜啊。
么叔和她的丈夫,我們稱為叔叔的,共生有四個子女。大兒子新平,二兒子社平,三兒子會平,老么是個女兒,叫美紅。社平十歲生日請客那天,我家小兄妹在爹爹帶引下來烏鳳嶺了。到么叔家時,天色還早,太陽還沒出,烏鳳嶺上空籠著細紗牛乳似的晨霧,樹葉草尖都沾掛露珠兒,潮潮欲滴,各種不知名的雀鳥早醒了,在灣前灣後滿是高樹的茂林間翔飛鳴叫,傳來滿耳的清脆,那景色太怡人了,我深吸著清新的空氣,神清氣爽。
因為是請客的大事情,么叔一家人也早忙活開來了。叔叔在灶門口搬碼劈柴,鐵鍋裡騰騰地往上冒著熱氣,六七歲的美紅坐門前光滑的青石上玩耍。側屋裡,兩隻條凳擱著叔叔還健在養父的黑油漆棺材,頭尾朝著側屋前後的門,很有些令人害怕。但我的害怕很快淡然了,望著門前的幾叢雪梨樹,我醒悟似地問美紅:“么叔到哪兒去了,怎麼沒見么叔?”“媽媽清早就到松樹山腳下的菜園裡摘菜去了”美紅指著遠處說。這時會平也不知從哪兒出來了,見我們的到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陪我到鄰居家前面禾場邊走看一會兒,然後我們便去菜園尋么叔。
我們循著兩邊都是稻田的一口長方大堰的堤壩一直向前走去。堰水清粼粼的,水面上稀疏地挺立些荷葉杆兒,幾處菱藤層層疊疊,堰邊角落長著蘆葦等水草,微微一陣風吹來,水面皺出細碎的波紋,水草柔順嫵媚地搖曳。太陽這時已從松樹山頂出來了,紅豔豔的,映照得滿山的松樹在沖田裡投下個偌大的影,將沖田幾乎全蔭著了,霧氣也漸消散了,而滿山松林裡的知了卻這裡那裡地鳴叫起來,混雜了松山背後的箍拉山等幾座石頭茅草山上雲雀吹口哨似的叫聲,傳來滿耳悅耳的繁響。
看到我們,么叔很興奮,於是我們便幫么叔摘菜,用長把的膠舀子澆園子。菜園是在山腳下的隙地裡開闢出的,面積半畝來大小的樣子,四圍都精心地紮了籬笆,籬笆上爬長滿了豆角、絲瓜,將籬笆簇繞得更嚴實了。裡面,修整得井然的廂壟上,仔細的么叔扯拔得一根草也沒有,一畦畦茄子、辣椒、莧菜、空心菜等等,一應夏秋季的果蔬俱全,青靈翠閃,滋滋競長。看那蔬菜長得欣榮意趣樣兒,又加上山間氤氳可人的氣息,我們一邊勞動著,心內別提有多愜意了,現在想,高中語文課本里陶淵明詩中那種“種豆南山下”的意境和心境,大約正是那樣的吧。
讀五年級時,有一天,會平湊近我的耳邊說,烏鳳嶺的拐棗熟了,星期天到那裡吃拐棗吧,我欣然應允。那是初秋九月的一個下午,我專來烏鳳嶺打拐棗,禾場前的那株大拐棗真高啊,我無法捋著枝柯,會平社平便搬來梯子,拿起鐮刀爬上樹去,騎在枝柯間幫我採摘,將拐棗一摞一摞扔下來。那些拐棗兒細看,一小段一小段的,麻青泛黃,兩頭都綴著些花椒般大小的小球兒,我撕斷揉進嘴裡,那味道甜甜澀澀的,幸福著難忘的時光。
歲月荏苒,天真爛漫的童少時光很快地過去了。烏鳳嶺發生大變化,么叔的四個孩子初中畢業後,一個個外出打工,結婚成家,他們的土磚老屋早拆了,烏鳳嶺的人家也大都外遷,以前人氣旺盛的灣子,我前年去看時,冷落空寂了。(李甫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