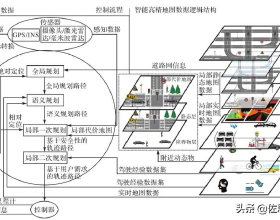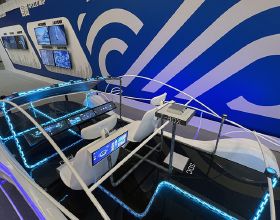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新時期文學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文體融合,具體到散文,則是其敘事的不斷增強,用以彌補單純抒情的空疏之感。李修文的散文集《詩來見我》就有著強烈的敘事意識,這是為了更好地與古人對話所進行的密集文化書寫。而這種書寫,則以中國舊體詩詞為載體。
《詩來見我》雖然有著文體融合的特徵,卻又不僅體現在散文的敘事手法上,它還融匯了古代的詩話和筆記。試看書中作家對一些詩人詩作的評價,比如對元稹和白居易的關係,作者說“這二人之交從未凌空蹈虛,所有獻給對方的狂喜、絞痛和眼淚,都誕生和深埋在煙火、糟糠、種種欲罷不能又或畫地為牢之處。”他認為李白將生前身後的全部都交付給了鵬鳥,透過這隻大鵬,將孔子、八裔與萬世交融在一起。此外,對於屈原、宋之問、柳宗元、羅隱、蘇軾、辛棄疾、李清照等人,他也有人詩合一之論。雖不似學術研究般嚴密,但卻是以誠喚誠,以心交心,在詩中見到了想見的古人,也見到了想見的自己。
如此密集的評點,知人論世又超脫,像極了本事詩,像極了詩品詩話,又像極了《世說新語》。因此,這部作品的文體意義,遠非小說、散文兩個大類所能概括。可以說,在以散文為形的前提下,李修文力圖不斷向內挖掘,透過內心的溝壑與腦海中的繁星,完成一種波瀾不驚的、靜態的文體探索。
《詩來見我》中的詩對李修文的意義,就好比科學對於眾人是一種萬物理論(一切事物的理論)一般,詩就是這個“痴人”的萬物理論。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文化,但這種“文化”,並不是盲目復古,也不似當下許多人對古詩的解讀,非要用跨越時空的玄語,來作現實的雞湯,最終落得一個心安。
李修文反其道而行之,別人以古語的幽玄來化現實的沉痾,他卻以自身的倉皇去回應古詩中那些客子書生的倉皇。書中的20篇散文,主題有友情、旅途、懷古、自遣、針砭、故里、親情、離別、飲酒等。這些主題又有一個基調——沉鬱。沉鬱要求不能有太多路數,也不能太浮動於塵世,最關鍵的,沉鬱還要求虔誠。
他選擇了一種頗為寂寞且危險的寫法,一種有“套古”嫌疑的古典作派來作為構思的模具。他的敏感隨處可得,又遍覽山川有著更多的壯遊經歷。這就使得他常常能想到一些詩句,並且在這些詩句中藏身,等來自己的知音,再回到現實世界,以看似無奈但卻堅定萬分的態度來對待下一步的生活。他在古詩中尋找的,往往是遍經崎嶇、方見真我的人生軌跡。
在與古人心靈的對話中,李修文用情至深,而且這種情是一種中國情愫。《詩來見我》涉及到當代散文如何處理古典文學經驗的問題。它啟示我們,要真正賡續中國詩歌的傳統精神,還需要當代有活力的作家對於古典知識進行內化,遂心應手地應用到日常寫作中來,也即透過學習古典詩歌的智慧,來尋找我們民族特有的情感表達方式。
中國的寫情傳統,有一種對集體的信任和維護意識,一種高潔與忠誠的超拔之氣,這也就促成了個人情感的節制與突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種節制與突破的雙重變奏之下,才出現了一些深情婉轉、鏗鏘有力的作品。因此,適當地借鑑古人的寫作機心,其實反而是從文學本體的層面學習一種似舊還新的表達方式。
李修文有這樣的修養和性靈,所以他遇見古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所寫下的不僅是我的審美物件,更是我自身命運的一部分。”《詩來見我》中有著無奈的離別、浮世的喧譁等一系列眾生皆有的困境。但是他在這種種困境中有著最好的棲居之所,那就是古典詩歌。所以當思念友人的時候,他能從元白的唱和聯想到與友人的通訊,從而更加領會緣分的珍貴與外物無關;當身在異鄉,孤寂難言時,他又能與李商隱、羅隱、宋之問、寇準、劉禹錫、柳宗元等“命中犯驛”的人進行交談,並且比較他們對待艱苦旅途的態度,從而找出自己的同道。詩歌給他一種特殊能力——明明認清現實,卻還能在跨越古今的酬唱之中得到前行的力量。
“也許,一覺醒來,到了明早,到了真正的別離之時,我也能夠像他一樣,寫出一首詩,再身懷著信心與作證之心,奔跑著,成為無數無名氏中間的一個。”這是在波瀾湧動之後,透過與古人對話而找到的對生活的平常心。他知道,擁有這一瞬間的喘息,才是一個人存在過的最好明證。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