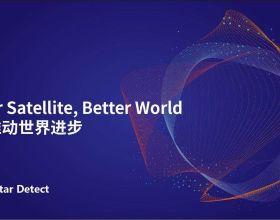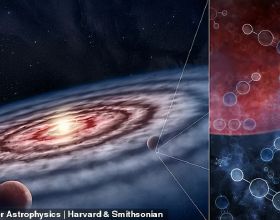在具象與抽象之間
——評北京青年編導汪圓清的現代舞《無自畫像》
北京青年編導汪圓清的現代舞《無自畫像》第二版在北京首次登場後。許是因為如今舞蹈界用心寫舞評的人太少,許是因為我之前寫的幾篇現代舞舞評引來了不少朋友的關注,所以這兩天居然有朋友在微信裡留言說:“雖然我們已經看懂了汪導的作品,很喜歡。但是還是很期待您的舞評。”
其實關於《無自畫像》第二版的創作思路、主題內容和音樂表現手法等,編導汪圓清、音樂師劉一緯以及雷動天下現代舞團的藝術總監曹誠淵老師都分別在他們的部落格裡公開講述了許多,因此,我在這篇評論中,並不打算去重複記錄大家已經明白的觀點和聲音,而是想從現代舞創作本身出發提出一些新的問題,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性的思考。
一、關於“作品非常汪圓清”
在微信朋友圈裡看到一位觀眾評價說:“作品非常汪圓清”。雖然我並不認識這位觀眾,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比較熟悉汪圓清。“非常汪圓清”的概念給我們傳遞的是這樣一種資訊:這個作品很像汪圓清這個人的風格,很具有汪圓清這個人的特點。那麼,汪圓清究竟具有怎樣風格和特點?又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質呢?我們先從節目單裡看看關於他的簡介:
汪圓清,藝術指導/舞蹈編導/視覺設計師。著力於跨領域的融合創作,作品涉及舞蹈、戲劇、音樂、視覺等。曾為北京舞蹈雙週、中法文化年、中日當代舞論壇平面設計/中德爵士即興音樂節聯合策劃人/樂視體育視覺設計總監。2014年創辦一個玩子藝術實驗工作室,2016年加入臺灣驫舞劇場以及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客席編舞。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頗具典型性的“斜槓青年”。他創作的靈感與源泉更多來自於他閱讀過的大量的書籍和“斜槓青年”這個身份所具有的多元化的知識結構和文化底蘊。例如,在創作《無自畫像》的過程中他吸收了德國新生代思想家韓炳哲的《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一書中的關於新的人類“手的萎縮”的觀念,並將其運用到了“無手而動指的人”——數碼人這一舞段中。演繹出數碼裝置讓新人類由人蛻變成猿猴的警示。
他曾經也給我推薦過一本叫作《上帝的語言》的書,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深意的觀點:現代科學與上帝和聖經信仰並行不悖。我們需要把科學和靈性(或宗教)這兩種視角結合起來,以便理解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 而他自己則發現《上帝的語言》不僅帶給他對“生”的思考,也引發出他對“死”的探究。因此他是帶著一副探險家的手杖走著屬於自己的現代舞創作之路,在他的現代舞創作探險程式中沒有預定的目的地,也不受任何規定的嚮導的限制。他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毫無教條,因為他不從隸屬於任何流派、任何主義、任何社會思潮,所以他沒有任何特定的原則需要遵循。如果有的話,那就是遵循在藝術創作中充分展示自己獨立不移的自由思想。
也許“汪圓清”將來真的會成為現代舞創作手法的一個特定的代名詞。因為他在創作中所做出的實驗性的“冒險”,不僅僅是代表了年輕的一代現代舞編導們的“冒險”,也是代表了一種現代舞實驗性創作方式的“冒險”。
二、是“編舞”還是“編導”?
在汪圓清的實驗性舞蹈創作過程中,編一段舞蹈動作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他完全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編舞的定義,而是把編舞的過程變成一個與舞者身心交流的過程,用很多非舞蹈的手段把所要表達的東西變成一個個非舞蹈性的素材,然後再去根據舞段的創作需要進行排列組合。
例如:在“自拍照的二維碼”那一舞段裡,每一個人的行走路線;每一個磚頭的擺放位置;每一個人的抬頭、低頭、睜眼、閉眼、張嘴、閉嘴以及一顰一笑都是由每一位舞者將自己在2018年12個月裡每月的自拍資料統計出來,構成了行走曲線圖、動作姿態和磚頭擺放的位置。如下圖所示,這就他要求舞者們做出的非舞蹈的功課:
《無自畫像》演員舞臺行走路線
因此,他更像是一位導演,採用不同的藝術語言,運用不同的創作手段,引發每一位舞者內在的潛能,鋪設出人意料的場景,讓舞者的身體融入其中,自然生髮出肢體舞動的慾望和方向。
我們說,所謂具象發端於對現實的摹寫,以再現作為創作的起點;而抽象則來源於觀念或情緒的表現。再現與表現是所有藝術創作的兩個重要的手段。但汪圓清在《無自畫像》中則試圖是在這二者之間找尋另一個方向,既不需要描摹生活真實的景象,也無需藉助舞蹈的表現手段宣洩人物內心的情緒。而是冷靜地、平和地呈現一種內心視像。而這種內心的視像並不脫離生活形象,又不去確定真實細節,只是去喚起所有人的聯想(包括舞者和觀眾)。即可謂之:“功夫全在舞外”。這種意境大於形象的方式,使人們視覺所看到的畫面就變得自然深遠起來。
《無自畫像》劇照3
三、在“第三空間”裡
在藝術創作中我們常常會提到一個叫作“第三空間”的概念,在這個空間裡我們是看不到人的完整思想,卻能感受到在那瞬息萬變的思想中的“一閃之念”。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所存在的心像,別人是無法看見的。然而,在《無自畫像》中,編導汪圓清則非要把這不可視的心像呈現於舞臺,將這不可視的潛意識描繪成一幅畫像。他正是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這種具有原創可能性的第三空間,一種可以展示“內心視像”的美學方式。
《無自畫像》選擇了一種不定型的表現形式,在內容的引導下,去追求視覺上的抽象,從而既不使其成為內容的圖解,也不刻意去強調某個形式,而是運用人的內心深處那個神秘的感召力,召喚出人的潛意識中所隱藏的影象,那也是在我們每個人內心中尋覓和發現得到的自我關照的景象。
例如:作品中有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網路遊戲。
網路遊戲的設計者總是極力想把現實社會中真實存在的人物原型設計進網遊中,而現實中的人們卻在極力去模仿遊戲中的人物,總想去體驗和嘗試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另一種虛擬的生存狀態。這大概就是人的潛意識裡的善與惡的較量,人性與獸性的對峙。
在這個場景裡,您彷彿看到有那麼一群人,在一個夜晚,經歷了一次權力和暴力的遊戲體驗。剛剛還是人與人之間你來我往,親密友好,瞬間變成了互相殘殺,你死我活;剛剛還是“美好的人間”瞬間變成“瘋狂的地獄”。這種體驗的結果對我們的教育有一種勝讀十年書的感覺。人間與地獄的轉換告訴我們﹕按照所謂進化論的推論,人從野獸進化成人類需要幾千萬年,而要讓人類從人轉化為野獸,只要一瞬間。
四、關於《無自畫像》的社會性
在6月8日晚第二場演出結束後的藝人訪談中,有觀眾提問道:“這個作品主要是根據演員自身的資料來表現這14位特定人物的自畫像,你將來是否有興趣用舞者的身體去表現更大範圍裡的具有社會性意義的自畫像?”
其實,我認為汪圓清的《無自畫像》已經遠遠超越了舞者和舞蹈本身所存在的領域,它所反映出的“數字遺產”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很社會性的問題。正如有些人認為“無字碑”是武則天個人意義上的特殊記錄方式,而它的社會性就在於武則天把自己的千秋功罪放置在一個廣闊而悠久的歷史空間裡“任人評說”。正因為她所立的這個碑“無字”,因此,凡是看到這個碑的人都很想把自己對武則天的“字”刻寫上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汪圓清的《無自畫像》也正是在引導著所有的人(包括舞者和觀眾)把自己的自畫像放進這個時代的大畫面裡去,在無和有之間去判斷自己存在的虛和實。這是一種具有哲學意義的“無中生有”。
五、“和時空”對話,“用樂響”交流
在舞蹈裡“說話”,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但人與時空對話,並同時與許多人對話,這卻是《無自畫像》的創意:一個舞者與其他十三個舞者的一段微信回覆,巧妙地運用了時間與空間的差異性,讓我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也像這回復晚了的微信一樣:已經時過境遷,再也不能尋回那當初及時的感覺中。
在《無自畫像》第二版創作中,編導汪圓清和音樂師劉一緯也是再度合作,只不過在《無自畫像》第一版合作的時候,劉一緯提供的是根據舞蹈內容需要,自己製作好的一段一段的音樂,而這一次兩位老朋友在作品中再度聚首,似乎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因為整部作品的音效和樂響完全靠音樂師的一雙手和舞者同步配合,才達到了該作品所具有的聲音和舞蹈完美結合的藝術效果,可以這麼說,舞者是在用身體跳舞,而音樂師劉一緯則是用他的一雙手跳舞,並且跳出了一種境界:彷彿宇宙神秘的韻律就蘊藏在這美妙的樂響之中。
六、一個永恆的話題:“活著”還是“死亡”
衡量社會文明的尺度本應該是我們人類自己,但在這個瘋狂的數字媒體時代人卻沒有時間考慮自己。人究竟是什麼?人就好像是那一塊塊磚頭,是用來建築起控制人的城垣,即作繭自縛。於是我們今天“活著”,卻感受到了一種“死亡”。
在《無自畫像》的一個讓人揪心的舞段裡,我們看到了一種近似殘酷的侵略,是人對人的侵略,是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靈魂主權的剝奪。人沒有了隱私,沒有了真正的自我。是一部份人強迫另一部份人交出靈魂,成為了透明的人;是一部份人強迫另一部份人交出大腦,變成了無腦的工具。這種如同死亡的被侵略,成為本世紀人類的超級恐怖。因此說,本.拉登的恐怖算什麼?就整個人類世界來說,他只能操控和恐嚇那極少數的一部分人。而數字媒體時代幾乎我們所有的人被極少數的人掌控著。於是,這個時代給我們留下了一道哲學命題,值得我們去好好思考:
活著的時候不一定能活得很好,但是死後卻還能“好好地活著”。
《無自畫像》劇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