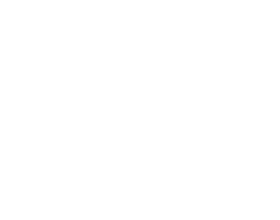當代的琴家又賦予《酒狂》一曲以新的色彩。1956年,廣陵派劉少椿在南京藝術學院任教時,與甘濤共同為《酒狂》打譜,節拍定為2/4、3/4與4/4拍的混合使用:
譜例1:劉少椿打譜《酒狂》
同時,他在演奏時採用了廣陵派的一系列特定指法,如用“長鎖”(在同一根弦上先抹、挑緩連兩聲,再用抹、挑、抹、勾連緩四聲,再用剔、抹、挑連彈三聲,共九聲)指法演奏的一串同音,以其特有的不露痕跡的過弦及富有程式化的劃圈手法,生動地闡釋出廣陵派“虛實寬窄”的古琴演奏特點,描繪出了一個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卻又極富抗爭力的阮籍形象。
20世紀50年代,引起音樂界普遍關注與好評的《酒狂》打譜版本,是由著名的浙派琴家姚丙炎先生於1957年以《神奇秘譜》為藍本,並參照《西麓堂琴譜》定譜而成功打出的琴譜,這是中國古琴史上,第一個規則使用三拍子的《酒狂》打譜版本。
《酒狂》曲子短小精悍,結構嚴謹,變奏體,分為四段加一尾聲。姚先生起初把它試彈成2/4拍,“彈了幾遍,覺得不對頭,簡直毫無酒意”,於是改彈2/4拍的切分節奏,“這樣雖然活躍些,但這種跳躍氣氛,和阮籍那種託酒佯狂的酣醉境界距離還是很大”。無奈擱置一段時間後,他又仔細研看樂譜,“發覺它全是三字句組成,即三個音一句。而且從全曲來看,基本上只有四大句”。於是姚先生靈感突發,在其節奏上做出了獨創性的三拍子處理,並有意識地打破一般的三拍子強弱規律,將重音後移,在第二拍出現沉重的低音或長音,造成了一種頭重腳輕、站立不穩的感覺,從而形象地刻畫出阮籍在醉酒後步履踉蹌的神態。
凝神欣賞此曲,可以發現姚先生並不注重於表現樂曲表面的狂態,而是透過描繪種種情狀,著重闡釋傳統“託興”之審美,即阮籍借酒佯狂,實為抒發內心積鬱之氣。據姚先生所言,他對《酒狂》的打譜為“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但他對《酒狂》這一特殊節奏的詮釋靈感,並不是憑空生成,而是以他所稱的“試之再三”即持之以恆的古琴演奏、研究為基礎的,當然更重要的是姚先生不怕懷疑、勇於嘗試的探索精神。
譜例2:姚丙炎打譜《酒狂》
1959年秋天,姚先生從上海去北京參加“胡笳”音樂會時,將其打譜的《酒狂》傳至北京,受到了北京古琴界的充分肯定與重視。但同時,琴家們對那種整齊劃一的意蘊與略有西方音樂風格的純6/8拍不甚滿意,並認為3拍的長音使旋律產生不流暢的停頓之感,於是吳景略等先生在該版本的節拍、節奏上動了腦筋,將姚先生原有主旋律句尾後半小節的3拍長音,截短為兩拍,由此樂曲原有的固定6/8拍,就變成了6/8與5/8混合拍的進行模式。這樣一改動,具有不穩定感的音樂與酒醉神態更為貼切,如同一位沉醉的舞者,步履搖曳,不能自已。
譜例3:吳景略打譜《酒狂》
由於此種複合拍的形式在《酒狂》曲中取得了一定的較高的審美效果,並得到了較多琴家的認可,因此,此後《酒狂》的打譜版本基本遵循了這種複合拍的形式。但因琴家對其醉者形象有著不同的理解,並在速度、力度、節拍節奏以及旋律潤飾等因素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個性處理,所以同為6/8與5/8混合節拍的打譜,也會刻畫出不同程度醉態的效果。如李祥霆先生的演奏版本,其速度略快,情緒活潑跳躍,強弱對比鮮明,展現的是一位略有醉意而亢奮好動的人物形象。
後來該版本《酒狂》在新浙派源頭杭州流傳時,浙派琴家徐匡華又將主旋律第二小節6/8拍中的第二拍進行任意延長,以凸顯音樂的不穩定感:
譜例4:徐匡華打譜《酒狂》
同時在旋律上行時逐漸加大力度,下行時減小力度,這時的音樂形象描繪出了一個微醺的醉酒者瀟灑肆意邁著酒步起舞,時近時遠的形象。
琴家龔一先生對此曲又有他自己的獨到見解。打《酒狂》譜時,他完全拋棄了姚先生奠定的三拍子,而將整首曲子處理成散拍子,速度緩慢,節奏時松時緊:
譜例5:龔一打譜《酒狂》
這時的音樂形象是一個頭重腳輕的酗酒者踉蹌走來,爛醉如泥卻還不時地掙扎著要繼續喝酒。對比其它版本的《酒狂》,龔先生所刻畫的阮籍形象似乎更多了幾份醉態,而其更是透過這種“酒徒”的形象來摹寫阮籍外表的狂態和內心的苦楚,正所謂是“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還有一個《酒狂》版本是由吳文光先生打譜。其在保留複合拍的基礎上,在其中穿插整句的單純拍子,透過這種節拍的變化對比來加深對醉態的表現。例如,有幾個完整的5/8拍句子穿插在6/8、5/8拍結合的旋律之中:
譜例6:吳文光打譜《酒狂》
這種將整體對比細化到區域性對比的處理方式也極具新意。而吳文光先生以雙古琴形式對《酒狂》進行演繹,則是在民族音樂內部的成功嘗試。其雙古琴合奏,並非我們習慣理解的、單純的同一條水平線上的合奏模式,而是在同一個聲部中採用了複合節奏形式,且還將此種形式運用在第二古琴和第一古琴的對位中。即第一古琴仍舊保持原來的演奏節拍,而第二古琴則採用4音一組的形式。這與鋼琴音樂中經常出現的4對3的節奏類似。
譜例7:吳文光的雙古琴《酒狂》
這種處理方式極富動感,在交錯複雜的復節奏中將阮籍左右搖曳、步履踉蹌的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該雙古琴合奏的形式不僅加強了琴曲的表達效果,還可以說是對拓寬古琴表現領域的一種有效嘗試。目前琴界還流行著其它曲目的雙古琴合奏形式,如《平沙落雁二重奏》等。因此,吳先生等琴家在古琴曲上的創新思想,不單是停留在某一首曲子的表現上,而是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對後學的音樂演奏及古琴演奏的發展起到了比較重要的指導作用。
根據《神奇秘譜》的題解,《酒狂》結束處主音do和屬音sol的連續使用,表現的是“仙人吐酒氣”,其表達了佯狂的背後藏著隱忍的痛楚。當時魏晉文人們有一種癖好是長嘯,也就是打口哨。也許是因為口哨既無語言,也無固定的旋律,符合玄學家言不盡意,以無為本的思想,人們把它作為語言和音樂無法表達的情感手段,而阮籍正是奉行這股風氣的佼佼者。即使對這段音樂性較具象、文字也有標明的樂句,琴家們也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姚丙炎先生給出了固定的三拍子;徐國華先生到此用九聲“長鎖”指法,接抓起音表現;而北京琴家李祥霆卻認為不雅且多餘,去之。
以上我們看到了不同的琴家在解讀《酒狂》時,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從而有了不同的打譜和音樂處理。也許這正是古琴曲給我們的混沌魅力吧,它讓我們猶如看到畫家筆下塑造的一個個不同的阮籍形象,體會到了每個人心中對一代名士狂放不羈、複雜又充滿魅力的內心世界的理解,正如世人所說“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形態不一,趣味無窮,音樂的多解性在這裡得到充分的展現。
參考文獻
徐君躍《琴曲<酒狂>的琴家詮釋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