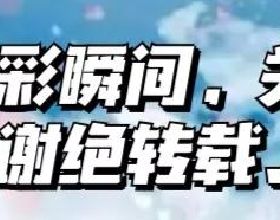人的閱讀應該是貫穿一生的。 視覺中國供圖
《名家書單》孫鶯 編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從晚清到20世紀初的各種報紙上,刊登有大量回憶敘述以往種種的文章,由於作者是當時的人,所寫均為當時的事,親歷親見親聞,保證了文章的可靠性,並因而具有新鮮的語境以及豐富的細節,堪稱研究近代中國的一手文獻。然而,由於以往查詢報紙資料的極大不便,這些文獻大都湮沒於報海當中,長期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由張偉主編的“近代報刊文獻輯錄叢書”所收錄的正是這些被遮蔽了一個多世紀、以近代上海為中心的珍貴文獻。
這套叢書中的《名家書單》是孫鶯的最新成果,收錄了當時各界名人的讀書書目,有開給別人的推薦書單,更多的則是自己的閱讀心得,以及與書相遇的記錄,不但能讓專業研究者汲取眾多新鮮史料、開啟視野、大獲收益,普通讀者也可從中瞭解知識、心結頓開、獲得閱讀的快感。
一種相通的境遇
儘管讀書是件很私人的事,但由於每個私人組成了大眾,結果導致讀書無論在何時何地,總是與時代、社會休慼相關
說起來,閱讀是很私人化的,每個人閱歷不同、背景不同、興趣不同,自然讀的書也不同,所以的確很難為別人做薦書之事,也由於私密性,甚至都不願公開過多過細地談及自己的書齋和藏書。我想,魯迅先生當年之所以拒絕孫伏園為《京報副刊》開列“青年必讀書”,蓋因如此吧。正因為這樣,在浩如煙海的民國報刊文獻中遴選出一本《名家書單》來,實在很不容易。
不過,做“名家書單”倒是歷來的傳統,儘管九十多年前魯迅先生弄出一個“梗”,可至今仍方興未艾,而且沒有受到紙質書在電子媒介衝擊下疲軟委頓的影響,顯出愈盛之勢。或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人的好奇心有關。人的好奇心無所不包,窺探名人的私家書單,看看他們都讀些什麼書,向來為人所樂道,我以為這沒有什麼不好。既為名家,總有不一般的地方,對於普通人來說,瞭解他們的閱讀,乃至隨之跟進,從小處說,能滿足好奇心;從大處說,這是一種傳播,跟隨有人生閱歷、有獨立見解、有讀書門道的名師大家進行閱讀,乃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
名人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現下,每每推出一本書,出版社總要拉來名家“聯袂推薦”,看來並不是多此一舉,名人效應還是有的。
其實,名人們的書單分散四處,常就是一瞥罷了,但是,一旦聚合成書,那就不一樣了。我讀《名家書單》頗感震動,感受到成規模後的浩蕩和遼闊,恰如書中作家、翻譯家胡山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集在一處,便可以成為洋洋大觀”,20世紀三四十年代迎面而來,一個時代的風氣、風尚、風貌面目清晰得觸手可及。原來,所有的閱讀都是一種相通的境遇。
1935年,《青年界》雜誌開設了“我在青年時代所愛讀的書”欄目,我瀏覽了一下眾多撰稿人的書單,發現雖然他們年齡、出身各異,專業領域不同,讀的書卻多有所雷同:《史記》《詩經》《牡丹亭》《水滸傳》《三國演義》《聊齋志異》,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魯迅的《吶喊》與《彷徨》,胡適的《胡適文存》,托爾斯泰的《復活》和《藝術論》;雜誌則有《學生雜誌》《小說月報》,而且還都強調這兩份雜誌換了主編,進行了革新,《學生雜誌》改由楊賢江編輯,《小說月報》則改由沈雁冰編輯,而這兩人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這些互有重合的書單,很明顯地打著時代的烙印,從中反映出當時被關注、被考慮、被鼓動的社會思潮。
由此上溯,就可以明白當初耿直的魯迅先生為何拒絕開列“青年必讀書”了,因為那時頑固、守舊的世風與他格格不入。這讓我想到,儘管讀書是件很私人的事,但由於每個私人組成了大眾,結果導致讀書無論在何時何地,總是與時代、社會休慼相關。
一種人生的索引
透過一個人讀什麼書,便可以看出其人及那代知識分子當年的思想狀態和人生追求
如果我們可以從《名家書單》中發現讀書是時事與思潮的投射,那麼,我們更可以從每一份具體的個人書目中找尋到其人生的索引。
學者、作家、翻譯家施蟄存先生寫於1936年的《繞室旅行記》,趣味十足,他圍繞自己的書齋做了一次“旅行”,並像導遊一般悠悠揚揚地向讀者介紹了他曾閱讀過的那些雜誌,而閱讀那些雜誌恰恰構成了他的人生歷程。“旅行”從剛拿到的《宇宙風》雜誌開始,翻完之後,袖手默坐,眼前書冊縱橫,不免閒愁潮湧。“書似青山常亂迭”,則書亦是山;“不知都有幾多愁”,則愁亦是水。於是,生出“我其在山水之間乎”的感慨。
太息之後繼續“旅行”,那是一沓沓的畫報與文藝刊物,畫報中最可珍貴的是巴黎印製的《真相畫報》,印著許多有關辛亥革命的照片,而“我對於它最大的感謝,卻是因為我從這份畫報中第一次欣賞了曼殊大師的詩畫”。在文藝刊物方面,則喜文明書局出版的三本《春聲》,其篇幅每期都達四五百頁,厚厚的一本,“是以後的出版界中不曾有過的事”。緊接著,“旅行”陡生懸疑,在一大批塵封的舊雜誌中,居然發現了一個紙包。開啟來一看,原是一份紙版,那是幾年前與戴望舒、杜衡、馮畫室一起為上海一家書局編輯的一本三十二開型的新興文藝小月刊,那時費了兩天的斟酌,才決定刊名叫作《文學工場》,“當時覺得很時髦,很有革命味兒”。不料,書局沒有透過,戴望舒和馮畫室前去交涉,最終帶回來了這本文學小月刊第一期的全部紙型,“老闆不敢印行,把全副紙版送給了我們!”
重新察看這始終未曾印行出來的《文學工場》創刊號的內容,一共包含著五篇文章:杜衡的譯文《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馮畫室的《革命與智識階級》和翻譯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施蟄存的擬蘇聯式革命小說《追》,戴望舒的新詩《斷指》。
“當我把這一包紙型鄭重地包攏的時候,心中忽然觸唸到想把它印幾十本出來送送朋友,以紀念這個流產了的文學月刊。”“旅行”至此,我想,我們可以找尋到施蟄存先生後來執著於編輯《無軌列車》《新文藝》《文飯小品》,尤其是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的人生索引了,而且我們還可以追溯到他以及他那代知識分子當年的思想狀態和人生追求。
《名家書單》中,這樣既生動有趣又不乏思想見地的文章還有很多。比如學者、作家許欽文的《〈新青年〉和〈新潮〉》,說自己先前並不愛讀書,平日裡做做手工、釣釣魚,有一次忽然得到這兩本雜誌,讓他知道了新文學,就此走上了小說創作道路。學者、教育家朱維之在《介紹四本書》一文裡,推薦了羅曼·羅蘭的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和郭沫若的研究專著《青銅時代》,認為前者有美的理想、美的情調和美的文字,可以藉此接受審美薰陶;後者可以啟發人們的批判精神,可知道怎樣去“讀死書”而不是“死讀書”。
其實,1930年,也就是魯迅先生拒絕開列“青年必讀書”後的第五年,他的好友、教育家許壽裳的長子許世瑛考取了清華大學國文系,許壽裳請他為其兒子列一份書目,魯迅先生還是以拳拳之情開列了12種書單,包括《世說新語》《全隋文》《唐詩紀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有史、有論,還有工具書,正是國文學習的入門書籍。魯迅先生還附上了簡明扼要的解說,如從《論衡》見漢末的風俗迷信,由《抱朴子外篇》看晉末的社會狀態等。時至今日,這份書單對於有志讀書的青年還是有很寶貴的建議。
一種摸得著的感受
不論閱讀方式有何改變,閱讀本身會是永恆的存在,人類文明的成果終將透過閱讀得以傳播和發揚
我覺得,人的閱讀應該是貫穿一生的,鴻蒙初開之時,跟隨名家書單讀書,不啻為一條捷徑。說實話,迄今我都很看重我所信任的國內外大師名家的書單,會從中汲取智慧;我還關注當下出版界、傳媒界推出的各種最新書目,會從中得到有益的資訊;當然,隨著自己人生的展開,我也積累了自己的書單,並樂意在各種媒介上進行“閱讀推廣”,與愛好讀書的朋友們分享。
我承認,我個人的閱讀史、我個人的書單就是我自己人生的索引,一路走來,我的閱讀書目也一路發生著變化,而這些變化無不與我所身處的時代和社會的思考、理解和認識有關,自然,也對我的文學和藝術創作、專業方面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我看來,不論閱讀方式有何改變,閱讀本身會是永恆的存在,人類文明的成果終將透過閱讀得以傳播和發揚,因而“名家書單”也就永遠不會落寞。在推進全民閱讀中,各種書單、榜單層出不窮,便是佐證,固然有推廣因素,這卻與傳統、與讀者的需求是相承和呼應的。雖然“名家書單”到了今天已有更多的內涵,即便在形式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時俱進地拓展為線上線下的活動,衍生出讀書節、讀書講座、讀書音影片、讀書旅行等等,但是,契合了過往眾多卓有成就者人生軌跡的《名家書單》這本書,還是讓人有一種摸得著、看得見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美好而真切的感受。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