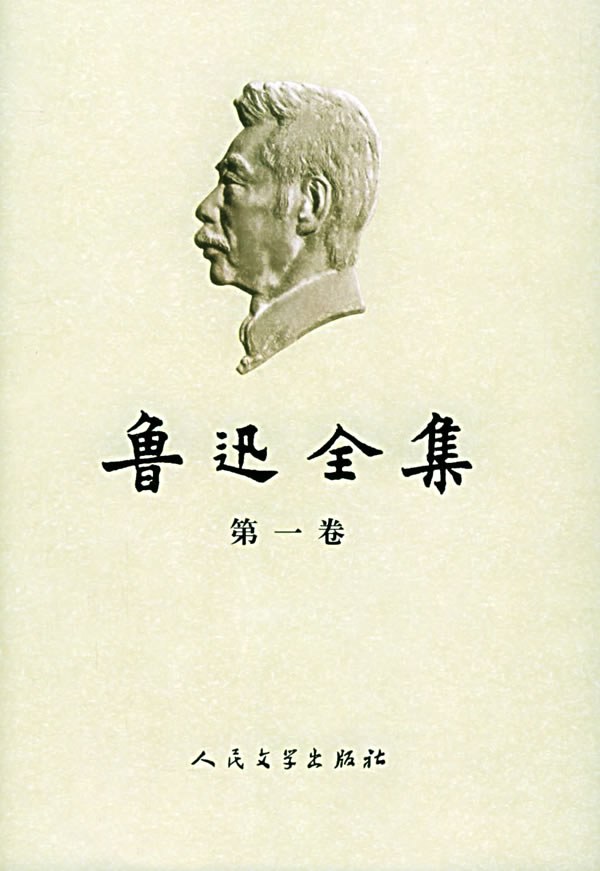吳靖
近代以來,魯迅或許是第一位深刻思考天才問題的中國人。
現代意義上的天才概念大約誕生於17世紀,指一個具有“天生的智力或才能(natural intelligence or talent)”,以及“顯著的天生的心智慧力(exalted natural mental ability)”的獨特個體。這正是我們今天所熟悉乃至崇拜的天才之意涵。事實上,它與歐洲啟蒙運動的文化轉型密不可分。歐洲文化在這一偉大的歷史時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從現代科學的誕生,到微積分的發明,從天文學、經濟學等重要學科的創立和發展,到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重要思想的確立和宣揚……而在所有這些進步背後,是相信人類可以透過自身的智慧開啟通往宇宙的鑰匙,從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一核心理念。可以說,這幾乎就是後世“天才崇拜”的原型。這一影響巨大的情結跨越中西方文化,至今仍為全世界所津津樂道。
天才與民眾
1924年1月17日,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發表了著名演講《未有天才之前》,由葛超恆記錄。這篇演講稿最初發表於師大附中《校友會刊》第一期,後經魯迅校正,於同年12月27日刊於《京報副刊》,最後收入《墳》(《魯迅全集》第一卷)。毫無疑問,這次演講的主題正是“天才”,其核心觀點圍繞著天才與民眾這一對基本概念。魯迅從當時文藝界對天才的盛大的呼聲講起,直言“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進而指出了一個極為荒謬的矛盾現象:“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於是,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想要有天才,首先要有產生天才的民眾。他說:“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在此,魯迅祭出了一對關鍵性的概念:天才與民眾。作為孕育天才的土壤,(高素質的)民眾是最為緊要的,沒有好的土壤,便沒有爭奇鬥豔的花朵。
當然,魯迅並未否定天才的存在,他在最後講道:“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同時又說:“泥土與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艱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是的,只有花大力氣提升國民的整體素養(也包括個體的自我提升),天才才有希望兌現他的卓異天賦,這正是泥土的偉大之處,這足以令每位教育工作者良久深思。
我們得承認,在魯迅這篇演講之後近百年的今天,他談到的問題依然存在。無論是廣為流傳的“錢學森之問”,還是全社會長期熱衷的“奧數班”“少年班”“尖子班”等等,一定程度上都是魯迅天才之憂思的某種變奏和迴響,“土壤”問題再度迴歸人們的視野。2020年11月16日,鄭也夫先生給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一年級新生作了題為《興趣的摧毀與發現》的演講。在這場同樣意義深遠的演講中,他直言興趣形成的關鍵是自生長,並指出了需要滿足的三個條件:一是有閒,二是自主,三是廣泛接觸各類學科、各種遊戲。最後他沉重地說道:“這三個條件本來應該是稀鬆平常的,但不幸在我們今天的教育中,大多數學生都得不到。”興趣是“土壤”質量的關鍵,一旦興趣被摧毀,“土壤”也將不復存在。
我們也得承認,美國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孕育了一大批改變世界的天才,美國文化在培育土壤(民眾)方面值得全世界學習。為此,一位名叫傑克·黑特(Jack Hitt)的美國記者專門寫了一本書來闡述美國文化的這一特質,名為《一幫業餘愛好者:探訪美國國民性》(Bunch of Amateurs: A Search for the American Character)。他在書中指出,19世紀中葉的家庭作坊形式開始與職業化趨勢競爭,隨著工業革命的降臨,職業化的速度加快了。但業餘愛好者從未消失,美國人認為業餘愛好者是夢想家,他們痴迷於某種真實的東西,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天才、做出重大發現。由此,他鮮明地斷言:“對業餘愛好者的崇拜是美國文化的靈魂。”正是這種深厚的文化造就了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和黑特所談論的東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存在著隱秘而深刻的聯絡。事實上,美國龐大的高素質業餘愛好者群體,正是魯迅所謂的產生天才的民眾、孕育大師的土壤。有了他們,才有了愛迪生與特斯拉、萊特兄弟與寇蒂斯、赫斯特與普利策、海明威與福克納、希區柯克與庫布里克、奧本海默與馮·諾依曼、喬布斯與馬斯克……這一連串的天才塑造了美國文明,也深刻影響了人類文明的程序。近百年前,魯迅直指作為天才孕育土壤的民眾的重要性。如今,黑特告訴我們,僅僅崇拜天才孕育不了天才,對業餘愛好者的崇拜才是孕育天才的關鍵,這與魯迅的天才之思幾乎如出一轍。
天才的群體效應
近百年來,對魯迅的天才之思做出的最有力回應和深化,當屬著名歷史學家王汎森。2008年12月13日,王汎森先生在《南方週末》發表了《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一文。在新媒體尚未大規模來臨、紙質媒介仍是知識分子人文思想交流重要陣地的年代,此文一出旋即引發廣泛矚目。那種關注,遠非時下讀者在網路上開啟一篇文章之後,或隨手“點贊”、或跟風“轉發”所造成的“流量幻象”,而是切實進入作者的思考視域,切磋琢磨,追古觀今,力求解答那時擺在人們面前的共同問題。
在文中,王汎森舉了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例子,這位據稱是當時人類最有智慧的人,現實中似乎總有參加不完的宴會,殊不知這可能是他“萌發新思想的場合”。類似的例子他也信手拈來,如19世紀末維也納的咖啡館,20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家的“週末派”,俄國以別林斯基(V.G.Belinsky)為中心的文藝圈等等,莫不是在思想交流中碰撞火花,即一群人共同做學問,並把一個人頂上去。王汎森對此評價說:“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
於是,我們看到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成了“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直到20世紀上半葉,維也納依然是天才匯聚的重鎮。在此,王汎森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1920-1930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 Vogelin等人。是的,如今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大師、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只是利用業餘時間研究經濟學,但他每週五晚7點的私人討論會質量極高,堪比愛因斯坦創立的奧林匹亞科學院。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米塞斯由日內瓦輾轉到美國後,於1945年以“訪問教授”的身份重新開啟了他的研討會,一直持續到1969年5月。由此,米塞斯將維也納的私人研討會傳統帶到了紐約曼哈頓的一個地下室,將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帶到了美國,而且開創了以其行動學為中心內容的新奧地利學派傳統——其標誌就是1949年其英文版《人的行動》(Human Action)鉅著的問世。事實證明,他的研討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一開始,參加研討班的不僅有紐約大學商學院的學生,還有來自校外的各色人等:新聞記者、商人、作家和其他大學的學生。研討會成了紐約周邊對古典自由主義學術研究感興趣的知識分子聚集地,同時也吸引了很多國外來訪者。在此,我們極為直觀地感受到了美國強大的業餘愛好者傳統,他們實實在在地構成了天才(及其傑作)誕生的肥沃土壤。1974年,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奧地利經濟學派自此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哈耶克的得獎也是對其老師米塞斯在這方面開創性研究貢獻的肯定。
王汎森所謂的“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現象,我願意將之稱為天才的群體效應。王先生站在巨人魯迅的肩膀上,將魯迅提出的民眾的宏闊概念進行了聚焦,重點鎖定在圍繞於一兩位天才人物身邊的一群人。正是這一群人,經由一場場不斷深入的陳述、研討乃至辯論,徹底激發了天才身上的天賦才能,形成了一個縱情激盪思想、揮灑天才的無形場域。對此,王汎森以“風”的比喻進行了精彩的闡述:“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人文學科的危機
我們如果足夠誠實,就不得不直面一個苦澀的問題,它恰好構成了王汎森之問的反面:(這個時代)為什麼天才沒有成群地來?這一問題背後所隱藏的,正是席捲全球的人文學危機。這一危機,在東亞尤其是中國表現地極為顯著,它不僅摧毀著天才成群而來的生長土壤,更使人文學的存在意義和內在價值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突出表現在“自然科學化”傾向和“指標化評價”兩大方面。
在社會科學領域,自然科學正規化、方法和評價體系對其的影響極為深刻,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人文學領域,自然科學化卻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更糟糕的是,這種傾向已經成為一種可怕的現實:只有有用的學科才有存在的意義。因此,倡導“無用之用”的人文學在這個處處強調實用主義的時代備受質疑。據說,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著《為歷史學辯護》,就是在兒子追問“學歷史有什麼用”的刺激下寫成。在大學裡,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自然科學興起和獨大後,人文學的這種春風化雨般的精神浸潤與傳遞,亟待重提和喚醒。
當下人文學危機的另一表現,是指標化評價尺度的泛濫。專案和論文至上的評價導向讓人文學術的特殊性蕩然無存。就專案而言,對於多數理工科學科來說,專案至關重要。對於某些社會科學學科而言,專案也有其必要,沒有專案,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察、問卷調查和資料蒐集便不易進行。人人心知肚明,只要有一支筆和一臺電腦,人文學者就可以利用圖書館和網上資源進行研究和寫作。事實上,古今中外人文大師們的成果都不是透過專案搞出來的,“一流的學術成果不是專案而是閒暇的產物”。
或許評價人文學者畢生成就高低的幾乎唯一的標尺,不是專案也不是論文,而是著作,這是由人文學術必得“著書”才能“立說”的內在特質所決定的。這就是為什麼一提到錢鍾書,馬上聯想到《管錐編》《談藝錄》;一提到陳寅恪,馬上聯想到《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提到福柯,馬上聯想到《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一提到薩義德,馬上聯想到《東方學》《文化帝國主義》……
愛因斯坦晚年被問及“如何看待早年的專利局生涯”,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學院式的職位使年輕人處於一種為難的境地。人們要求該年輕人寫出數量可觀的論文——這種誘惑將導致膚淺。……如果他有更強烈的科學興趣,除了完成被要求的工作外,他會致力於研究他所鍾愛的問題。我要感激馬賽爾·格羅斯曼,使我處在這樣一個幸運的位置上。”愛翁的這番言論的確引人深思,不難猜想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一定深深懷念著那所他親自創立的可愛迷人的“奧林匹亞科學院”。頗為弔詭的是,口口聲聲鼓勵創新的大學有時卻是扼殺天才的地方。
或許,對於天才來說,閒暇才是最好的大學。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